《一藏輪迴》 第1084章 八個時辰!賭一粒花生米
白一離開了觀世湖。
留給任公子的只能是一個背影。
有些,只能是生命中的不能承之重。
在最后的十二時辰里,白一能陪任公子喝一次酒已經算是一種報答。
不希隕落了,然后任公子日日夜夜思念于。
任公子沒有阻攔白一,也沒有挽留。
他明白,有些事是不能阻攔的。
風的心念,在白一心中高于一切。
白一在最后的時辰里能陪他來喝一次酒,那麼他就覺夠了。
若再相見,我便和你在一起!任公子回想白一的話,欣而又苦地一笑。
他明白,白一不是對他無,而是不敢用。
可是,還有不到八個時辰了。
我還能做什麼?任公子回頭看了看觀世湖。
湖面上,還有諸多蓮花。
他監察的世界可不僅僅是一個一藏世界。
可是,此時諸界在他的心中已經不重要了。
任公子又看了看白山的方向,然后單手一揚直接收起了釣竿,選擇離開了觀世湖。
…………聽界樓。
酒香四溢。
同時,杜書生與賈書生正在對賭。
兩個人吆五喝六的,聲音極大甚至傳出了聽界樓。
侍畫在旁邊一臉生無可地看著眼前的兩個書生。
本來,他是在門外看門的,后來他被了進來。
Advertisement
之前,他們說了什麼,侍畫并不知道。
然后,聽界樓便了賭場酒肆。
侍畫了酒保。
兩個書生喝了七八壇酒了。
那些酒,都是賈書生的珍藏。
但是,侍畫實在是不了兩個人了。
因為,他們的賭注就是一碟花生米。
誰贏了,誰吃一粒。
酒則是不限制的,花生米不能隨便吃。
因此,兩個人似乎都有幾分醉意。
“唉!”侍畫無奈地搖了搖頭,“但凡多一盤花生米,你們也不至于醉這樣!”可惜,侍畫提議再上兩個菜,卻被兩個書生斷然拒絕。
他們要得就是這最后一賭的覺。
兩個人換了七八樣賭,各有勝負。
最后所幸就是劃拳有趣。
有辱斯文!侍畫在心中腹誹,虧你們兩個還自稱書生,為什麼不弄點文雅一點的?比如,詩作畫。
“三生石呀!”“七回啦!”“一世一心!”“四方云!”“九九歸一!”“……”兩個書生手中比劃,口中大喊。
只不過,他們的口令和一般的凡俗不同。
他們的口令多了幾分出塵的味道。
但是,此刻他們豪氣干云。
大碗喝酒,大聲呼,只不過不能隨便吃花生米。
“嘿嘿!你又輸了!”賈書生灌了一口酒,然后用中食二指很是愜意地夾起一粒花生米送到里。
“滋滋——”賈書生表陶醉,然后細細地嚼著那粒花生米,居然還滋滋有聲,似乎他吃得乃是一等一味靈食。
“再來!”杜書生自然不服。
只不過,他今天的手氣似乎差了一些。
一碟花生米,他只吃了七八粒,這還不算吃到的兩粒。
“哈哈!杜書生,你這運氣不行呀!”賈書生打了一個酒嗝,“原來,我一直是大意了。
今天,我一認真,你就完蛋了吧!”“哼!”杜書生冷笑一聲,“我這是怕我死了沒人陪你賭,給你留個念想!”“不用!”賈書生傲然道,“你不行,就是你不行!”“我不行?”杜書生擼起了袖子,“來!”“愿雙修呀!”“五行生呀!”“八苦遁!”“喝!——”賈書生又贏了,邊喝酒邊吃花生米,“哈哈!”賈書生覺這是他在落凡鎮上最得意的時刻。
諸多年來,在賭上,他可是一直被杜書生在下面的。
話說,哪個男人愿意總在下面?今天,他終于要翻了。
“鄙!俗不可耐!俗不可耐——”侍畫在心里嘶喊,然后他低頭開始作畫。
這一刻,他覺自己才是一個滿腹經綸的書生。
旁邊的兩個乃是無賴賭徒。
“二師兄!”而就在這時,門外傳來白一的聲音。
“哦?”杜書生微微一愣,旋即收拾緒,轉出了聽界樓。
樓外,白一俏生生地站著,雙頰微醺,帶著酒意。
“告別完了!”杜書生道。
“嗯!”白一乖巧地點了點頭。
“該說的話都說了?”杜書生又問。
“嗯!該說的,都說了!”白一再次點頭。
“沒啥憾?”杜書生道。
“本就沒奢,何談憾?”白一了額前的一縷碎發,然后笑了笑。
“那就好!”杜書生嘆息了一聲,“小師妹,你千萬不要留什麼憾。
因為,我們未必能乘愿再來了!”“我明白!”白一道。
“嗯!”杜書生回頭沖著喊道,“書生,我走了!”“呃?”而此時,賈書生剛剛走出聽界樓皺眉道,“這就走了。
咱們還沒有賭完,花生米還剩不!”“呵呵!”杜書生不會再回頭,“咱們的賭,哪里有完?那些花生米送你了。”
“書生!”賈書生想要住杜書生。
可是,杜書生擺了擺手,直接帶著白一走了,就沒有回頭。
“公子,你的賭見長!”侍畫在旁邊沒好氣地道。
畢竟,剛才兩個人喊的他頭都疼了。
“呵呵!”賈書生卻是苦笑了一下,“哪里是我見長了?只不過,他今天故意讓我贏罷了!”“故意讓公子贏?為什麼?”侍畫有些不解。
“因為,他就剩下最后的十二個時辰了!”賈書生道,“不對!其實,已經不到八個時辰了。
他,不想讓我有什麼心魔吧!之前,我和賭幾乎全輸的。”
“杜書生要出門?”侍畫問。
“嗯!”賈書生笑了笑,“是的!一趟遠門,整個風一脈都要去,不知道什麼時候回來。”
“呵呵!”侍畫看著賈書生道嘆了口氣,“公子,你又再說笑了。
那杜公子如此決絕,辭別時頭都不回,怕是回不來了吧!你們算是至,他是來和你道別的吧?”“侍畫,你還不算笨!”賈書生點頭道,“風一脈要沖擊白山了,失敗了八次。
這第九次,怕也難以功!”“公子,他們不功,為什麼還去做?”侍畫道。
“因為不去做,永遠不能功!”賈書生道,“風一脈,值得敬重!”“書生,你倒是有覺悟的。
咱們是不是應該去看看!”旁邊傳來任公子的話。
他手持釣竿,頭戴斗笠,就站在不遠。
猜你喜歡
-
完結3849 章

不滅龍帝
身懷絕世血脈,少年自北漠拉棺而來,他要將世上神魔全部埋葬。
750萬字8.25 162049 -
完結1227 章

最強修仙高手
仙尊從修仙界重生回來,和女友見家長竟然被岳母看不起………
304.3萬字8 106163 -
完結1440 章

玄幻,我能無限頓悟
蕭云的系統只會一個功能——頓悟!體質平凡?頓悟混沌體!功法難修?頓悟圓滿境界!神通難修?頓悟圓滿境界!沒有什麼是頓悟不能解決的,如果有,那就頓悟十次,百次……
282.7萬字8 290835 -
完結1100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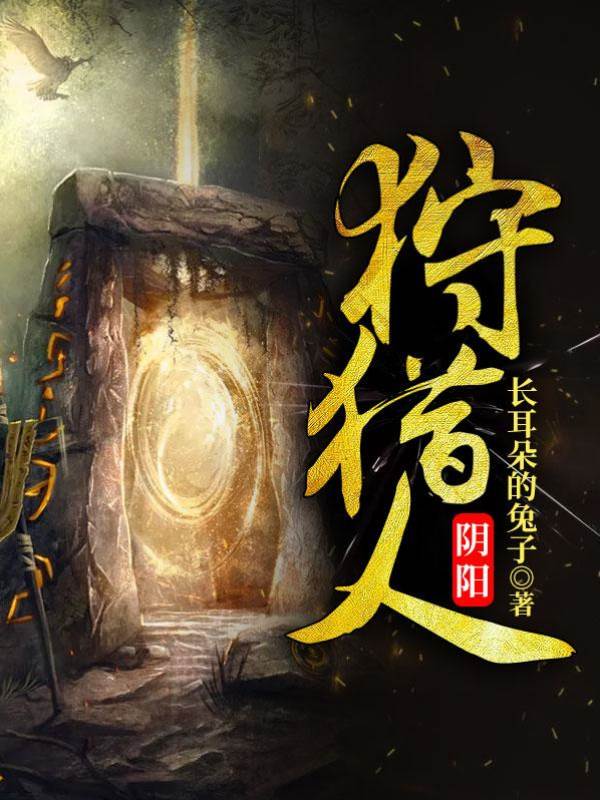
陰陽狩獵人
簡介: 一個傳承千年的神秘組織,一群擁有特殊能力的人,行走在陰陽之間,狩獵魅靈、僵屍、怨魂、妖獸等一切邪門東西!遊離在午夜的魅靈,複活的千年僵屍,修煉成精的妖物,《山海經》裏的異獸,這個世界並不像表麵看上去那樣簡單!
193.7萬字8.33 772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