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外懷了權臣的崽》 第53頁
「太.......太丟人了。」
還好方才在馬車裡,沒進宮在登極殿外等賀重錦,這幅樣子被朝中文武百們看見了,會連帶著賀重錦一起被恥笑的。
對了,還有劉裕和太后,前幾日進宮去見他們,江纓都是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從不敢失了面。
用不施黛的臉都覺得不妥,更別說是這幅天崩地裂的模樣了。
賀重錦:「這里也有。」
江纓低頭一看,淡藍衫上也有一片黑乎乎的墨跡,說:「夫君,來時的路上我正在寫字,馬車停得突然,墨硯倒下去了,許是在這個時候濺我一吧。」
記得自己寫的太迷了,把硯臺撿起來後用筆蘸了蘸墨,繼續在宣紙上書寫,本沒注意別的。
這時,一雙骨節分明的手了過來,將那面被倒扣的銅鏡翻轉,鏡子再次映照著江纓那張髒兮兮的面孔。
「總要正視自己的。」他溫聲道,「用心洗,會有洗掉這些墨的那一天。」
江纓並未聽懂賀重錦話中的深意,茫然地點點頭,他又問:「纓纓今日,為什麼會忽然來宮門外接我?」
Advertisement
答:「因為我想和夫君一起去姚遜家查案。」
起初江纓不打算出門,想著在家中練習八雅,後來見到文釗,順口問了一案子,文釗說賀重錦今日去見姚氏。
江纓聽說,姚遜剛死之時,姚氏跪在大理寺前哭訴,最後賀重錦鬆了口,才準去見賀夫人的首。
婦人喪夫,本就是一件痛心疾首的事,江纓想到之前賀重錦在地牢時詢問呂廣的形,不由得在心裡擔心。
一張榻上,一個錦被裡睡得久了,這個夫君如何對待公事的,江纓再清楚不過了,只是對待男子尚且可以狠厲些,對待子怎能行?
得看他,免得弄砸了案子。
賀重錦著江纓,烏黑帽之下是青年俊逸的眉眼,他自然而然地握住了的手,答道:「好,賀相府再大,也不比外面,等查完案我們一同回府,因為還有一些東西我沒給你看。」
「什麼東西?」
「現在告訴你尚且還太早。」他笑,「算是.......是驚喜。」
驚喜二字,與一朝宰相實屬不太相襯,但還是從他口中說出來了。
江纓點點頭,同樣握了賀重錦的手。
忽然覺得有個夫君是很不錯的,從前自己除了讀書,就是圍著江夫人轉,時常還要面對吳姨娘和許姨娘找茬。
現在邊只有賀重錦一個人,他平日裡又忙於國事,子沉穩,讀書時清淨不。
不僅如此,退一千步一萬步來講,至今年去桂試八雅,江纓再也不用翻牆了。
姚遜的家住在皇京東街一巷子口裡,巷子口狹窄,幾歲大的們進進出出,嬉笑打鬧,賀府的馬車太過寬敞,本進不去。
見到了,江纓放下墨筆,賀重錦道:「夫君,恰巧我寫完了,我隨你一起下車吧。」
「嗯,好。」
賀重錦走下馬車,江纓掀開車簾出來,馬車雖然穩當,但心裡總覺得搖搖晃晃的。
這時,看到了賀重錦一襲紫服,在艷下朝自己過來的手:「來。」
聽到這個字,江纓幾乎沒有猶豫,纖細玉手就這樣放在了青年寬大溫暖的掌心上。
江纓從馬車上下來時,賀重錦注意到淡藍下遮掩的腹部,心頭一暖。
從前無論去哪兒,他都是孤一人,邊只有侍衛文釗,從未想過有一天賀相府的馬車上會多出親近之人。
一個是他的妻,一個還沒出生。
他溫聲道:「慢點。」
江纓問道:「夫君,姚遜的家就在裡面嗎?」
「嗯。」
這條巷子口雖算不上破舊,但稱不上什麼適合安居之。
不過,江纓記得軍械監的鐵匠有一千餘人,鐵匠們日夜鍛造兵,每個月發下來的銀錢不算太多,所以姚遜夫婦住在這種地方並不奇怪。
巷子盡頭之,幾個頑朝著這邊跑過來,頑們沒輕沒重的,玩心旺盛,並未注意到江纓懷了孕。
幸好賀重錦及時上前,將江纓護在後,然後,孩子們便注意到了這個大哥哥投過來的寒冷目。
其他的孩子們嚇得跑開了,而年紀最小的僅有三歲,當場嚇傻了,一屁坐在地上哇哇大哭起來,甚至一邊哭一邊喊著:「娘!我要找我娘!」
哭聲刺耳,比磨刀的聲音還要令人心煩,小孩子都是這樣吵嗎?
江纓深吸一口氣,用平靜的語氣對賀重錦道:「夫君,你嚇到了。」
「我知曉。」他答,「顯而易見了。」
常年在安靜之讀書的江纓,聽不得一點風吹草。
實在忍不下去了,拉了拉賀重錦的袖:「哭得太厲害了,你去哄哄,讓停下來別哭了。」
賀重錦:「……」
「快去。」
把賀重錦推到了小孩跟前,自己則往後退了退,躲得遠遠的,在心裡默默地為賀重錦鼓勁。
賀重錦無奈笑笑,隨後幫小孩掉撿起在地上的撥浪鼓:「對不住,這撥浪鼓還給你,剛才的事,是因為我夫人有了孕。」
小士:如果覺得不錯,記得收藏網址 或推薦給朋友哦~拜託啦 (>.
: | |
猜你喜歡
-
完結940 章

農門長嫂富甲天下
倒霉了一輩子,最終慘死的沈見晚一朝重生回到沈家一貧如洗的時候,眼看要斷頓,清河村的好事者都等著看沈家一窩老弱病殘過不了冬呢。 她一點都不慌,手握靈醫空間,和超級牛逼的兌換系統。 開荒,改良種子,種高產糧食,買田地,種藥材,做美食,發明她們大和朝見所未見的新東西……原打算歲月靜好的她一不小心就富甲天下了。 這還不算,空間里的兌換系統竟還能兌換上至修仙界的靈丹,下到未來時空的科技…… 沈見晚表示這樣子下去自己能上天。 這不好事者們等著等著,全村最窮,最破的沈家它竟突然就富了起來,而且還越來越顯赫。這事不對呀! ———— 沈見晚表示這輩子她一定彌補前世所有的遺憾,改變那些對她好的人的悲劇,至于那些算計她的讓他們悔不當初! 還有,那個他,那個把她撿回來養大最后又為她丟了性命的那個他,她今生必定不再錯過…… 但誰能告訴她,重生回來的前一天她才剛拒絕了他的親事怎么辦?要不干脆就不要臉了吧。 沈見晚故意停下等著后面的人撞上來:啊!沈戰哥哥,你又撞我心上了! 沈戰:嗯。 ———— 世間萬千,窮盡所有,他愿護阿晚一生平平安安,喜樂無憂。
181.6萬字8.33 135289 -
完結78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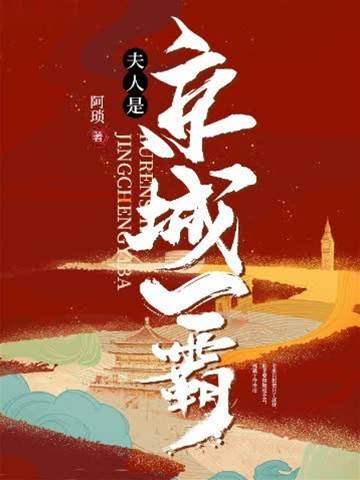
夫人是京城一霸
七姜只想把日子過好,誰非要和她過不去,那就十倍奉還…
123.2萬字8 19066 -
完結109 章

偏執太子的掌心嬌
宣威將軍嫡女慕時漪玉骨冰肌,傾城絕色,被譽為大燕國最嬌豔的牡丹花。 當年及笄禮上,驚鴻一瞥,令無數少年郎君為之折腰。 後下嫁輔國公世子,方晏儒為妻。 成婚三年,方晏儒從未踏進她房中半步。 卻從府外領回一女人,對外宣稱同窗遺孤,代為照拂。 慕時漪冷眼瞧著,漫不經心掏出婚前就準備好的和離書,丟給他。 「要嘛和離,要嘛你死。」「自己選。」方晏儒只覺荒謬:「離了我,你覺得如今還有世家郎君願聘你為正妻?」多年後,上元宮宴。 已經成為輔國公的方晏儒,跪在階前,看著坐在金殿最上方,頭戴皇后鳳冠,美艷不可方物的前妻。 她被萬人敬仰的天子捧在心尖,視若珍寶。
33.7萬字8.18 14518 -
完結942 章

重生我嫁給了未婚夫的死對頭
86.7萬字8 2805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