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愛你》 第154章 陸綰,和我過一輩子吧
言彬說的這些,紀航完全都不知曉,但若仔細想想也並不是完全無跡可尋。
他悔恨,到底還是自己不夠關心子期,如果之前他能多了解幾分,今天這悲劇便不會釀了。
紀航通過言彬的描述,想像著一個孩在做這些事的艱難。
子期去國外不僅要躲避紀小凡的監視,還要面對許多未知的危險,並非那種天不怕地不怕的孩,能做這麼多無非是心中帶著。
再細細回味過去幾年,從與子期相識至今,的所作所為,衡量無力償還,他便更加覺得自己罪孽深重。
一時間,紀航覺被的無法息,那種痛苦就好像正面迎接死亡一般。
「子期。」
紀航只敢在心裡默默念著的名字,因為他覺得現在的他本連的名字都不配提起。
言彬鬆開紀航的領,冷眼相待,「你最好祈禱沒事,否則我一定不會放過你,還有,你給我聽好了,從今天從此時從此刻開始,不允許你再靠近。」
言彬撂下話之後便離開了,他現在必須要去打聽子期到底是什麼況。
紀航慢慢轉,他看著那扇閉的鐵門,它牢不可破,一如現在子期的心。
沒有機會,再沒有機會了。
紀航深吸一口氣,仰起頭看著天花板上的中央空調,一時間酸楚難自抑,他緩緩閉上眼,將眼淚埋藏在了心裡。
後來,許是子期這人生來就命大,又一次從鬼門關被拉了回來。
當時的形足以用「驚心魄」這四個字來形容。
因為在做人流手的過程中大出,命懸一線,庫的量又告急,紀航幾乎用了所有的力量,甚至不惜耗費巨大的人力力從周邊的臨市尋求支援。
Advertisement
當然,紀航覺得自己做的這些本不值一提,因為他永遠都欠子期的,欠的可能是那種用生命都無法償還的債。
*
夜,申城下起了大雨,噼噼的雨聲裹挾著狂風狠狠地打著玻璃車窗,紀航開著車,盯著遠都市的霓虹燈,它們在淅淅瀝瀝的雨里發著落寞而溫的。
他不覺地想起子期的那封信,想到那個親手被他殺死的孩子。
於是,冷的寒意浸上心頭,他覺得眼前的一切開始天旋地轉。
副駕駛座上,手機一直震著,電話是陸綰打來的。
紀航並未理會,他踩著油門加快速度往那個他最不想待的地方開。
到家的時候已經是凌晨一點了,客廳里還留著燈。
紀航停好車,熄了火,然後到翻找,幾分鐘之後,他找到了自己想要的東西。
只見他巍巍地從煙盒裡出一煙,然後哆哆嗦嗦地放進裡,置於兩瓣的薄之間。
啪嗒——
靜謐的空氣中,火機被打開的聲音異常的清脆。
藍的火焰將煙頭燃燒,很快濃郁的煙草味便在狹小的中彌散開來。
紀航用力地吸了一口,尼古丁肺的那一瞬間,會讓人產生一種仙死的錯覺。
他很這種短暫被麻痹的快,似乎心頭繚繞的煩惱在這一刻都可以因為尼古丁迷醉著神經,從而消散。
紀航像是上了癮一般短短十幾分鐘,將近掉了半包煙。
「咳咳——」
許是的太過生猛,他覺到肺部在灼燒,嚨里就像被塞進了稻草,的人難。
在一陣劇烈的乾咳之後,他嘗到了令人作嘔的腥味。
紀航滅掉煙,然後從副駕駛座的暗格里取出一罐啤酒。
咕咚咕咚,三兩口的功夫,酒就喝完了,酒沖淡了腥味,卻帶不走紀航中的苦悶。
只見他用力地扁見底的空罐,然後重重地往擋風玻璃上砸去!
「!」
紀航終於再是綳不住了,他狼狽地趴在方向盤上任由自己的緒發泄。
車外,狂風驟雨肆,車,紀航被囚在痛苦的牢籠里,千千重門,所有悲傷無安放。
一小時又一小時,當紀航回到別墅的時候已經是凌晨三點。
推開門,他便看見躺在沙發上正在小憩的陸綰。
聽到響,陸綰立刻醒了過來,手了惺忪的睡眼,言語之間還帶著幾分睏倦,「你回來啦,抱歉,我睡著了,剛才一直打你的手機都打不通。額,吃過飯了嗎,廚房還煨著湯,我去幫你盛一碗吧。」
陸綰起,因為作太快,結果有些暈眩,強烈的不適讓再度坐回到沙發之前。
紀航沒有上前,也沒有說話,他就這麼看著陸綰,一直看著。
過了一會,陸綰緩過神來,主走到紀航面前,看到他肩頭殘留的雨滴,於是關心地問道:「怎麼淋雨了?冷不冷,要不要去泡個澡,我去替你放水吧。」
陸綰把妻子這個角詮釋的非常到位,不僅微,而且獨立自強,長相也可以說非常不錯,這樣的人哪個男人不。
可紀航現在看見就有一種想逃離的覺,沒錯,是逃離,他好像對這個人到了已經連討厭都討厭不起來的地步了。
他不止一次的想,如果人生可以重來該多好,如果他沒有遇見陸綰該多好?
可是,人生哪裡來的那麼多如果。
陸綰正轉離開,紀航立刻住了,「等等。」
「嗯?怎麼了?」
陸綰眉眼之間帶著笑容看著紀航,「有事嗎?」
「…」
紀航不說話,他就這麼看著陸綰,目不轉睛,神專註,給人一種意綿綿的錯覺。
陸綰臉紅了,不自覺地低下頭,然後小聲地說了一句:「為什麼這麼看我。」
紀航還是不說話,他在想什麼旁人本無法預知。
就在陸綰抬頭準備再度詢問的時候,紀航突然開口了,他說了一句讓可能這一生每每只要回想起來都會甜進心裡的話。
但在經歷過一些事之後想起來又痛不生的話。
紀航對著陸綰突然說:「和我過一輩子吧。」
嗯,話沒有錯,是過一輩子。
紀航說完這句話也不管陸綰,越過直接就上了樓。
他走進浴室,將門反鎖,然後打開水龍頭,將浴缸放滿水。
眼下是寒冬,屋雖然有暖氣,但即便這樣也沒有辦法抵的過刺骨穿心的涼水。
紀航長一,走進浴缸里,他就這麼穿著服泡進冷水。
嘩啦啦~
潺潺的水聲不停地拂過耳邊,浴缸里的水早已經漫了出來,流淌的到都是。
陸綰拍門的聲音不停地由外向里傳來。
紀航沒有理會,他就這麼任由自己在水下那種無法呼吸的窒息。
為什麼要這麼自,因為他覺得只有這樣,他才能讓自己的心鬆快一些。
從子期送「禮」的那一刻起,紀航就知道他再也不可能挽回了,真的沒有任何迴旋的餘地了。
如果說第一次犯錯還罪不至死,那麼第二次再犯同樣的錯誤那就是死有餘辜。
紀航知道的,所以,他不想再去禍害子期了,他覺得自己本就不配為人,更別說去擁有子期的了。
他的後半生註定是活在痛苦折磨以及對子期的贖罪里。
至於陸綰,紀航已經不願意再把時間和力花在上了,現在的他早已為一隻千瘡百孔的行走,所以和誰在一起又有什麼區別。
正如言彬說的那句話,他娶陸綰就是自己造孽,所以,他一輩子都逃不開了。
「砰砰砰——」
門外,陸綰焦急的拍門聲仍舊持續不斷。
「紀航,你怎麼了?我求你開開門好嗎?」
「…」
「嘩——」
只聽一聲巨大的水花聲,紀航整個人從浴缸里鑽了出來,他一拳重重地打在大理石牆面上,瞬間猩紅的鮮便順著的巖壁流到了地上。
那一刻紀航「死」,被無盡的悔恨萬箭攢心而亡。
終究這一場是曇花一現。
高估他的。
他低估了的。
*
「沒有末路憑目照明,火花碎后更加幸福。」
「重生」后的子期只有一個悟,那就是在有限的生命里,想沒心沒肺地活著。
「吱——」
臥室的門被慢慢地推開,子期合上手裡的書放在一旁,扯了扯上蓋著的昂貴羊毯子,扭頭向窗外。
天空灰濛濛的,今日雨連連,怕是凜冬的雪也將隨之而來了吧。
「期期,該吃藥了。」
紀小凡端著一碗味道濃郁的中藥來到子期面前。
這葯是他親自煎的,自從子期做完人流撿回一條命之後,紀小凡便寸步不離地照顧。
每天,他都會早起親自去菜場買菜,然後回來煲營養湯,五菜一湯,三葷兩素,是他用心對待人的最好現。
撇開,紀小凡做的那些毒的事來說,他本是一個很暖的男孩。
以前在別人上網吧打遊戲、泡夜店醉生夢死的時候,他做的最多的事就是守在家中,伺候生病的母親。
現在對待人,他也是這般的妥帖、細心、無微不至。
「期期?」
紀小凡溫地喚了一句,「這葯醫生囑咐一定要趁熱喝,如果你怕苦,我還準備了糖,還有,今天我做了你最吃的菜。」
子期聞言,默默地回頭,看了一眼紀小凡,語氣寡淡地說道:「你打算什麼時候放我走?」
「不…」
拒絕的話紀小凡口而出,他把葯放在一旁的桌子上,然後半蹲在子期面前,滿眼誠懇地祈求道:「不要走好不好?」
子期笑笑:「嗯?不走?理由呢?你是還想用誰來威脅我嗎?小凡,你覺得我現在除了我自己,我還在乎誰?」
當然這話有點絕對,還在乎言彬,對他那是一種遠遠凌駕於之上,甚至超過親的。
很在乎他。
紀小凡握著子期,他的手很涼,那是一種從骨子裡出來的寒徹。
「期期,我不威脅你了,好不好,我求你,我現在求你留下來。我不能沒有你,真的,我已經離不開你了。」
這話一萬個不假,紀小凡對子期的那是從頭到尾都沒有搖過的。
從第一次見面,這麼多年過去了,他紀小凡的心裡乾淨的容不下除子期以外的任何人。
「我你,我真的你。」
眼淚順著臉頰流進裡,紀小凡嘗到了一種讓他深深懼怕的苦。
「期期,我知道你恨我,但是我真的沒有辦法。那時候,你那麼紀航,我真的被的走投無路了。為了得到你用極端的手段,是我不對,請你相信我,以後我一定會對你好的。」
紀小凡說著說著,這膝蓋慢慢地就了,他甚至拋卻了一個男人該有的傲骨和自尊就這麼在子期面前跪了下來。
「求你!求你!」
紀小凡把頭的很低,他握著的越收越,聲音也變得愈見哽咽。
此時此刻,連殺人都不眨眼的紀小凡竟然會因為一個人變得膽怯懦弱。
他不敢多說話,說多了,就生怕那句說錯了惹子期煩,說了又怕不了解自己的,一句話卡在嚨里,進退兩難。
「…」
子期沒有說話,知道,以紀小凡這麼偏執的格,哪怕逃到天涯海角,他也會追到到窮途末路。
子期一點都自己的後半生過的是那樣的糟心與顛沛流離。
能一頓飯解決的好聚好散,為什麼要搞的那麼累呢?
看著紀小凡眼眶裡的波淋漓,輕輕地嘆了一口氣,然後反握住他的手說:「小凡,我很謝謝你對我的,可你要明白,這世間最不可以勉強的東西它就是。你強留我在你邊,痛苦的是兩個人,與其這樣,不如海闊天空,各自安好。還有,我知道你其實並不壞,你只是被有些仇恨蒙蔽了自己的心。小凡,收手吧,不要再做壞事了。」
子期越是這樣溫和平靜的說話,紀小凡就越是制不住自己的緒。
猜你喜歡
-
完結574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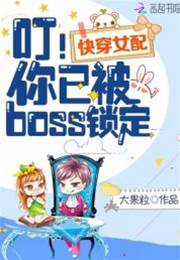
快穿女配之你已被boss鎖定
阮綿綿隻想安安分分地做個女配。 她不想逆襲,也不想搶戲,她甘願做一片綠葉,襯托男女主之間的純純愛情! 可是為什麼,總有個男人來攪局?! 阮綿綿瑟瑟發抖:求求你,彆再纏著我了,我隻想做個普通的女配。 男人步步逼近:你在彆人的世界裡是女配,可在我的世界裡,卻是唯一的女主角。 …… (輕鬆可愛的小甜文,1v1,男主都是同一個人)
103萬字7.83 14294 -
完結231 章

離婚夜,植物人老公扒光我馬甲
成為植物人之前,陸時韞覺得桑眠不僅一無是處,還是個逼走他白月光的惡女人。 成為植物人之後,他發現桑眠不僅樣樣全能,桃花更是一朵更比一朵紅。 替嫁兩年,桑眠好不容易拿到離婚協議,老公卻在這個時候出事變成植物人,坐實她掃把星傳言。 卻不知,從此之後,她的身後多了一隻植物人的靈魂,走哪跟哪。 對此她頗為無奈,丟下一句話: “我幫你甦醒,你醒後立馬和我離婚。” 陸時韞二話不說答應。 誰知,當他甦醒之後,他卻揪著她的衣角,委屈巴巴道: “老婆,我們不離婚好不好?”
56.4萬字8 19064 -
完結81 章

仲夏呢喃
霖城一中的年級第一兼校草,裴忱,膚白眸冷,內斂寡言,家境貧困,除了學習再無事物能入他的眼。和他家世天差地別的梁梔意,是來自名門望族的天之驕女,烏發紅唇,明豔嬌縱,剛到學校就對他展開熱烈追求。然而男生不為所動,冷淡如冰,大家私底下都說裴忱有骨氣,任憑她如何倒追都沒轍。梁梔意聞言,手掌托著下巴,眉眼彎彎:“他隻會喜歡我。”-梁梔意身邊突然出現一個富家男生,學校裏有許多傳聞,說他倆是天作之合。某晚,梁梔意和裴忱走在無人的巷,少女勾住男生衣角,笑意狡黠:“今天賀鳴和我告白了,你要是不喜歡我,我就和他在一起咯。” 男生下顎緊繃,眉眼低垂,不發一言。女孩以為他如往常般沒反應,剛要轉身,手腕就被握住,唇角落下極輕一吻。裴忱看著她,黑眸熾烈,聲音隱忍而克製:“你能不能別答應他?”-後來,裴忱成為身價過億的金融新貴,他給了梁梔意一場極其浪漫隆重的婚禮。婚後她偶然翻到他高中時寫的日記,上麵字跡模糊:“如果我家境優渥,吻她的時候一定會肆無忌憚,撬開齒關,深陷其中。”·曾經表現的冷漠不是因為不心動,而是因為你高高在上,我卑劣低微。 【恃美而驕的千金大小姐】×【清冷寡言的內斂窮學生】
40.2萬字8.18 483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