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宮熹妃傳》 第56章 榮憂相隨
那廂淩柱一行人也在李衛的引領下出了貝勒府,李衛幫著將東西裝上馬車後方才離去。馬車帶著輕微的晃悠緩緩駛離了貝勒府,伊蘭趴在窗沿上著漸漸遠去的貝勒府不時回頭看一眼堆滿了馬車的各禮,巧的小臉上流出深深得羨慕之,許久似乎下定了什麽決心,對正與富察氏說話的淩柱鄭重道:“阿瑪,等蘭兒長大了也要像姐姐一樣為人上人。”
淩柱一愣,抱過伊蘭讓坐在自己膝上問:“為什麽突然這樣想?”
伊蘭把玩著係著藍帶的發辮一臉奇怪地反道:“阿瑪難道不這樣想嗎?您看姐姐現在過的多好啊,錦玉食,出有人伺候,還給了咱們那麽多好東西,那些緞子好好舒服,比阿瑪上朝時穿的朝服料子還要好。”
淩柱為之愕然,沒料到會有這樣的想法,一時竟不知如何回答,反倒是在一旁啃蘋果的榮祥皺著鼻子吐出兩個字,“淺。”
一聽這話伊蘭立時不高興了,像炸了的小貓,柳眉倒豎喝道:“你說什麽吶?”
榮祥把蘋果啃幹淨後將果核往外麵一扔抹一抹道:“我說你淺,姐姐如今固然是錦玉食,但何嚐又不是關在金籠中的雀,莫說出門了就是見一見親人都難,你沒見著剛才咱們走的時候姐姐有多難過,虧得你還羨慕姐姐,不是淺是什麽。”
伊蘭不以為然地反駁道:“姐姐雖不能出貝勒府,但旁的地方卻無一委屈,甚至還能幫襯著咱們,難道說還是忍凍挨來得更好?”
“話不投機半句多!”兩人哼一聲各自將臉轉到一旁不再說話,淩柱輕拍著伊蘭的腦袋道:“你當真以為你姐姐隻是被限製了自由嗎?”
Advertisement
“那還有什麽?”伊蘭一臉茫然地問。
淩柱歎一歎氣看著富察氏道:“夫人,你有沒有覺著除了淨思居以外,不論我們走到哪裏,仿佛都有人盯著?”
富察氏一臉詫異,口道:“老爺也有這種覺嗎,妾起先還以為是錯覺來著。”
淩柱搖搖頭,著不時被風吹起的車簾,沉沉道:“看來若兒在貝勒府的日子並沒有自己說的那樣好過,一言一行皆被人監視著。”他輕著伊蘭的背道:“風榮華之背後是旁人難以想像的刀劍影與生死相向,每一皆是殺機四伏,稍有不甚就會落得一個碎骨的下場,從此萬劫不複。隻怕你姐姐在貝勒府的每一個夜晚都不曾真正安枕無憂過。” 說到此他長歎一聲仰臉道:“若然可以,阿瑪寧願你姐姐從未與皇家有過集,茶淡飯過著寧靜淡泊的日子。”
伊蘭嘟了小不悅地道:“阿瑪嚇唬人家,哪有您說的那麽可怕。”
淩柱憐惜看了一眼道:“你現在還小,很多事都不懂,等將來長大了自然會明白。”
伊蘭不以為然地撇撇將目轉向細雨漣漣的車外,隨著馬車的轉彎,隻能看到貝勒府飛簷卷翹的一角,然那份厚重的奢華早已深深刻腦海,抹之不去。
彼時,朝雲閣中,年氏正閉目倚在貴妃榻上,兩個小侍一左一右蹲在兩邊以玉在其雙上按,榻邊小幾上擱著一座鎏金博山香爐,此刻正焚了上等的百合香,縷縷輕煙帶著令人心怡的輕香自爐中悠悠逸出,於無聲無息間遍布屋中每一個角落。
這百合香以沉水香、丁子香、骨香等二十餘種香料以古法配製而,製之後必須以白相和然後放瓷中再封以蠟紙封住,使其不至於泄了香氣。相傳此古法已經失傳,哪怕是最高明的製香師也調配不出真正的百合香。年羹堯知道妹妹素喜香,不知從何購來百合香殘缺的古方,由京城最有名的製香師研製,終是部分還原了這種古香。
“福晉您是不知道,不知給貝勒爺灌了什麽迷湯,這才府一年都不到呢,就讓家人府相聚,妾當時可是足足等了三年才等到這個機會。更過份的是那頓午膳,不算點心果品,是菜就足足有十二品,招搖至極;嫡福晉甚至還派人送了一隻烤豬過去。”在旁邊宋氏絮絮說著話,言辭間是掩之不去的酸意與忌妒,熬了這麽多年甚至失去一個兒才熬到這個庶福晉之位,可鈕祜祿淩若呢,什麽都沒做,輕輕鬆鬆就與平起平坐,這教如何甘心。
宋氏絞著帕子撇道:“就在他們走的時候妾親眼看到拿了許多東西回去,什麽緞子、首飾、補品,應有盡有,敢咱們這貝勒府就是他們鈕祜祿家的金山銀山。”
“說夠了嗎?”年氏睜開半閉的眼眸,抬手示意綠意攙起來,發髻正中的金累釵垂下一顆小指肚大小的紅寶石,流閃爍,映著眉心金的花鈿可外耀眼。
年氏扶一扶雲鬢,眸漫不經心地掃過忿忿不平的宋氏道:“能讓貝勒爺和嫡福晉抬舉,自是的本事,何需惱怒?你說這麽多無非是希我出手對付。”
宋氏被年氏毫不留點中了心事,訕訕不知該說什麽好,許久才憋出一句來,“妾……妾是替福晉不值,鈕祜祿氏素來自以為是不尊福晉,甚至還毒害了福晉最喜歡的絨球,簡直就是罪大惡極,福晉難道當真要眼睜睜看著氣候?”
年氏咯咯一笑,若無骨的手輕輕搭在宋氏肩上,“知道我生平最討厭什麽人嗎?”
宋氏怔一怔,仰一仰臉,與年氏目不經意錯的那一瞬間子往後了一下,有難掩的恐懼在其中,雖然年氏在笑,但那雙眼冷的像千年不化的寒冰一樣,毫無溫度可言,隻一眼便能將人凍住。
“我……妾……妾愚昧,豈能猜得出福晉……的心思。”想站起來,但按在肩上的那隻手猶如千鈞重,令本生不出一反抗的,唯有結結地說著,雙手死死絞著帕子,扯出一抹比哭還難看的笑容。
宋氏的害怕,正是年氏想要的,伏下在宋氏耳邊一字一句說道:“我最恨的就是心口不一、自作聰明的人。”
此時乃是九月深秋,尚未冬,宋氏卻有一種赤站於冰天雪地中的覺,連都似要結冰一般,耳邊的聲音更如閻王催命,嚇得魂飛魄散,連忙雙膝一屈倚著繡墩跪下磕頭,“妾知錯,妾知錯,求福晉饒恕!”
年氏默然一笑,回坐下後接過綠意遞來的茶慢慢抿著,沉默往往是最好的威懾,因為它會使得別人揣不到心意無從應對。待得一盅抿完方才對跪在地上心驚膽戰的宋氏道:“你以為你那點小心思能夠瞞得過我?哼,簡直就是笑話!”
年氏的這一聲冷哼聽在宋氏耳中猶如晴天霹靂,心撲通撲通狂跳險些從嚨中蹦出來,為自己剛才所存的那點取巧之心後悔不已,可是現在說什麽都晚了,眼淚鼻涕花了的妝容,令看起來像個小醜一樣,然現在的宋氏已經顧不得許多了,爬到年氏腳邊攥著的擺哀求道:“福晉,妾知道錯了,妾下次絕不敢再犯,一定對福晉忠心不二。”
盡管年氏府不足一年,但宋氏對的手段已經領教過,不說淨思居那回,就是宋氏親眼所見的就不止一回,格格嫌送到那裏做冬的料子不好看,去找高管家要換料子,令高管家很是難做。此事恰好被年氏看到,讓高管家去庫中取出準備分派給各位福晉格格的料子,蜀錦、雲錦、荊錦足足有上百匹。
格格還沒來得及謝恩,年氏已經輕描淡寫地命高管家將每一匹錦緞展開來層層纏繞在格格上,待得百匹錦緞纏完之後,格格已經了一個圓球,莫說走路連一下都難,這樣足足在院中站了一夜,無人敢解下布匹,且正好那一夜還下了雨,淋得格格瑟瑟發抖,不斷討饒喊救命,但換來的是毫不留的掌,朝雲閣的下人奉了年氏的命令,隻要格格敢出聲便掌的,直至昏過去。
格格被救醒後大病一場,即使病好後也嚇破了膽,從此變得唯唯諾諾,看到年氏猶如老鼠見了貓,遠遠就饒著走。而年氏的雷霆手段也震懾了所有人,更讓人看清了年家的權勢,府中的那些近百匹料子,不出兩日便有人源源自府外運送進來,且無一不是出自蘇浙兩地的上好綢緞。
宋氏暗恨自己怎麽一時糊塗忘了年氏的手段,可是現在說什麽都晚了,唯有不斷求饒。
年氏嫌惡地瞥了一眼花了妝的宋氏,若非還有用得著的地方,真恨不得一腳踹出去,這副窩囊樣子看了就鬧心,如此一個愚鈍如豬的人也敢在麵前耍心眼,當真是活得不耐煩了。揮手示意隨宋氏一道來的侍扶起後道:“記著你今日的話,若再有言不由衷,我定不輕饒了去。至於鈕祜祿淩若……我自然會好好教教,讓知道不是得了貝勒爺幾分寵就可以為所為。”撥弄著指上的鏤金菱花嵌珍珠護甲冷笑道:“嫡福晉不是讓咱們三日後去清音閣看戲嗎?那咱們就好好看這場戲,別辜負了嫡福晉一番心意。”
鈕祜祿淩若,上回被你逃過一劫,那這一次呢,還能那麽幸運嗎?
這一夜,許多人難以眠……
猜你喜歡
-
完結1099 章
鳳女重生:侯爺夫人要複婚!
前世,許瑾瑜將豺狼虎豹當成了良人,闔府被斬首,自己也落得個葬身火海的下場。最後她才知,那個冷心冷情的人將自己愛到了何等地步。重活一世,許瑾瑜想要馬上上了花轎,跟那人和和美美的過完這一生。可是還冇走兩步,就看到了那人,一本正經的說道。“雖家父與叔父早已有言在先,可婚姻大事並非兒戲,既大姑娘不願,我亦是願意就此解除婚約。”許瑾瑜握緊了自己的小拳頭,眼裡起了一層薄霧,直接噠噠噠的走了過去。“侯爺戰功顯赫,為世人敬仰,理應知道流言不可儘信,現如今又怎可因為流言就要解除婚約呢?”孟敬亭冷心冷情,從未對任何人動過心,可是卻被這眼前的小姑娘給軟了心腸。
131.7萬字8 50226 -
完結77 章

奪金枝(重生)
虞莞原本是人人稱羨的皇長子妃,身披鳳命,寵愛加身。 一次小產后,她卻眼睜睜看著夫君薛元清停妻再娶,將他那個惦記了六年的白月光抬進了門。 重活一次,本想安穩到老。卻在父母安排的皇子擇婦的宴會上,不期然撞進一雙清寒眼眸。 虞莞一愣。面前此人龍章鳳姿,通身氣度。卻是上輩子與薛元清奪嫡時的死敵——模樣清冷、脾氣孤拐的的薛晏清。 迎上他的雙目,她打了個哆嗦,卻意外聽到他的一句:“虞小姐……可是不愿嫁我?” - 陰差陽錯,她被指給了薛晏清,成了上輩子夫君弟弟的新娘。 虞莞跪于殿下,平靜接了賜婚的旨意。 云鬢鴉發,細腰窈窕。 而在她不知道的上輩子光景里—— 她是自己的長嫂,薛晏清只能在家宴時遠遠地看她一眼。 再走上前,壓抑住眼中情動,輕輕喚一句:“嫂嫂。” 【又冷又甜薄荷糖系女主x內心戲起飛寡言悶騷男主】 1V1,男女主SC 一些閱讀提示:前期節奏有些慢熱/女主上輩子非C,介意慎入 一句話簡介:假高冷他暗戀成真。 立意: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
20.2萬字8 39694 -
完結139 章
我以為我拿的救贖劇本
一朝穿越,虞闕成了修真文為女主換靈根的容器。好消息是現在靈根還在自己身上,壞消息是她正和女主爭一個大門派的入門資格,她的渣爹陰沉沉地看著她。虞闕為了活命,當機立斷茍進了一個不知名的小門派。入門后她才發現,她以為的小宗門,連師姐養的狗都比她強…
62.6萬字8.33 16859 -
完結10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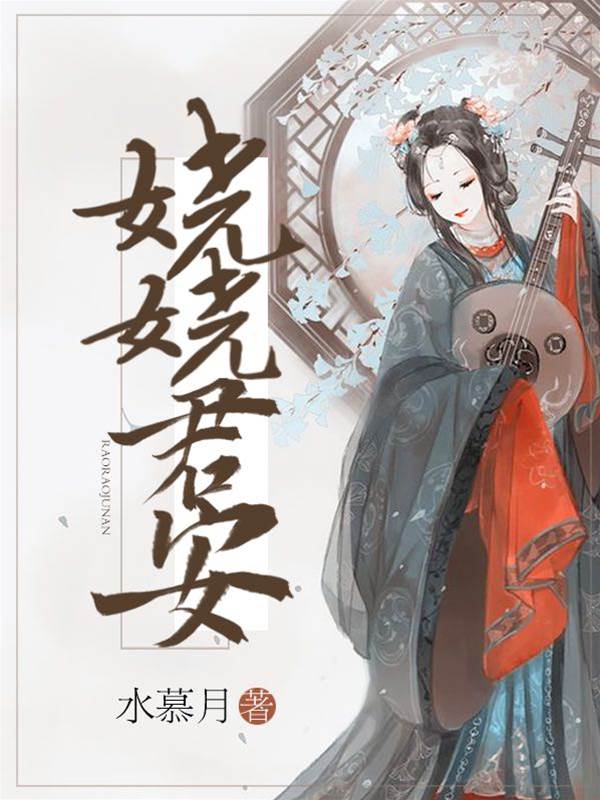
嬈嬈君安
原想著今生再無瓜葛,可那驚馬的剎那芳華間,一切又回到了起點,今生他耍了點小心機,在守護她的道路上,先插了隊,江山要,她也絕不放棄。說好的太子斷袖呢!怎麼動不動就要把自己撲倒?說好的太子殘暴呢!這整天獻溫情的又是誰?誰說東宮的鏡臺不好,那些美男子可賞心悅目了,什麼?東宮還可以在外麵開府,殿下求你了,臣妾可舍不得鏡臺了。
16.6萬字8 1482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