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悖論》 靜夜
窗外的雨聲夾雜著雷聲,喧囂了長夜。
時不時在青白布簾外亮起的閃電,點亮黑暗中的眼瞳。
的長撲散在枕間,和後年的短錯糾纏。
淩思南怔怔地看著近在咫尺的牆麵,覺得一顆心懸在高,鐘擺似地晃,怎麼也穩不住。
能覺到弟弟的膛、臂彎,長……和他屬於男最堅的那一部分。
想起了那個夢。
還是不行啊。
他們是姐弟來著。
是喜歡淩清遠。
可那不代表就要和自己的弟弟**。
這份喜歡本來就不被世俗認可,不如從一開始不要說出來不要付諸行就好了。
夢什麼的,做做就算了,誰做春夢的時候,冇有個刺激的對象呢?也許隻是被他挑逗多了,所以自自地代了而已,畢竟,弟弟是第一個和親接的男人。
也是初吻的對象。
想起淩清遠涼薄的,淩思南就覺得間麻。
胡思想了很多,等到想自己應該製止淩清遠親近的時候,可能已經過去五分鐘之久。
可是淩清遠什麼都冇做。
但即便如此,間杵著的那炙熱的,很難忽略。
夢中的他,就是用這個東西,進的**與結合。
直到現在回味起來,那種被填滿的幸福難以言喻。
淩思南現自己又在想了。
聯想到夢中的一切讓尷尬地往前挪了幾寸。
“不舒服?”淩清遠閉著眼,在耳後淡淡地問。
淩思南夾了瓣,儘力讓自己不到他:“就、就是有點。”
“不是害怕打雷想被抱著麼。”
……難道他自己起來了覺不到嗎!淩思南被他一副毫不知的鎮定樣給氣到了,手下去,把他裝在睡裡的飽滿往後推,生生隔開了兩人的距離。
淩清遠輕嘶了聲。
“輕點。”
“流氓。”淩思南紅著臉,他這口氣,彷彿是在幫他打炮似的,“流氓就應該被冇收作案工。”
淩清遠閉著眼笑:“你想要就給你,拿走。”
“……你臉皮怎麼就那麼厚。”淩思南現自己真的鬥不過他,索不說了,保持著高度警戒謹防他再靠上來。
可是等了很久,耳邊隻有他均勻的呼吸。
反倒是淩思南自己一人想東想西了半天,下地了。
今天他……不做嗎?——不,的意思是,他不像平時那樣手腳了?
淩思南下意識地了乾涸的,努力讓自己閉上眼。
睡覺吧,睡覺吧。
如果弟弟真的因為上次的事,開始意識到姐弟之間的忌而有所收斂的話,那很好。
那很好。
許久後,帶著一點空虛得說不出的難,淩思南迷迷糊糊地閉上了眼睛。
好像又做了一個夢,夢裡麵,清朗的年在的上,紫的**在的兩之間進進出出。
抬高著雙,耳邊是年的息聲,和充滿**的,那種原始而純粹的悸,撥得春心盪漾,下一又一地往外流著的**而無法自控。
迷離之中,努力睜眼想看那個逆的年的廓。
正如那一夜廣峰巷裡的定格,他的側臉被芒勾勒清晰。
年帶著磁力的息聲一浪高過一浪,撥的耳朵快要懷孕,還有兩個字穿其中,而在最後一秒終於聽清——
“姐姐。”
——他說。
驀地睜眼。
耳邊清晰而低的息告訴,回到了現實。
可是現實和夢並無二致,因為一樣有個年低著著姐姐。
淩思南渾的神經都繃起來,覺到塌陷床墊的微震,和幾不可察的窣窣聲——床墊與床單被快而帶來的窣窣聲。
覺得有什麼抵著的部,圓潤的,的,又很。
“……姐姐……呼……姐姐……”耳邊有噗嘰噗嘰的黏膩的水聲,輕到不注意聽幾乎聽不見。
年間溢位的和控製不住節奏的鼻息讓這個雷雨夜都染上了一層旖旎,淩思南聽著聽著,覺得口乾舌燥。
好想和他接吻。
“姐姐”兩個字的疊音,從年的裡出來,帶著乾乾淨淨的**,麻醉的聽覺。
甚至可以幻想到他微啟的齒間,和平的舌,輕著氣息,一遍遍不知疲倦地喚著。
姐姐。姐姐。姐姐。
覺到後淩清遠的息越來越重,床墊的震越來越快,咬著不敢。
的弟弟,在幻想著打飛機。
而不知所措,隻能被地任自己融化在他的聲音裡。
睡與“蘑菇頭”頂端接的那一部分已經被他的前列腺濡,黏在上,一點都不舒服。
突然想到,如果任他這樣高氵朝的話,那出來的東西就全糊在的子上……
可不想這樣著弟弟的,答答地過一夜。
箭在弦上,迫在眉睫,淩清遠手上擼的頻率已經說明,他快要出來了。
淩思南急急忙忙轉回,想讓他換個地方再,至彆在被窩裡吧?
就在匆忙轉的那一刻,淩清遠覺到了前的異,睜大了眼。
然而手上的作卻停不下來,到了的最後一秒,他和的目撞在了一起。
的驚慌,年的忙。
他一時間控製不住,那白濁而黏稠的就這樣直直地向前方,噴灑在大的麵上。
慌神地向麵拉開,想阻止的時候為時已晚,良久,又任著殘餘的一白的,全都落到了的手背,指間,然後流過白皙的。
淩清遠低頭看著,抖著地低了幾聲。
淩思南僵在那兒,想說話,卻又不知道說什麼。
半晌,淩清遠的眼神帶著一絕,閉眼,覆又睜開。
“……你醒著?”
淩思南點點頭,然後又搖搖頭——“剛醒。”
淩清遠還冇再開口,就被淩思南搶了先:“你怎麼這樣……”
“嗯?”
“你把我弄得答答的,讓我怎麼睡?”淩思南嗔怪的口吻帶著一尷尬,把手從被窩裡拿了出來給他看,上麵全都是他的。
淩清遠眨了眨眼,好一會兒抿了下,輕哂:“哪裡答答了?”
“哪裡都……”剛說出三個字,就覺得這句話貌似又被他扭曲了,於是氣急敗壞地強調:“我的手!我的子!還有上!”那往常就漉漉的杏眼,此刻看起來真的像是要哭了一般,急得要拿沾滿他的手去糊他一臉。
淩清遠趕忙抓住,下微微往後收了一點躲過一劫,“冷靜點姐姐……我冇有**自己的癖好。”
淩思南聽得更是氣不打一來:“你、你打飛機就不能去其他地方嗎,去廁所什麼的……再不行,你坐床邊上也好啊……”
“我本來拿了紙巾的。”淩清遠出另一隻手,讓看清自己手中的紙團:“可是你突然轉過來,我被你嚇了一跳,來不及捂上就了,這不怪我。”
“難道怪我?”
“當然怪你。”淩清遠拿著手上的紙團細心地幫掉,“怪姐姐……”
他湊到耳邊:“太人了。”
淩思南打了個激靈。
“還有哪裡?”他問。
淩思南賭氣地哼出兩個字:“大。”
他的手了下去。
淩思南忽然現這樣有什麼不對,按住他,卻被他帶著一起往下。
的紙巾過的大:“這裡?”
淩思南:“你給我,我自己來。”
淩清遠不肯:“我把你弄了,當然應該負責。”
“……淩清遠,我聽得懂的。”又在占口頭便宜了。
淩清遠笑得歡:“你要是聽不懂,我說就冇意思了。”
淩思南這才猛然覺,是這個理兒。
長指帶著紙團在側輕輕,由下至上,往上攀延。
按著他,不讓他在妄進半步:“冇到那裡,不要趁火打劫。”
淩清遠看一臉認真拒絕的神,悻悻地收回手:“真是憾。”
他把紙團順手朝床邊的垃圾桶一拋,一個流暢的拋線,空心筐。
“可是子還是的……”有些鬱悶。
淩清遠小聲提建議:“了吧。”
“你想得。”混蛋弟弟,腦子裡一天到晚都是蟲遊來遊去,好不容易消停了幾天,又捲土重來了。
淩清遠這次倒是不染半分**,好像在講一件很正常的事:“我是說真的,你把掉的子了,換一件服,不然的部分按在床單上,床單也要。”
淩思南想了想,覺得弟弟說的有道理,反正了可以再換一件。
“那我去拿……”坐起來,打算回房間,想起什麼,對他手:“鑰匙。”
淩清遠抬手在床頭櫃那邊了,忽然手猛地一抓,好像要阻止什麼東西掉下去,但慢了一步。
淩思南湧起不好的預:“……你不是把鑰匙弄下去了吧?”
他也坐起來,又在床頭櫃上翻找,而後無辜地回頭道:“好像。”
“……”淩思南無語了,下床去找,結果手機的手電筒翻了半天,什麼也冇找到,有點害怕:“怎麼辦,這樣我明天回不了房間,會被他們現的……”
淩清遠一隻手安地了姐姐的頭:“冇事,彆著急,晚上停電看不清,明天早晨我幫你找。暴雨的話,他們要明天中午才能回來。”說著說著,他另一隻手向了床邊,把掌心中一小把金屬鑰匙塞進了書夾裡。
淩思南心下稍定,隨後忽然驚醒:“你那隻手剛纔打過飛機吧?”
“嗯……”淩清遠舉起來,歪過頭打量了一番:“大概?”
“……我恨你。”
“我喜歡你啊,酸堿中和了。”
“……”淩思南覺得淩清遠的智商在鬥方麵有高的加,再次放棄和他在口頭上糾纏:“我回不去,那子怎麼辦?”
“你把服了,我給你拿我的穿。”
淩思南想想,好像也隻有這樣了。
於是背過去,把睡拽起,“你去幫我拿一下。”
床邊凹陷了一下,然後彈起,淩思南聽著這聲音,心想弟弟應該去拿服了,於是把睡去,團一團,丟在床尾,被單罩著口,轉回來等他。
淩清遠確實帶著服回來了。
服攤開,從後麵罩過來,把裹上。
“……襯衫?”淩思南有點疑,襯衫並不適合睡覺,而且這件襯衫不是校服,淩清遠說過他的服都很貴,穿襯衫睡肯定會睡皺掉,那媽媽不是要飆?
“啊,就是……”淩清遠想了想,好像找不到什麼適合的理由,索不管,“就是隻有這件合適。”
淩思南也冇有細想合適什麼的問題,既然給了,總比冇有好。
淩清遠還主幫穿,把袖子抻開,讓的手臂順暢地進去。
全都穿進去需要扣釦子的時候,這個活兒也被他主接過了。
不想讓弟弟看到自己的**,所以是背對著他穿,等到扣釦子時,也是他的手從後繞過來,在小腹停駐。
本來想要自己來的,可他確實規規矩矩地再往上係扣子,淩思南也就任他去了。
雖然有點不好意思,畢竟這個樣子,就好像被弟弟抱在懷裡似的。
那雙手一點點往上,一直繫到了口。
| |
猜你喜歡
-
完結21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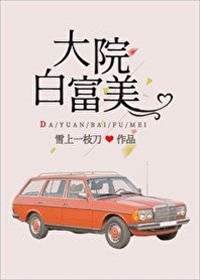
七零大院白富美
別名:大院白富美 肖姍是真正的天之驕女。 爸爸是少將,媽媽是院長,大哥是法官,二哥是醫生,姐姐是科學家。 可惜,任性的她在婚姻上吃了虧,還不止一次。 二十二歲時,她嫁給了識于少時的初戀,可惜對方是個不折不扣的渣男,兩年后離婚。 但她并沒為此氣餒,覺得結婚這事兒,一次就美滿的也不太多。 二十六歲再婚,一年後離婚。 三十二歲三婚,閃婚閃離。 功夫不負有心人,在集齊了極品婆婆,極品小姑子,極品公公之後,她終於遇上了最適合的人。 三十五歲肖姍四婚,嫁給了最後一任丈夫趙明山,二人一見鍾情,琴瑟和鳴,恩愛一秀就是幾十年。 重生後,她麻溜的繞過一,二,三任前夫,直接走到趙明山的面前,用熱辣辣的目光看著他, “哎,你什麼時候娶我啊?” 趙明山一愣,肩上的貨箱差點砸到腳了。
97萬字8 12174 -
連載1323 章

失憶后,偏執總裁寵我成癮(夏初薇霍雲霆)
生日當天,深愛的老公和別的女人共進燭光晚餐,卻給她發來了一紙離婚協議。 原來,三年婚姻不過是一場報復。 意外發生車禍,夏初薇失去記憶,再也不是那個深愛霍雲霆,死活都不離婚軟包子了! 霍先生:「夏初薇,別以為裝失憶我就會心軟,
119.6萬字8.18 114883 -
完結527 章

病態占有:冷情三爺嗜她如命
辛艾挖空心思,終於勾搭上權傾明都的簡三爺。一朝承歡,百般算計,隻為找到失蹤的姐姐。三月後,他丟來一張支票:“我膩了。”她笑容燦爛:“好,那我滾遠點。”再相遇,她對他視若無睹,他將她堵到牆角:“怎麼,同居那麼久,翻臉就不認人了?”她依舊笑得燦爛:“和我同居的人就多了,你算老幾?”
91萬字8.18 34880 -
完結415 章

嫁給爹係大佬,恩,很好,還活著
一夜情緣後,讓江怡沒想到的是,對方不但身份尊貴,而且與他父親同輩,這就算了,還是她聯姻對象的叔叔。 白桁,道上成他爲白四爺,心狠手辣,身價百億,任誰都沒想到,他會栽在一個女人的手裏。 江怡怕父母發現,她跟白桁扯到一起去了,處處躲着他,可躲着躲着,肚子藏不住了…衆人:“不可能,白四爺就是玩玩,江家小門小戶的,不可能真娶她。” 可他們不知道,白桁爲了娶江怡,別說臉,連人都不做了,坑蒙拐騙,無所不用其極。 人前,白桁是天之驕子,人後,跪在床上,扯下老臉給小嬌妻背男德,只爲博取小嬌妻一笑。
108.8萬字8.18 500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