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婚吧靳太太的癡情人設崩了》 第61章 為什麽突然喝酒
沉沉夜裏,一輛低調奢華的跑車在馬路上飛速行駛。
“靳先生,出事兒了,您快回來看看吧!”
吳媽焦急的聲音在耳邊幾乎被擴到了最大,靳承寒一腳將油門踩到了極致,眼裏難得的焦灼不安。
闖了一路紅燈,原本四十分鍾的車程,靳承寒是二十分鍾就趕到。
車子剛一停在南莊,就有傭急忙忙迎了出來:“靳先生,您終於到了。”
“怎麽樣了?”靳承寒一邊問話,一邊大步向樓上走去。
“喝了不酒,一聽到吳媽說要打電話通知您,就又哭又鬧非要自己打給您,現在吳媽帶人正陪著,可還是一直吵著要喝酒,攔都攔不住。”
英的眉頭蹙得越來越,靳承寒鬱著臉,薄抿一言不發,腳下的步子卻生風一般。
Advertisement
主臥的門輕輕掩著,靳承寒一推開門就看到沈言渺站都站不穩,卻還護著酒杯死命往裏灌,吳媽和傭人都快急哭了卻束手無策。
“沈言渺,你瘋了是不是?!”三步並作兩步衝到邊,靳承寒不由分說奪過手裏的酒杯。
他費心費力給找醫生治胃病。
可倒好,這才剛出院幾天就敢喝這麽烈的酒,一喝還是這麽多。
這人真嫌自己命太長了!
酒燒了所有的意識,沈言渺眼前一片混沌,本就認不出人來,抬手就去搶他手裏的酒杯,裏還念念有詞:“你才瘋了,幹嘛搶我的杯子,想喝酒你就自己去拿啊!”
無所畏懼地撒起酒瘋。
拉扯間,不知道是誰先手下一,酒杯哐當一聲摔在地上,應聲而碎。
靳承寒臉瞬間黑得難看,怒不可遏地吼:“沈言渺,你看看,你把自己醉了什麽鬼樣子?”
今天穿了一條霧藍的連長,此刻已經被紅酒染得不樣子,長發淩地垂落在肩頭,一張小臉哭得七八糟,活生生像極了街頭邋遢的流浪漢。
不就是一個福利院?
他靳承寒什麽樣的地皮買不起?
有必要為了這麽一點小事就這麽待自己?
沈言渺被他突如其來的怒吼嚇得瑟了一下肩膀,像是了驚的兔子,水汪汪的大眼睛裏氤氳著霧氣,怯生生地看著他。
一副慘兮兮的小可憐模樣。
“靳先生,您這樣會嚇到的”,看到靳承寒有些發火,吳媽連忙出聲相勸,生怕靳承寒耐心耗盡一走了之。
這就能被嚇到了?
喝醉的沈言渺膽子就這麽小?
靳承寒煩躁地扯開頸間的領帶,幽深的視線卻始終沒從沈言渺臉上挪開:“知道了,醒酒茶留下,你們都下去吧。”
“是,靳先生”,吳媽應聲擱下醒酒湯,領著傭人離開。
眼看一屋子人都走完,隻剩下靳承寒站在麵前,沈言渺有些茫然不知所措地向他:“為什麽們都走了?”
“被你氣走了”,瞪了一眼,靳承寒沒好氣地說。
沈言渺定定地看著他許久,半晌,像了委屈的小孩子一樣告狀:“是們先來搶我的杯子,真的不是我先手的,真的,我發誓。”
保證下得真意切,靳承寒有些無奈地額,這人,喝醉酒就連一點判斷能力都沒有了嗎?
跟這麽一個傻瓜較勁兒,他也真是有夠閑的。
抬手小心地幫撥開在臉頰的幾縷碎發,靳承寒極力嚐試著放語氣:“為什麽突然喝酒?”
而且還把自己醉這副德行。
“喝酒?”
一雙水眸驀然睜得老大,沈言渺頭搖得像撥浪鼓,連連說:“不能喝酒,外婆說過,小孩子喝酒會變笨,不能喝的。”
這都什麽七八糟的。
猜你喜歡
-
完結3579 章

韓先生情謀已久
“收留我,讓我做什麼都行!”前世她被繼妹和渣男陷害入獄,出獄後留給她的隻剩親生母親的墓碑。看著渣男賤女和親爹後媽一家團圓,她一把大火與渣男和繼妹同歸於盡。再醒來,重新回到被陷害的那天,她果斷跳窗爬到隔壁,抱緊隔壁男人的大長腿。卻沒想到,大長腿的主人竟是上一世那讓她遙不可及的絕色男神。這一次,她一定擦亮眼睛,讓 韓先生情謀已久,恍若晨曦,
354.7萬字8 57206 -
完結70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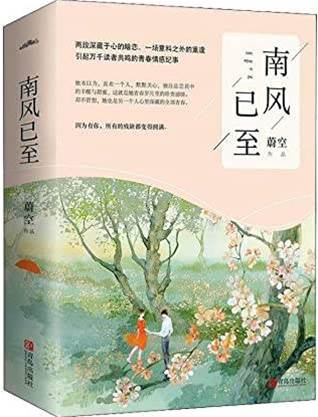
南風已至
——我終于變成了你喜歡的樣子,因為那也是我喜歡的樣子。 在暗戀多年的男神婚禮上,單身狗宋南風遇到當年計院頭牌——曾經的某學渣兼人渣,如今已成為斯坦福博士畢業的某領域專家。 宋南風私以為頭牌都能搖身一變成為青年科學家,她卻這麼多年連段暗戀都放不下,實在天理難容,遂決定放下男神,抬頭挺胸向前看。 于是,某頭牌默默站在了她前面。
22.2萬字8 6582 -
完結491 章

裴教授,你行不行啊
絕世小甜文,年齡差,先婚后愛,1v1雙潔,斯文敗類教授X古靈精怪富家女。劇情一:葉允澄可憐巴巴的看著裴修言:“老公,我作業沒寫完,你跟我們導員熟,你跟她說一聲讓她別檢查作業了好不好。”裴修言抿唇不說話。結果第二天,導員只檢查了葉允澄一個人的作業...下班回家的裴修言發現家空了一大半,葉允澄不見了...
97萬字8 44785 -
完結183 章

乖吝
【甜寵&雙暗戀&校園到婚紗&雙潔&救贖】(低調清冷富家大小姐&痞壞不羈深情男)高三那年,轉學至魔都的溫歲晚喜歡上了同桌校霸沈熾。所有人都說沈熾是個混不吝,打架斗毆混跡市井,只有溫歲晚知道,那個渾身是刺的少年骨子里有多溫柔。他們約好上同一所大學,在高考那天她卻食言了。再次相見,他是帝都美術學院的天才畫手,是接她入學的大二學長。所有人都說學生會副會長沈熾為人冷漠,高不可攀。卻在某天看到那個矜貴如神袛的天才少年將一個精致瓷娃娃抵在墻角,紅著眼眶輕哄:“晚晚乖,跟哥哥在一起,命都給你~”【你往前走,我在身后...
32.4萬字8 9635 -
完結872 章

誘捕玫瑰
五年前,溫棉被人戳着脊樑骨,背上爬養兄牀的罵名。 所有人都說她是個白眼狼,不懂得感激裴家賜她新生,反而恩將仇報。 只有她自己知道,這所謂的恩賜,只是一場深不見底的人間煉獄。 五年的磋磨,溫棉險些死在國外。 重新回來時,她煥然一新,發誓要讓裴家的所有人付出代價。 本以爲這是一場孤注一擲的死局。 卻沒想到,這個將她送到國外的養兄,卻跟個甩不掉的牛皮糖一樣跟在身後。 她殺人,他遞刀,她報仇,他滅口。 終於,溫棉忍不住了—— “你到底要幹什麼?” 而那隱忍多年的男人終於露出了尾巴:“看不出來嗎?我都是爲了你。”
84.4萬字8 210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