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意燃盡:厲先生的小軟糖走丟了》 第26章 她不相信他!
楚修晏一錯不錯的看著近在咫尺的人,近到能看到臉上細小的絨,還有那陣幽然的桃子香。
楚修晏忍不住深吸了口氣,鼻尖不由自主的想要探近。
眼看著危險距離的拉近,溫融的恐懼攀上了頂點!
“嘶——”
楚修晏疼的皺了下眉,卻仍舊沒有放開錮著溫融的手。
隻是不悅道:“還真是牙尖利,屬狗的?”
但他的眼裏卻並沒有半分怒氣。
溫融這一口是下了狠勁,咬的下都發麻。
看著一雙麗到會說話的眸子,楚修晏放輕了語氣,“你別喊出聲,我不會傷害你,放心。”
溫融用力眨了眨眼,那雙睫不是卷翹的,而是原生態的嬰兒睫,細纖長,像是能扇到人心裏去。
他鬆開自己的一瞬間,溫融立馬閃遠離他的懷裏,隔了足足三米遠。
Advertisement
楚修晏低頭看著空了的懷中,那陣桃子香也飄散而去。
保持了安全距離後,溫融才平複好呼吸,盡量不帶緒的質問:“楚這是做什麽?不去招呼客人,卻來洗手間這裏堵我,難不是因為我剛剛罵了小爺,所以你來替他教訓……”
“對不起。”
溫融一愣,沒有反應過來。
楚修晏正對著,鄭重的看著的雙眼,一字一句的再次重複,“溫融,我替修澤的無禮,向你道歉。”
溫融眼神探究的看向他,難以辨別他話裏的真假。
要知道楚修晏這類人,在商界可是被稱為“逐利禿鷲”的資本家,殺人不見的那種,誰知道他不是上一套,心裏又一套呢?
要是真的相信了他,一不小心就會掉進這種人的陷阱裏,死都不知道怎麽死的。
溫融手將碎發到耳後,微笑著回複,“楚言重了,楚小爺先前和我弟弟有些矛盾,所以心裏有氣是正常的,再說了,上次多虧了楚大度肯放過我弟弟一馬,溫融激不盡。”
溫融的話挑不出錯來,客氣疏離,可聽在楚修晏耳朵裏卻分外刺耳。
楚修晏深深看了一眼,便轉離去。
溫融這才算鬆了一口氣,心想得馬上遠離這種偏僻人的地方。
……
來到外麵宴會廳,院子裏甚至搭好了一個下沉式的舞臺,幾個熒屏上悉的藝人,在上麵表演著。
果然權貴麵前,請多大的咖位來都不是問題。
厲政霆已經不在人群的中間,溫融巡視了一圈並沒有發現他,索朝著一邊的休息區走去,從早上出門到現在,一點東西都沒吃,可這時,楚修澤又擋在了的麵前。
楚修澤嘖嘖了幾聲,“我要是你,絕不會來這裏自取其辱。”
聽著他的挑釁,溫融並不會被激怒,隻是對楚修澤這種睚眥必報的人,厭惡了幾分。
“楚,今天是你父親的壽宴,你確定要三番兩次的對客人無禮?”
楚修澤沒想到溫融這種無趣的柿子,今天居然會反駁,於是眼神更加惡毒,“別以為你嫁給了厲哥就有了靠山了,他是屬於我姐姐的!”
說到這裏,楚修澤笑得更開心了,“哦,忘了和你說,下個月我姐就要回來了,到時候你以為厲哥還會要你?”
溫融冷哼了一聲,微抬下,向前走了一步。
“我求之不得,若你現在就能說服厲政霆不要我,我馬上簽字走人,關鍵是,怕是楚小爺沒有這個份量吧。”
楚修澤剛想上前,便看到了自家大哥正在不遠際應酬,但是眼神卻暗含警告的看著這邊,他用手指了指溫融,咬牙切齒的道:“你給我走著瞧!”
……
溫融沒把楚修澤的話放在心上,來到甜品區隨便撿了幾個小蛋糕,端到一旁吃了起來。
隻不過吃的快了些,有些噎,手拿起旁邊的高腳杯往裏送,但是聞到了淡淡的香檳味,就立馬放下了,酒是絕不會再的。
這時,一杯果遞到了的麵前,溫融接過說了謝謝,抬頭便看到了一楚家傭人裝扮的生。
隻一眼,溫融眼神便亮了亮!
猜你喜歡
-
完結367 章

前妻,敢嫁別人試試
三年前,她在眾人艷羨的目光里,成為他的太太。婚后三年,她是他身邊不受待見的下堂妻,人前光鮮亮麗,人后百般折磨。三年后,他出軌的消息,將她推上風口浪尖。盛婉婉從一開始就知道,路晟不會給她愛,可是當她打算離去的時候,他卻又一次抱住她,“別走,給…
95.4萬字8 74666 -
完結11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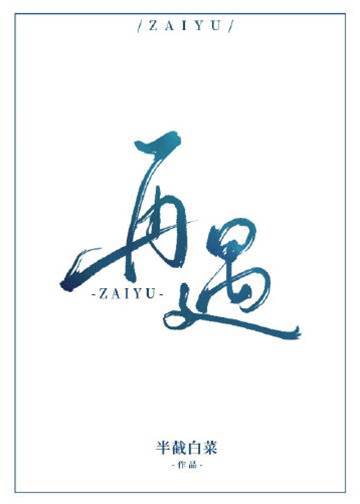
再遇
孟淺淺決定復讀,究竟是為了自己還是為了應浩。她也不知道。但是她成功考上了應浩所在的大學。一入學便得知,金融系應浩正跟金融系的系花談戀愛。-周喬曾說應浩不是良人,他花心,不會給她承諾以及未來。孟淺淺其實明白的,只是不愿意承認,如今親眼所見,所…
38.8萬字8 18890 -
完結641 章
重返七零之空間小辣妻
末世大佬唐霜穿到年代成了被壓榨的小可憐,看著自己帶過來的空間,她不由勾唇笑了,這極品家人不要也罷; 幫助母親與出軌父親離婚,帶著母親和妹妹離開吸血的極品一家人,自此開啟美好新生活。 母親刺繡,妹妹讀書,至于她……自然是將事業做的風生水起, 不過這高嶺之花的美少年怎麼總是圍著她轉, 還有那麼多優秀男人想要給她當爹,更有家世顯赫的老爺子找上門來,成了她的親外公; 且看唐霜在年代從無到有的精彩人生。
121.5萬字8 68733 -
完結2314 章

第一名媛:奈何嬌妻太會撩(盛莞莞凌霄)
“我愛的人一直都是白雪。”一句話,一場逃婚,讓海城第一名媛盛莞莞淪為笑話,六年的付出最終只換來一句“對不起”。盛莞莞淺笑,“我知道他一定會回來的,但是這一次,我不想再等了。”父親車禍昏迷不醒,奸人為上位種種逼迫,為保住父親辛苦創立的公司,盛莞莞將自己嫁給了海城人人“談虎色變”的男人。世人都說他六親不認、冷血無情,誰料這猛虎不但粘人,還是個護犢子,鑒婊能力一流。“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是什麼?”“哪怕全世界的人都說你不好,那個人依然把你當成心頭寶。”
426.6萬字8 3977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