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總要乖,蘇小姐又去滴血認親了》 第398章 愛情史詩
陸景行詫異地仰頭看著蘇染:“什麼孩,什麼是你?”
蘇染一隻手按著他的肩頭,一隻手掐著他的下,聲音從牙裡出來:“十七年前,會做蛋糕的小孩,食客中毒,店鋪被封,舉家遷走,事相似度這麼高,以你的智商會聯想不到一起?那個時候我剛剛七歲,記得不深。你可是十一歲,這麼重要的事,你會不記得細節?”
陸景行眼睛故意瞥向左上方,以表示自己是在回憶而不是撒謊,思索了一下,然後恍然大悟:“你就是拿著搟麵杖幫我把那兩個人趕走的孩?染染,真的是你?”
蘇染想掐他的脖子,又捨不得,用力著他的下:“演,還跟我演?”
馮恆去書房打個電話的功夫,再出來就發現閨和婿掐起來了。
馮浩源聽到聲音也從臥室出來,這才領證姐姐就家暴?
“姐夫,你這是心虛拒絕婚檢,還是被我姐發現你其實是半人馬了?”
馮恆扭過頭:“兒不宜,你回去。記住,家暴不對,無論男,你姐除外。”
馮浩源“哦”了一聲,往後退了一步,繼續扶著樓梯扶手探頭看。
蘇染翻從陸景行上下來:“回屋坦白。”
Advertisement
陸景行乖乖往臥室走。
蘇染抬頭看馮恆:“媽,沒事,就是他小時候淘氣乾的缺德事太氣人。一會兒您要是聽到他的慘聲,不用擔心。尺度絕對在法律允許範圍之。”
馮恆半真半玩笑,勾住蘇染的肩叮囑:“原則問題不姑息不退讓,不是原則問題,別打臉和要害,還要留著自用。”
蘇染:“問題質還要等嚴刑拷打之後才知道。”
陸景行緩步上樓,路過馮浩源時,重重拍了一下浩源的肩。
馮浩源咧笑:“姐夫,借我你那輛16缸Galibier開開,不然我告訴我姐,你這會兒還在笑,本沒有悔改的意思。”
陸景行:“幫我哄你姐,借你開一年。”
馮浩源立刻揚起聲:“姐,姐夫只是犯了一個所有小男孩都會犯的錯誤。小時候我也淘氣把媽的珍珠項鍊拆了兩顆,還是最大兩顆,當雪人的眼睛。丟了才知道那玩意兒有多貴。自此之後好好學習,就為了長大掙錢補回來。”
馮恆早知道是浩源乾的,當時怕他自責,
假裝要揍他,朝樓上揮拳:“我的大溪地黑珍!你知道配一串大小和品相都相當的有多難嗎?”
馮浩源一脖子,跑了。
蘇染押著陸景行回臥室,關上門立刻轉抓住他的睡領:“我家店因為食客中毒被封店,是因為你?”
陸景行點頭:“雖然不是我的本意,我也並不知,但如果你確實是那個拿搟麵杖的小孩,確實和我有關。”
蘇染想把搟麵杖點燃,在燭中把他送走:“其實你早就知道是我了?”
陸景行抿一條線,垂眸睨著:“沒有多早,不到兩年。”
不到兩年,那不就是第一次見到的時候就知道了。
所以在高山週年會上,問的名字,多看了兩眼,引發一連串的蝴蝶效應。
蘇染咬牙切齒:“陸景行,你好樣的,婚期定了,婚服快定製好了,不擔心我後悔了,敢說實話了?”
陸景行:“按照你說的道理,我應該辦完婚禮,儘快跟你一年一胎,然後在你懷三胎的時候,告訴你。”
蘇染氣得把他推倒在床上,傾按著他的膛:“你當我是豬?”
陸景行仰頭看著蘇染笑:“老婆是仙明珠。”
蘇染低頭咬他被自己掐紅的下:“咬死你個豬頭。”
陸景行嘶了一聲,翻反住蘇染:“當時我確實過敏嚴重,是大哥帶我回去的,住院三天,出院後又賴在大哥家裡戴著墨鏡封閉了三天。派人舉報封店的也確實是老頭子,我也去讓人去赤宏縣找過你。除了打聽到你的名字,別的什麼都不清楚。”
蘇染氣歸氣,也理解一切都怨不得他。這小兩年來,他給蘇家的幫助巨大,想來除了這層關係,也有補償的心理。
但他瞞還撒謊,不能原諒。
蘇染呲著牙:“為什麼不早說?”
陸景行埋下頭親:“還記得我很早之前對你說過的話嗎?我說,是我欠你的。我故意在食品展會上,當著你的面前吃含氫化油的桃花,告訴你我的弱點。就是想讓你聯想到之前的事。去赤宏縣的時候,我說那裡有些悉,也是想告訴你。”
“蘇染,我想了很多種不著痕跡的方式告訴你,說自己因為那段回憶不堪回首,所以選擇淡忘,說自己看不到後走,差點被人拐走。但最後我選擇真誠坦白。”
蘇染狠狠道:“詭辯,你就是想分散我的憤怒點!你是不是覺得已經圈住我了,所以無所謂了?”
陸景行親嫣紅的臉頰:“那我圈住你了嗎?”
蘇染瞪他,如果不是打他自己手疼,很想給他幾拳。
陸景行輕輕著的腰,一點點用作試探:“沒想好怎麼回答?那我幫你想。如果我當時和你一起回了店裡,或者我早一些回去找你,我們或許可以青梅竹馬,姥姥也會早早和家人團聚。可惜沒有如果。”
“我一直想和你說句對不起,雖非我本意,但你們顛沛流離的那幾年,確實因我而起。”
“差錯,你們搬來薊城。鬼使神差,你敲了我的房門。因緣隨遲,但兜兜轉轉,我們還是走到一起。”
“老婆,我們錯過了十幾年的相伴,讓我用餘生來彌補,好不好。”
這一聲錯過,這一句餘生,把瑕疵的過去,變了氣迴腸的史詩。
陡然間,蘇染覺得自己的心和已經一起慢慢變。在華麗悠長的故事中淪陷起伏。很快,仰頭“嘶”了一聲。
陸景行勾輕笑,在蘇染耳邊低啞音:“無論如何,你現在已經‘圈’住我了。”
猜你喜歡
-
完結560 章
雲胡不喜
她是出身北平、長於滬上的名門閨秀, 他是留洋歸來、意氣風發的將門之後, 註定的相逢,纏繞起彼此跌宕起伏的命運。 在謊言、詭計、欺騙和試探中,時日流淌。 當纏綿抵不過真實,當浪漫衝不破利益,當歲月換不來真心…… 他們如何共同抵擋洶洶惡浪? 從邊塞烽火,到遍地狼煙, 他們是絕地重生還是湮冇情長? 一世相守,是夢、是幻、是最終難償?
133.3萬字8 6379 -
連載3902 章
女神歸來:七個寶寶超厲害
一場意外,她被家人陷害,竟發現自己懷上七胞胎! 五年後,她強勢歸來,渣,她要虐,孩子,她更要搶回來! 五個天才兒子紛紛出手,轉眼將她送上食物鏈頂端,各界大佬對她俯首稱臣! 但她冇想到,意外結識的自閉症小蘿莉,竟然送她一個難纏的大BOSS! 婚前,他拉著七個小天才,“買七送一,童叟無欺,虐渣天下無敵!” 婚後,他帶著七小隻跪榴蓮,“老婆,對不起,咱們一家子的馬甲都冇捂住……”
689.8萬字8.18 90712 -
完結60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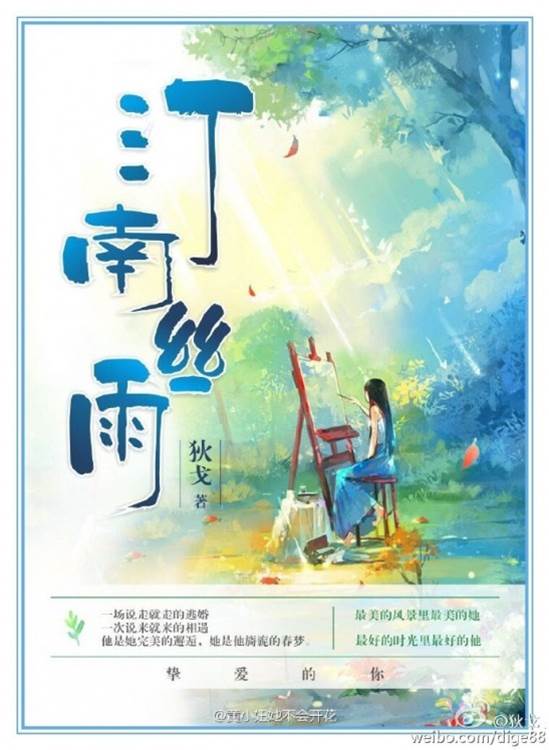
汀南絲雨
通俗文案: 故事從印象派油畫大師安潯偶遇醫學系高才生沈司羽開始。 他們互相成就了彼此的一夜成名。 初識,安潯說,可否請你當我的模特?不過我有個特殊要求…… 婚後,沈醫生拿了套護士服回家,他說,我也有個特殊要求…… 文藝文案: 最美的風景裡最美的她; 最好的時光裡最好的他。 摯愛的你。 閱讀指南: 1.無虐。 2.SC。
16.9萬字8 9132 -
完結516 章

恃寵而嬌
在愛情上,卓爾做了兩件最勇敢的事。第一件事就是義無反顧愛上鄭疏安。另一件,是嫁給他。喜歡是瞬間淪陷,而愛是一輩子深入骨髓的執念。…
89.6萬字8 5584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