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情寵婚:前妻休想逃!》 第四十五章 捏碎她這一身驕傲
晚翎倏然驚醒,尚未看清那男人到底是誰,便一腳踹了過去。
不論是誰,都必然要這麽做。
然而他似乎非常了解,知道會怎樣出招,長一抬便將的製住了。
用力掙了掙,掙不開。
淡淡的青竹氣息,夾雜著冰冷的雨意,包圍了。
耳邊響起男人低低沉沉的笑聲。
他說,“真好奇你的功夫是從哪裏學的,反應夠快,出手也夠辣,倘若換個人,怕是被你踹得斷子絕孫了。”
是湛司域!
晚翎簡直要七竅生煙,知道他邪惡,知道他混蛋,卻沒料到他會如此的狂瘋。
他居然深夜爬窗潛湛寒澍的住所,來欺負,這也太肆意妄為了些。
“湛司域,你趕給我滾!”
“別這麽無,前妻,”他嗓音清越,還帶著一懶意,“倘若我以前知道是你的話,我們早就夜夜同床共枕了不是麽?”
“那又怎樣?錯過就是錯過了,你後悔也沒用,滾!”
“我是不會滾的,這個作業我補定了。”
“你休想!”
晚翎抬手就劈向他的側頸。
很想告訴他,倘若早知道他不是個殘廢,也決計不會嫁給他,又哪裏來的補作業?
Advertisement
大概湛司域的注意力都在防控的上,這一次,被結結實實地劈了一掌。
倘若是個普通人,定會劈暈了,可湛司域的得像鐵。
晚翎劈上去反痛了手,不由得輕呼了一聲。
當然湛司域也痛了,他倒吸了一口涼氣,責備道,“還真是個蛇蠍人,你是準備劈斷我的脖子嗎?”
一掌不,晚翎毫不猶豫劈來第二掌,結果就是雙腕都被他牢牢地攥在了大手裏。
像一條被他掐住腰的鯉魚,心有不甘,但也隻能倔強地扭、幾下。
深深無奈。
於是也歎了口氣。
“湛司域,你就不能放過我嗎?我和你已經無冤無仇了不是嗎?”
“嗬嗬嗬……”
第一次聽到這麽無奈的語氣,湛司域興致然,低低地笑了起來。
他的笑激起了晚翎的怒火,恨恨道,“那夜就該讓你死在大海上!”
湛司域忽而就不笑了。
他輕抵著的額頭,貌似有點約的溫,“最後是不是舍不得我死,嗯?”
晚翎嫌惡地向後仰了仰頭,與他拉開些許距離,“湛先生,你未免太自作多!若不是怕惹上司,我決計不會拖你回來!”
湛司域半天都沒再說話。
他相信所說的,倘若他的死不會給帶來任何麻煩的話,一定視他的命如草芥。
雖然他對也不是,就是想占有,但他至不會傷害,更不會輕視的命,可是一點都不把他放在心上。
人生中第一次遇到這樣一個人,收不來對等的回應,哪怕一點點都沒有。
“你當初為什麽嫁我?”他突然問,“我不相信以你的能力,反抗不了那樁婚事。”
“需要一個份,否則沒有理由回來。”
“你倒是坦誠。”
他冷笑了一聲,倏爾鬆開了。
晚翎迅速將被子卷走,把他一個人晾在外麵。
湛司域倒也沒再強求,仰麵躺在床上,將雙手墊在後腦。
“晚小翎,你回麗城想做什麽?”
“那是我自己的事。”
“想不想和我做易?”
“易什麽?”
“做我的人,我給你想要的一切幫助,不論你做什麽,金錢,權力,名譽……反正除了婚姻,我都可以給你。”
他就是這樣想的。
既然三年前的積怨已消,就沒理由報複了,那麽他想睡到,就得拿利益換。
這是原則。
看得出超級喜歡錢,而他有的是錢,組合起來還登對的。
晚翎在黑暗中諷刺地扯了扯。
果然就不可以高估他的人,他居然可以把始終棄包裝上華麗外,再強拿到別人床上來談判。
與男人做易這種事,對來說不新鮮,也不恐懼,十三歲的時候就把自己的一生都賣給宮慕深了。
“怎麽不說話,我嚇到你了?”湛司域道。
晚翎還是不說話,用沉默讓他滾。
湛司域又道,“你到底還是個小孩,空談什麽明份和,將來你長大了就會明白,那兩樣東西是最無趣的。
婚姻其實也很無味,孩子就更麻煩,倒不如打破枷鎖,活得放縱肆意些。
我向你保證,隻要你做我的人一天,我就把你護在羽翼下一天,沒有什麽是你想得而得不到的。
就算將來你不是我的人了,我也會給你足夠後半生揮霍的錢,這樣不好嗎?”
晚翎冷笑道,“湛先生,你是個終日活在影裏不能見的人,所以就想找個甘願陪你發黴的人,是麽?”
他偏頭看,“你想要名分?那不過是一張紙,隨時都可以燒掉的,要它做什麽?”
晚翎再次冷笑,“雖然我名聲不怎麽好,但想和我做易的男人,還是有很多,不差湛先生你一個。
既然我的選擇有這麽多,那選誰我都不會選你。”
湛司域倏然坐起來,側眸凝視著,“為什麽我不行?”
晚翎翻甩給他一個後背,閉上眼睛,不再理會他。
倘若十三歲那年是他降臨神病院,會選擇他,左右不過是一場易,湛司域或宮慕深,本質上沒有區別。
但現在,隻能是宮慕深了。
至於湛司域,隻想離他遠遠的。
湛司域靜靜地看著,等著的答案,可是等來等去,居然等來了均勻的呼吸聲。
“嗬!”他自嘲地笑了笑。
倒是心大,居然睡著了!
不過此刻,他也的確平靜下來了。
來的時候,他還懷著報複心理,如果在這裏要了,是對湛寒澍以及湛家,最大的辱。
可是來到這裏,看到,就又沒那麽邪惡的心理了,生生把強迫變了談判。
談判還以失敗告終。
他有些喪沮。
淅淅瀝瀝的雨滴打在玻璃窗上,啪啪地響。
想了想,他又重新躺回去,盯著的背影,看得出神。
這麽纖瘦,這麽俏可人,明明看起來很好欺負,卻偏偏屢次都欺負不來,甚至還反被暗算到。
他就從來沒遇到過這麽丟臉的事。
越想越是惱怒。
不就是個人麽,還能是他啃不下的骨頭?
欺負完,再甩一臉錢就是了。
他抬起手便去掐的脖子,想要將扯過來,就像把一朵鮮豔的玫瑰花一瓣一瓣摧殘掉,碎這一驕傲。
如是想著,他果斷掐了下去……
猜你喜歡
-
完結1170 章

早好霍同學
一天,於桑知收到男同學傳話:“風哥叫你放學後去北門小樹林!” “風哥”即霍風,他逃課打架成績吊車尾,是校內大名鼎鼎的壞學生! 突然被他傳喚,於桑知害怕了整整一天。最後冇辦法,隻能求救班主任。 於是放學後,班主任提著掃把殺到小樹林,揪出霍風……一頓胖揍! 班主任:“臭小子!我們班的優秀生你也敢警告!欺負到你爸頭上來了,看我不打死你!” 霍風:“誤會!我隻是想追她!” 班主任:“你憑什麼!你個學渣!辣雞!臭蟲!” 霍風:“……”擦,親爸? * 若乾年後,於桑知穿上婚紗,對閨蜜說,“我老公以前是校霸。他說,他認識我的第一天,就被公公打了一頓,公公還警告他彆耽誤我考清華。” 閨蜜:“這麼慘?那後來呢?” 於桑知:“後來,他也考了清華。”
264.3萬字8.18 9357 -
完結93 章

退婚后,前任小叔親她上癮
【清貴腹黑機長+京圈太子爺上位+先婚后愛+爹系老公+甜寵】未婚夫商瑾之為了白月光,在婚禮現場拋下明黛,還把她當替身。 出于報復心理,明黛誘惑商瑾之小叔,商嶼,“做嗎?” 傳聞中矜貴禁欲的京圈太子爺出奇好撩,“你不后悔就行。” 一夜風流后,商嶼卻提出娶明黛,“你嫁給我,報復力度更大。” 明黛原以為各取所需的婚姻,商嶼送房送車送頂奢,陪她手撕渣男,打臉白蓮花堂姐。 深夜里,高冷的他又變得粘人精,控制狂。 “你昨晚沒抱著我睡覺。” “說好每天親三次,今晚你還沒親我。” “你和別的男人去喝酒,我很生氣,你快哄我。” “不準看別的男人,視頻里男人的身材都沒我好,你摸下。” ...... 明黛忍受不了沒有自由,離家出走鬧離婚。 商嶼逮住明黛押回家,狠狠懲罰,“你還逃不逃,離不離婚,喊老公。” 接下來好幾天,明黛都腫著紅唇,扶墻走路...... 后來,商瑾之發現早愛上明黛。 他腸子都悔青,拽住明黛不愿撒手,“我們重來好不好?” 身后人神情陰鷙,醋意十足,“不好,她是你的嬸嬸。再騷擾她,我打斷你狗腿。”
19.7萬字8 12180 -
完結6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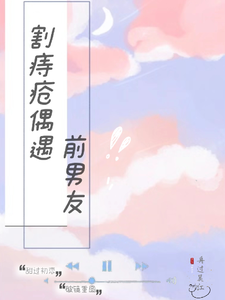
割痔瘡偶遇前男友
新作品出爐,歡迎大家前往番茄小說閱讀我的作品,希望大家能夠喜歡,你們的關注是我寫作的動力,我會努力講好每個故事!
15.5萬字8 60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