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不乖,佞臣替人養妹被逼瘋》 第48章 本督瞧上你了?
祁桑的回答幹脆利落:“我不會。”
“無妨。”
謝龕將茶杯擱下了,回頭對不夙道:“去將那嫌犯的手砍下來,本督好好欣賞欣賞這雙男子的手究竟哪裏與眾不同,還能彈得如此婉轉纏綿的曲子。”
“謝、龕!!!”祁桑攥雙手,咬牙一字一頓地他的名字。
不夙繃了好一會兒的神經啪一聲斷了,恨不能此刻自雙耳聾了算了。
他立刻跪了下去。
沉默在空氣中蔓延。
僵持了許久,終還是祁桑先妥協了。
沒什麽好同這畜生講的,來此就是妥協的。
院子裏早已放置了一架古箏,雙手麻木地落於箏弦之上,閉著眼彈一氣,隻想著手下的弦是謝龕的筋,恨不能一一給他拽斷了。
或許是想得太過神,不留神間,竟真生生勾斷了一弦。
刺耳的聲音劃過夜。
睜眼,看一眼指間上好的金蠶琴弦,心中頓無限淒涼。
彈琴之人,本該敬重每一把好琴的,可如今,不論是古箏還是古琴,在手中都了工。
師父若還活著,怕是要狠狠給兩戒尺。
Advertisement
心中不平靜,強著恨意怒火,糟踐了一把好古箏,謝龕也不同計較,隻問道:“用過晚膳了麽?”
祁桑手在弦上,冷笑道:“事已至此,總督大人也不必假惺惺地一副好人做派了,有話直說便是。”
“去備晚膳。”謝龕說。
不夙應了聲,忙退出了寢殿。
謝龕轉而又看向祁桑:“你倒是聰明,本督耐不好,這個固侯若再不知死活地糾纏你幾日,怕是沒那個命再回戰場了。”
“多謝總督誇讚,我不止在固侯那裏聰明,我還知曉總督你應該是瞧上我了,若真單純為了那所謂的寶藏,如今的我大約同沈吉一樣在牢獄裏刑了,幾日酷刑便能撬開的,總督這樣聰明的人,自不會大費周章地同我玩什麽循序漸進的把戲。”
這話說得直白,既不見被喜歡的欣喜,也不見破他人心思的得意洋洋,仿佛在說一件同自己毫無關係的事。
謝龕來了興致,起走到麵前。
兩人之間連半步的距離都不剩。
他自上而下地瞧著漉漉的眼睛,涼涼反問:“本督瞧上你了?”
“總督若想否認大可……”
Advertisement
“不否認。”
謝龕說:“祁桑,你說得沒錯,本督的確是瞧上你了。”
祁桑闔眸,忽然深深吸了一口氣。
一瞬間,仿佛心如死灰。
心中有所猜測是一回事,被板上釘釘地認下了,又是另一回事。
就好像知道自己會死是一種覺,真被拉上刑場砍頭的時候,又是另一種覺了。
努力平複好了緒,才抬頭看向他:“然後呢?總督打算同我玩多久?你該知道我不是個安分的,隨時都會招惹一些不該招惹的人,留下一個個爛攤子,你一個收拾不好怕是要惹火燒。”
謝龕俯,長指勾了幾微涼順的在指間撚著。
“是會麻煩一些,不過無妨,這肋有了便有了,本督以後走哪兒都帶著你,盯得了,麻煩自然也會一些。”
祁桑直接給氣笑了:“日日帶著,你就不怕走著走著,或是睡著睡著,突然就被我一劍刺死了?”
“好啊,本督親自教你劍,免得你連心口在哪裏都分不清,刺偏了可就白白浪費了機會。”
咬出最後一個字來時,謝龕的齒也咬上了的耳骨。
同那夜一模一樣的位置,似是嫌棄齒痕消了,再重新給補一個。
祁桑渾一抖,許多記憶洶湧撲腦海,恐懼淹沒理智,力將他推開:“別我!”
月那樣黯淡,依舊掩不住眼底的厭惡與憎恨。
謝龕卻並不在意。
他要的是的人,隻要在他眼前就行,是高興是傷心都無所謂。
“晚膳來了,先用膳。”他說。
祁桑自是沒什麽胃口,隻把自己當木頭杵在那裏。
謝龕食素,晚膳備的都是清淡爽口的素菜,他夾了脆筍放到麵前的碗裏,道:“來都來了,就別繃著個小臉給本督瞧了,左右早晚都是要吃的,你總不是打算要死在這總督府。”
祁桑沒說話,甚至沒有去看他或那竹筍一眼。
的注意力在院子裏那棵半死不活的花樹苗上,想起先前同奉業一起將他種下,又想起奉業死前的淒慘模樣,難免心中淒然。
“若那日沒有曹四周他們。”
忽然問道:“若奉業回來了,你會殺了他嗎?”
辦事不利之人,要了何用?養在總督府好看的麽?
那夜便是奉業回來了,下場也不過是死得好看些,最終還是會被一張草席卷了丟城外葬崗去的。
謝龕落下的目不不慢地掃過失魂落魄的小臉,道:“自是不會,本督是那種濫殺無辜的人麽?”
祁桑似是冷笑了一聲:“你是不是那種人,還要問我嗎?”
而,如今同這棵要枯死的花樹沒什麽區別,哪怕還勉強活著,最終結局都免不了一死。
表實在喪氣,好像用完這個晚膳就要被拉出去砍頭似的。
謝龕終於歎了口氣,放下碗筷將不夙了進來:“去備幾樣葷食送過來。”
不夙一怔,下意識道:“可是府中並沒有食材,若要出去采購怕是要耽擱一段時辰。”
“不用了。”
祁桑忽然道:“晚些時候待接回了扶風,我帶他一道出去吃就好。”
不夙拿不定主意,沒敢貿然出聲。
謝龕:“本督有說過你可以接回他?他一個嫌犯……”
“主犯是我。”
祁桑忽然起,一腳用力將座椅踹了出去。
或許是想起了奉業的慘死,也或許是兄長的埋骨他鄉,亦或是大理寺獄那生不如死的半個時辰徹底抹去了生命中最後的一點亮。
緒忽然就發了,憤怒、憎恨、怨懟……
那些激烈的緒撕扯著理智,祁桑口急劇起伏著,不顧死活地開始發瘋。
猜你喜歡
-
完結228 章
將門嬌
大盛朝邊疆狼煙起,鎮國將軍一家五子慨然赴陣,隨時都可能爲國捐軀, 臨行前,老太君淚求聖旨,要替五郎求娶傳說中特好生養的安定伯府崔氏女,以求一槍命中,開花結果. 安定伯府有女兒的,不是裝病就是玩消失,只有崔翎覺得這是門好親—— 門第高,沒人欺;賊有錢,生活水平低不了;又是小兒媳,不擔責任日子好混; 沒有三年五載回不來,樂得清淨;要是丈夫不幸了,那就是烈士遺孀,享受國家補貼的! 這對勾心鬥角了一輩子,今生只想安安穩穩過養老日子的她來說,**太!大!了! 一片混亂中,崔翎淡定開口,"我嫁!"
61.5萬字8.18 54973 -
完結328 章

全能小毒妻
她是21世紀天才神醫,一朝穿越靈魂誤入架空大陸。 斗渣男,虐白蓮,解謎題。豈料遇到腹黑太子爺。打不過,跑不掉,還漸漸遺失了心。 “爺,奴家只想一生一世一雙人!您身份高貴,不約不約。” 他邪魅一笑:“天下,權位,都不及你半分!”
61.2萬字8 77760 -
完結1510 章

醫妃萌寶,逆襲成凰
【虐渣爽文男強女強團寵萌寶隨身空間】醫學天才溫錦,意外穿越到花癡醜女身上,醒來就是洞房花燭夜。 「王爺,你聽我解釋,我不是……」 好疼! 想哭! 原主就是個顏狗舔狗,竟然招惹了暴躁癥王爺,小命都作沒了。 好在她有醫術在手,前世的胎記竟然跟她一起穿越,變成了隨身靈泉空間! 被棄六年後,華麗變身的溫錦帶著萌寶走出冷院,手撕白蓮,痛扁綠茶。 撩什麼男人?獨美做個富婆它不香嗎?溫錦帶著萌娃,治病救人賺銀子。 醫治瘸腿大哥,鼓勵哥哥做大官。 沒有金大腿,靠著金手指咱也能成為人生贏家! 唉,不對,這個又帥又撩的王爺怎麼老糾纏她?說好的冷清疏離,兩看相厭呢?
409.6萬字8.33 1047824 -
完結19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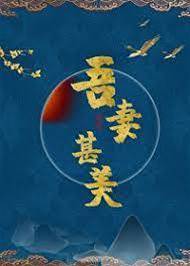
吾妻甚美
昭虞是揚州風月樓養的瘦馬,才色雙絕。 誰知賣身當天風月樓被抄了個乾淨,她無處可去,被抄家的江大人收留。 江大人一夜唐突後:我納你進門。 昭虞搖頭,納則爲妾,正頭夫人一個不高興就能把她賣了,她剛出泥沼,小命兒得握在自己手裏。 昭虞:外室行嗎? 江大人:不行,外室爲偷,我丟不起這個人,許你正室。 昭虞不信這話,況且她隨江硯白回京是有事要做,沒必要與他一輩子綁在一起。 昭虞:只做外室,不行大人就走吧,我再找下家。 江大人:…… 後來,全京城都知道江家四郎養了個外室,那外室竟還出身花樓。 衆人譁然,不信矜貴清雅的江四郎會做出這等事,定是那外室使了手段! 忍不住去找江四郎的母親——當朝長公主求證。 長公主嗤笑:兒子哄媳婦的手段罷了,他們天造地設的一對,輪得到你們在這亂吠?
28.4萬字8 22367 -
完結315 章

攬芳華
京城落魄貴女馮嘉幼做了個夢,夢到了未來的當朝一品。 醒來後,發現竟然真有其人,如今還只是大理寺裏的一個芝麻小官。 她決定先下手爲強,“劫”走當夫郎。 北漠十八寨少寨主謝攬,冒名頂替來到京城,潛伏在大理寺準備幹一件大事。 沒想到前腳剛站穩,後腳就被個女人給“劫”了。
48.7萬字8.18 8395 -
完結193 章

榻上歡:冷麵攝政王索取無度
昭國太後蘇傾月是寧國公府自幼被抱錯的嫡女,可是大婚之夜,先帝駕崩,攝政王慕瑾辰入了她的洞房。他們立場敵對,目的相悖,他給予她所有的冷酷,漠然,卻又在深夜,抵死糾纏。密不透風的深宮牢籠之中,她清醒地掙紮,沉淪,期盼與絕望中輾轉,本想一走了之,卻又被慕瑾辰緊緊攬進懷裏,訴說著從不敢期待的情意綿綿。
35.4萬字8 1415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