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執暴君又把他的小嬌嬌寵廢了》 第一百一十章 狗阿無
燈會結束已經很多日了,陳坐在塌上發呆。
想到那晚完和雅說的話,第一次見完和雅猶猶豫豫,結的說宴哥哥不想讓你知道。
但想知道,想知道自己的存在到底給他帶來了什麽。
何舒明,十五也不說,隻能從下手。
他們三個常在一塊兒,肯定知道點。
確實,從完和雅口中,得知了三件事。
第一,這個前朝溫寧公主已經引起很多人的不滿了。
大陳的老臣們不滿是因為‘認賊作父’,他的臣子們不滿因為‘禍國妖妃’。
第二,陛下已經到了必須要立皇後的地步,不能再拖了。
第三,他需要一個太子。
陳清楚的知道,是導致這三點沒有辦法實現最大的原因。
他頂著力留下,閉眼不聞,又能拖到什麽時候呢。
突然腰間被人環住,悉的氣息包裹,陳笑出來轉摟住他,“阿無。”
“不早了,走吧,沐浴休息了。”
“你沒有事要辦了嗎,今日這麽早。”
“嗯。”
祁宴點了點頭,派人都送去給何舒明了,他能有什麽事。
現在最大的事就是盤算今晚怎麽喝鴿子湯。
褪去外後,被抱溫水中,陳歡騰的像隻小鴨子。
趴在池邊,勾住他的手來回晃。
他蹲在池邊,一手被牽住,一手整理垂在水中的長發。
Advertisement
的黑發養的很好,長年細心打理,垂順又細。在手中纏繞,打了他的袖口。
發梢染上淡雅的清香,披在肩頭溫順。
即便最初那段日子,他還是往長歡殿裏塞了常用的油。
若是了影響,豈不可惜。
“阿無。”
陳墊腳,親上他的。
猶如水中歌唱的鮫人,捕來往的漁民,一點點拽著他水。
祁宴知道的壞心思,隨著。
墜水中後,他的手護住了的後腦勺。
背到池底,陳下意識的唔了聲,嗆了兩口水,被人立刻抱出水麵。
又不會又折騰,祁宴無奈的拍了拍的背,小雀雀鑽進懷裏,埋頭不了。
“阿無。”
除去,何其依賴他。有他在的腦子都可以丟到十萬八千裏外,笨的自己都吃驚。
自己怎麽能蠢這樣,陳都不懷疑自己沒他本活不了。
“嗯?上去吧,別涼了。”
“那你親親我。”
的手指到左臉上,祁宴笑了下,俯親上。
“可是,右邊會不高興的。”
他用力親上右側的臉,陳呀了聲,的一團。
抱住他的脖子,撒的上了上去。
“心肝。”
耳邊傳來他低沉的聲音,連帶著歎息聲,似乎無奈,包容又寵溺,陳沒出息的紅了臉。
更沒出息的趕應了聲,認下了這句心肝。
有小月在,將一臉哀怨的他趕了出去,不許他幫著換裳。
等穿好服後才坐進他懷裏,讓他幹頭發。
祁宴接過巾,想起第一次給頭發。
半天也幹不,靠在懷裏睡著了。他煩極了,隨便的來回,不停的用巾著。
等到醒,頂著一頭,功的給人氣哭了。
最後還是他幫著重新洗好,在手心裏一點點的幹,才給人哄好。
從那以後,他才知道,頭發都是用巾幹的,曰其名不傷頭發。
想著他不免覺得好笑,陳看到他勾,不解的問,“你笑什麽?”
“沒事。”
想笑因為頭發這種小事抹眼淚,但說出來怕有人要生氣,還是算了。
這項活計,他至幹了得十年,悉的不能再悉。
陳在他懷裏尋了個舒服的位置靠好,等著他將頭發幹。
等著等著就犯困,摟住他的腰閉上眼小瞇一會兒。
好一會兒,四無聲,也覺不到他在頭發,自己倒像是被抱著往下走。
陳迷茫的睜開眼,對上他垂下的眼眸裏一副幹壞事被抓包的樣子。
迅速的被人放進了悉的地方。
“狗!阿!無!你還沒拆掉啊!”
金籠子的小門啪嗒一聲合上,陳氣到冒煙。
還什麽頭發,氣都能氣幹了。
趁著犯困,他又給弄下來了。
“你是不是有什麽癖好啊,這有什麽好玩的?”
他傻不兮兮的蹲在麵前,親親的臉,也不說話。
時不時的手,真像養了隻小鳥。
“明日何舒明給你弄隻真雀鳥不行嘛!”
“不要,朕就想養隻。”
好悉的話,陳白了他一眼,一屁坐進的墊子裏。
他必是有什麽病,幸好現在不帶鏈子了。
“朕有個禮要送。”
祁宴站起,走到桌上,將盒子裏什麽東西倒在了手心裏,然後握住手重新蹲在麵前。
陳好奇的向前挪了兩步,“什麽啊?”
看著他的表,咬牙,“你要讓我猜在哪隻手,我就咬你!”
又被人抓包了,祁宴老實的將手進袖口裏,好一會了出來。
他右手手腕上帶著個金的小環,沒有任何圖案,隻是細細的一條。
那條環上還順著垂下了長長的金鏈子,垂落在地上,看著很長的樣子。
上頭隔著距離還嵌著亮閃的寶石,不知道是什麽奇特的工藝,搖晃時有鈴鐺叮嚀。
陳不解的從地上撿起另一頭,他從不喜歡帶這種東西,而且說好是給的禮呢。
順著鏈子索到另一頭,陳才知道是什麽樣的‘禮’。
“所以這一頭是給我準備的?”
大狗點頭,一臉快試試的雀躍。
陳歎了口氣,盤坐下,著手指如同街邊的神。
“我七歲那年,陛下十一歲了。我今年十九歲,陛下也該二十又三了。您覺著好嗎?啊?”
“好。”
祁宴湊近,再一次親了親鼓起的小臉。
毫不客氣的拉著的手,扣上了小環。
兩人間被一條長鏈子相連,鏈子做的長,行上沒有任何阻礙,隻是不能相隔太遠距離。
陳抬了抬手,開口三次都嫌棄的沒能說出話。
以為之前的那條銀鏈子已經是最無語的禮了,沒想到還有一條。
“你就送我這個禮?我還期待了半天呢。”
“朕何時說送給你了,是送給朕的。”
“我能咬死你嗎............”
他像是被滿足了,搖晃了許久鏈子,侵過來又親。
陳哎呀了聲,又覺著這樣的他可,又覺著無奈。
環住祁宴的脖子,點了點他的鼻尖,“小阿無好稚,是我把你拴牢了。”
他溫暖的呼吸噴灑在麵前,陳心了,每晚都能被他勾了去。
清雋的眼眸被的倒影填滿,全然是。
親了下他的鼻尖,他/倒的附上,“,嫁給我吧。”
不是為祁國皇帝的皇後,是為他祁宴的妻子。
眼眶酸,陳不想在這哭,也不願打破現在的好。
手拉他躺在邊,“你娶過我啦,我的蓋頭是你掀的。”
“好啦我有點困,我今天都送了你一個禮,你要讓我早點睡。”
說完閉上眼,就要睡著的樣子。祁宴眨了下眼,沒明白過來。
似拒絕,又不似接。
或許真的已經娶了?
想不明白,他索幫蓋好被子,熄了蠟燭。
黑夜中,陳眼角強忍的淚珠滾落。
落枕席裏,不見蹤影。
*
(陳:後老公從狼了狗,換了種,怎麽破,在線等,急。)
猜你喜歡
-
完結940 章

農門長嫂富甲天下
倒霉了一輩子,最終慘死的沈見晚一朝重生回到沈家一貧如洗的時候,眼看要斷頓,清河村的好事者都等著看沈家一窩老弱病殘過不了冬呢。 她一點都不慌,手握靈醫空間,和超級牛逼的兌換系統。 開荒,改良種子,種高產糧食,買田地,種藥材,做美食,發明她們大和朝見所未見的新東西……原打算歲月靜好的她一不小心就富甲天下了。 這還不算,空間里的兌換系統竟還能兌換上至修仙界的靈丹,下到未來時空的科技…… 沈見晚表示這樣子下去自己能上天。 這不好事者們等著等著,全村最窮,最破的沈家它竟突然就富了起來,而且還越來越顯赫。這事不對呀! ———— 沈見晚表示這輩子她一定彌補前世所有的遺憾,改變那些對她好的人的悲劇,至于那些算計她的讓他們悔不當初! 還有,那個他,那個把她撿回來養大最后又為她丟了性命的那個他,她今生必定不再錯過…… 但誰能告訴她,重生回來的前一天她才剛拒絕了他的親事怎么辦?要不干脆就不要臉了吧。 沈見晚故意停下等著后面的人撞上來:啊!沈戰哥哥,你又撞我心上了! 沈戰:嗯。 ———— 世間萬千,窮盡所有,他愿護阿晚一生平平安安,喜樂無憂。
181.6萬字8.33 135289 -
完結78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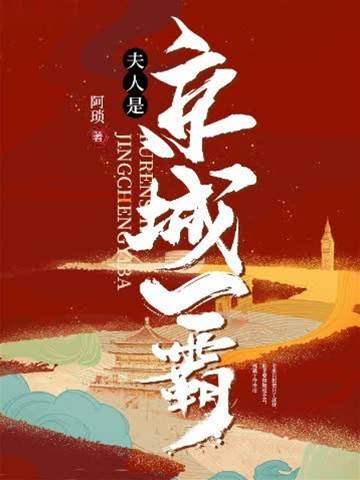
夫人是京城一霸
七姜只想把日子過好,誰非要和她過不去,那就十倍奉還…
123.2萬字8 19066 -
完結109 章

偏執太子的掌心嬌
宣威將軍嫡女慕時漪玉骨冰肌,傾城絕色,被譽為大燕國最嬌豔的牡丹花。 當年及笄禮上,驚鴻一瞥,令無數少年郎君為之折腰。 後下嫁輔國公世子,方晏儒為妻。 成婚三年,方晏儒從未踏進她房中半步。 卻從府外領回一女人,對外宣稱同窗遺孤,代為照拂。 慕時漪冷眼瞧著,漫不經心掏出婚前就準備好的和離書,丟給他。 「要嘛和離,要嘛你死。」「自己選。」方晏儒只覺荒謬:「離了我,你覺得如今還有世家郎君願聘你為正妻?」多年後,上元宮宴。 已經成為輔國公的方晏儒,跪在階前,看著坐在金殿最上方,頭戴皇后鳳冠,美艷不可方物的前妻。 她被萬人敬仰的天子捧在心尖,視若珍寶。
33.7萬字8.18 14518 -
完結942 章

重生我嫁給了未婚夫的死對頭
86.7萬字8 2805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