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吻》 第七十七章 沒有
晚上的風刺骨得厲害,寒流接連無數,況且這還是山上,
靠著墓碑坐了一會兒,起拍拍僵的下半。
陵園倒不是一個人都沒有,零零散散的還是能湊齊十個人的那種,有來訴喜的,兒拿著滿分試卷擺給端正在墓碑上的照片看,無人應聲,也有來訴苦的,哭著家里長家里短,散著濃濃憂悒。
世間百態,生死難定,死了不見得不好,活著的不見得好,人總是要跌跌撞撞而來,苦泅七六,縱觀酸甜苦辣,挨過來的是千帆閱過,沒過來的是千瘡百孔。
逆中,看不太清那人的臉,能認出來還是他那獨特的尾戒,與生俱來的深沉矜貴。
是他。
他眼前的墓碑上沒有照片,沒有刻字,無字碑,不知在思念誰。
謝厭的電話已經打了好幾個,容棲站在原沒。
鬼使神差的,走過去,可能是聽著耳邊的哭聲大過一切,心里也起了憐憫,“先生。”是一截覺的手帕,上面繡著玫瑰。
Advertisement
自走過來起,遲硯表微頓,呼吸中帶著點張。
愣了一瞬,看著遞過來的手帕,頷首,淡聲道:“多謝。”接過。
總覺得這一幕,有種悉,像是經歷過一番。
開門見山:“我們是不是在哪里見過?”
又是這樣的問題,場景在他腦海中兜兜轉轉。
里那個是打轉了好幾遍,“沒有。”
......
山腳下,謝厭正準備親自上山把那人逮下來,驀然抬頭。
看著容棲邊的男子,倒是收回了腳,眼里冷怠如水。
倆人走近,輕扯了下:“好久不見,遲先生?”
“謝先生。”依舊是不溫不火的態度。
真是個會裝的家伙。
才剛知道別人名字的容棲,“你們認識?”
側過于致的男人,不咸不淡開口:“見過幾次。”
謝厭心想,豈止幾次啊。
只有容棲不記得,他們這圈人,小時候可都見過呢。
陳最一直候在車上,見遲硯下來了,湊在他跟前耳語了幾句。
男人神沒有太大的變化,說了句我知道了。
這頭,謝厭也催著容棲快走了,臨上車前,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的:“你明天還要相親呢,今天晚上早點回去休息吧。”
容棲沒瞧出來,跟著遲硯說再見,對于長得好看的人總是耐心和底線放得寬。
陳最選擇站遠點,別以為他笨察覺不出來。
不用看都知道,四爺這個臉比五彩斑斕的黑,還要黑。
他轉往車里走,“去查那個人是誰。”
......是。
后夜。
容棲做了個夢。
夢中是七歲的樣子,病床圍的一圈都是打打鬧鬧的玩伴,幾個小孩兒科打諢。
“容棲我怎麼覺你進醫院不瘦反而胖了?”
已經恢復得差不多小孩兒把后的枕頭砸到那人腦殼上,“再說我胖這個床位的下一個繼承者就是你信不信。”
小男孩兒才不怕呢,做著鬼臉挑釁。
”哥~回頭,得千百,被哥的那個年只是笑笑,手上的勺子就是準備給喂飯吃。
猜你喜歡
-
完結1221 章

報告爹地:媽咪要逃婚
夏心妍嫁了一個躺在床上昏迷三年的男人,她的人生終極目標就是成為一個超級有錢的寡婦,然後陪著她的小不點慢慢長大成人。 「霍總,你已經醒了,可以放我走了麼?」 「誰說的,你沒聽大師說麼,你就是我這輩子的命定愛人」 一旁躥出一個小身影,「媽咪,你是不是生爸比氣了?放心,他所有的家當都在我的背包里,媽咪快帶上我去浪跡天涯吧」 男人深吸一口氣,「天賜,你的背包有多大,還能裝下爸比麼......」
193.5萬字8 13052 -
連載1504 章

夫人她A爆全世界
【甜寵,重生,虐渣,馬甲,團寵】“還逃嗎?”秦初使勁搖頭:“不逃了。”放著這麼好看的男人,她再逃可能眼睛真有病,前世,因錯信渣男賤女,身中劇毒鋃鐺入獄,自己最討厭的男人為替自己頂罪而死,秦初悔不當初,重回新婚夜,秦初緊抱前世被自己傷害的丈夫大腿,改變前世悲慘人生,成為眾人口中的滿級大佬。人前,秦初是眾人口中秦家蠢鈍如豬的丑女千金,人后,秦初是身披各種馬甲的大佬,某天,秦初馬甲被爆,全
135.4萬字8 16222 -
完結13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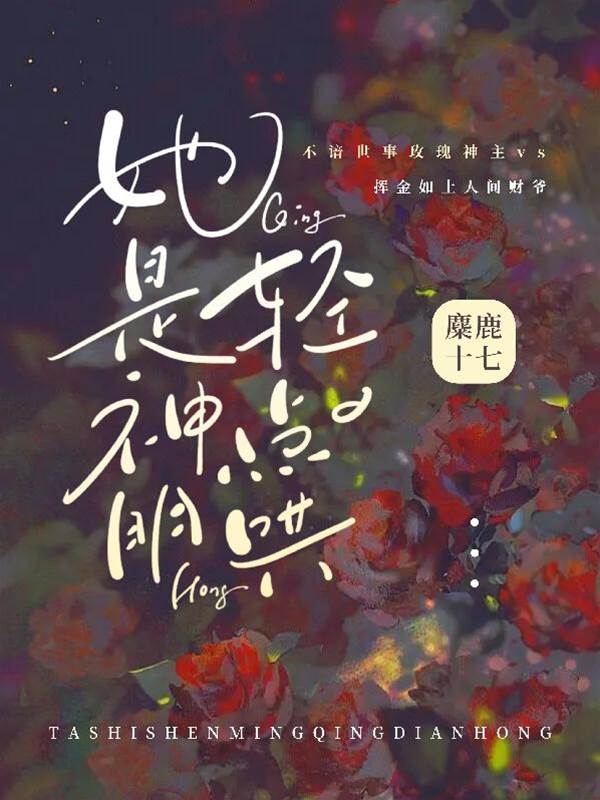
她是神明輕點哄
[不諳世事玫瑰神主VS揮金如土人間財爺][先婚後愛 雙潔+情有獨鍾+高甜]“她牽掛萬物,而我隻牽掛她。”——柏聿“愛眾生,卻隻鍾情一人。”——雲窈雲窈有個好的生辰八字,擋災的本事一流。不僅讓她被靈蕪城的豪門喬家收留,還被遠在異國,家財萬貫的柏老爺給選中做了柏家大少爺柏聿的未婚妻。—雲窈喜歡亮晶晶的寶石和鑽戒,豪門貴胄笑話她沒見過世麵,柏總頓時大手一揮,寶石鑽戒一車一車地往家裏送。—雲窈有了寶石,想找個合適的房子專門存放,不靠譜的房產中介找上門,柏太太當機立斷,出天價買下了一棟爛尾樓。助理:“柏總,太太花了十幾億買了一棟爛尾樓。”男人麵不改色,“嗯,也該讓她買個教訓了。”過了一段時間後,新項目投資,就在那片爛尾樓。柏聿:“……”—柏聿的失眠癥是在雲窈來了之後才慢慢好轉的,女人身上有與生俱來的玫瑰香,他習慣懷裏有她的味道。雲窈卻不樂意了,生長在雪峰上的玫瑰神主嫌棄男人的懷抱太熱。某天清晨,柏太太忍無可忍,變成玫瑰花瓣飄到了花盆裏,瞬間長成了一朵顏色嬌豔的紅玫瑰。殊不知,在她離開他懷抱的那一瞬就已經醒過來的男人將這一切盡收眼底…他的玫瑰,真的成精了。
23.9萬字8 771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