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在說小爺的壞話?》 第 70 章
陸書瑾聽了這個規則之後發現,這場猜謎招婿,其實就是用另一種方法賺銀子的把戲而已。
專門吸引那些好且貪圖利益,心懷不軌之徒獻上自己白花花的銀兩,蔣宿就算是其中一個。
本來這種一個願打一個願挨的賺錢方法也不算什麽,隻是陸書瑾瞧著蔣宿模樣可憐,想著把他的那十兩拿回來而已。
將第一個燈謎翻了個麵,就見謎語寫在背麵上:飛書錢塘春已去。
這種題目對來說頗為簡單,幾乎是掃一眼,就已知道了答案,將花燈遞給旁邊的中年男子,卻不承想坐在旁邊的姑娘突然站起,從手裏接過,對怯怯一笑,“公子可猜出來了?”
陸書瑾並未察覺出有什麽異常,隻道:“鴻江之夏。”
那姑娘將燈謎下方黏著的紙撕去,出的謎底與陸書瑾所言一致,笑道:“答對。”
蔣宿站在下麵,小小歡呼了一聲,而後抓了一把蕭矜的手臂說道:“蕭哥,你說咱們能不能靠陸書瑾在這發家致富啊?”
蕭矜沒說話。
蔣宿又道:“你瞧那人對陸書瑾笑得多開心,莫不是瞧上陸書瑾了?我聽旁人說這酒樓的東家隻有這麽一個兒,誰當了老東家的婿,這酒樓日後便是誰的,若是陸書瑾願意當贅婿,往後那是不愁吃穿了。”
要不怎麽說他是個沒眼的東西呢,都沒發現蕭矜的臉黑鍋底了,一張還叭叭個不休,盡往蕭矜的心尖上踩。
蕭矜沒好氣道:“就這麽一棟破舊樓,能值幾個錢?”
“話不能這麽說。”蔣宿說道:“你瞧瞧陸書瑾以前剛來海舟學府的那子窮酸模樣,就差把‘窮得要死’四個字寫在臉上了,蕭哥你看不上這酒樓,陸書瑾可未必瞧不上。”
Advertisement
“此事絕不可能。”蕭矜道。
蔣宿嘖了一聲,“俗話說得好,寧拆十座廟,不毀一樁姻,蕭哥你偶爾也行善積德,做些好事吧。”
蕭矜實在忍不了了,一把就住了他的豬,惡狠狠道:“你見過那種鹵好後的豬耳朵是如何擺盤的嗎?”
蔣宿出疑的目。
蕭矜道:“就是將整片豬耳朵切一條一條的,然後整齊碼在盤子上。”
蔣宿扭了下,從他的手裏掙出來,關切地問道:“蕭哥你想吃豬耳朵了?”
蕭矜就笑著說:“不,我是說你若是再說廢話,你的就會變豬耳朵那樣。”
蔣宿趕忙抿住,表示自己不會再說一句話。
就這麽幾句話的工夫,陸書瑾已經在上麵解了八道燈謎,摘一個燈,便解一道題,速度很快,並無錯誤。
十個燈謎解完時,那中年男子問是繼續摘燈,還是就此領了十兩銀子作罷。
陸書瑾道:“繼續。”
中年男子道:“若是繼續摘燈,那麽再解三盞則得十一兩,解五盞則得十五兩,解十盞則得二十兩,倘若未解到規定燈數便解錯,
那邊所有銀兩皆不得,還要補十兩,公子可想清楚了?”
陸書瑾從容點頭。
下麵兩排的燈都是些簡單的問題,已經被陸書瑾解完,再往上的燈謎則是為了賺銀子而故意刁難,但對陸書瑾來說並不算是什麽難事。
有些人學識淵博,但對上這種生僻的燈謎未必能夠解出,而陸書瑾曾經研究過一段時間的燈謎,對此有些信心。
畢竟過去的那麽多年裏,每一個上元節都在自己那間小屋中,總要找些娛樂來填補自己那孤寂而無趣的生活。
眼看著陸書瑾一盞盞將燈摘下來,一道道解出謎底,臺下的人歡呼好的聲音也越來越響,中年男子的臉上也越來越掛不住。
蔣宿憋了那麽一會兒,終於憋不住了,衝上麵大喊,“陸書瑾!快快將二十盞燈拿下!”
蕭矜被他吵得左耳朵嗡嗡響,一掌拍到他後腦上,將他攆到一邊去。
陸書瑾將十五盞燈解完時,整個架子上的燈已經沒有了。
那姑娘從下人手中接過一杯熱茶,轉手遞給,微笑著道:“公子先喝口茶歇一歇,我們即可將燈補上。”
陸書瑾並不口,拱手婉拒,往旁邊走了兩步等著他們補燈,期間往下掃了一眼,在人群中看到了蕭矜。
他個子高,麵上又戴狼麵,站在人群中相當顯眼,陸書瑾一眼就看到了他,彎對他笑了笑。
隔著約莫十來步的距離,這個笑容被頭頂上的燈染上了曖昧的,仿佛一支包了頭的箭,直直中蕭矜的心髒。
頓時一春水在心中漾起來,將他的心泡得綿綿的。
蕭矜很想問問別人,隻有他一個人覺得陸書瑾的笑容很好看嗎?
蔣宿瞧在眼裏,明知道是找打行為,卻還是湊到蕭矜邊,說道:“蕭哥,怎麽你這會兒不怪陸書瑾笑了?”
蕭矜睨他一眼,“怎麽著,有人這麽對你笑嗎?”
蔣宿立馬,“誰說沒有?多了去了。”
蕭矜攥著拳頭要打他,蔣宿趕忙往前溜了幾步,到另一邊去。
剛站定,就覺得東西砸在了他的後腦勺上,他往頭上擼了一把,回頭瞧了瞧蕭矜。
以為是蕭矜拿東西砸他解氣,便沒有計較,誰知剛扭頭回去沒多久,頭上又砸了個東西,是個小玩意兒,應當是小石子一類,砸得微微有些痛。
他又回頭,說道:“蕭哥,你砸一下差不多得了。”
蕭矜不明所以,疑地看他一眼,“你怎麽就那麽多話呢?閉上老實一會兒!”
蔣宿被兇了,隻好老老實實站好,結果正瞧著陸書瑾解第十六道燈謎的時候,又有石子往頭上砸。
他這下真的怒了,扭過頭想與蕭矜好好說道一番,結果發現蕭矜已經不在那,換了個位置去了斜前方。
蔣宿頓時二丈不清頭腦,他分明是覺到有人砸他的,不是蕭矜還能誰?
他踮著腳往後巡視了幾圈,沒
看到一個悉麵孔,結果又是一個石子砸在腦門上,他當即然大怒,捂著腦門怒而抬頭,尋思是誰那麽不長眼,逮著他欺負。
結果這麽一抬頭,就看到二樓的欄桿,站著兩個人。
一人趴在欄桿上,手裏隨意地顛著手中的石子,那正是方才砸他的罪魁禍首,但他臉上戴著麵瞧不出真容,與蔣宿對上視線之後也毫沒有被逮到的心虛,反而是出個笑容來,對他招手。
蔣宿剛想罵他,眸一瞥,就看到那人旁邊站著的竟然是梁春堰。
梁春堰反靠在欄桿上偏著頭看他,手裏慢慢轉著麵。
人前見到蔣宿的時候,他臉上總是掛著溫和善的笑,但是一到了人後,那張臉就很是淡漠,眸子裏沒有什麽緒。
蔣宿嚇一大跳,臉劇變,隻覺得他是撞了鬼。
這會兒也沒什麽被砸的怨氣了,甚至想裝瞎子,將頭扭回去,裝作沒看見這倆人。
但梁春堰沒給他機會,衝他招了兩下手,示意他上樓。
蔣宿豈敢不從,轉頭看了眼蕭矜,便從人群中橫過,到了樓梯往上,來到了梁春堰與吳運麵前。
梁春堰十分客氣,說道:“借一步說話。”
蔣宿想回一句能不能不說,但沒有那個膽量。
三人隨便去了二樓的一個上了鎖的房間之中。那門鎖在梁春堰的手裏跟棉花似的,蔣宿見他好像就是輕輕一,鎖就斷開了。
進去之後反手關上門,吳運摘下麵,點了屋中的燈。
外頭還是喧鬧的,隻是到底隔了一扇門,那些吵鬧的聲音被降了許多,顯得屋子裏頗為安靜。
吳運不坐椅子,翻上了桌子盤而坐,見蔣宿著腦袋的樣子有些稽,就道:“別張,我們若是要殺你,不會選在人那麽多,且你又在蕭矜邊的況下對你下手,否則事不好理。”
蔣宿訕笑道:“哪能呢,二位一看麵相就是大好人來著,不可能會殺無辜。”
這馬屁拍了等於沒拍,兩個人麵上一點變化都沒有。
梁春堰突然問了個奇怪的問題:“你家養狗嗎?”
蔣宿愣了一下,說:“沒有。”
梁春堰道:“上回說你若是將我的份泄出去,我就將你蔣家上下屠盡,連狗都不放過,但你家若是沒有養狗,豈非我食言?改日我就送你一條。”
“這……不用了吧。”蔣宿有氣無力道。
梁春堰道:“我從不食言。”
吳運翻了個白眼,暗道難怪他方才讓自己去找條帶崽的母狗,原來是要送給這小子。
一個要求,折騰兩個人,心眼是真壞。
蔣宿了後脖子,沒再吭聲。
眼前這兩個人是實打實的殺人不眨眼,且看起來又喜怒無常,誰知道會不會哪一句話惹了他們不開心,悄無聲息就給他抹了脖子。
一時間他又埋怨起喬百廉來,心說喬院長這到底是上了年紀,
眼神不好使了,統共就招了三個寒門學子,其中兩個是大壞種。
梁春堰像是說完了正事,而後隨手從懷中拿出一封信,遞到蔣宿麵前,說道:“把這個轉給蕭矜。”
蔣宿看著信封,方才還趴趴的眼神頓時一厲,聲問:“這是什麽?你們是不是在信裏撒了什麽毒,等蕭哥一打開信就將他毒死,還想嫁禍於我!我絕不可能幫你做此事!”
“大丈夫有所為有所不為,舉頭三尺有神明,你們要殺就殺吧,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我本不怕!”
梁春堰冷漠地看著他,聽他胡背了一通詩詞之後,才說道:“這是蕭矜正在查的事。”
蔣宿瞪著雙眼,一臉兇猛,“我看起來很好騙?”
“嘿,你小子。”吳運笑了,在旁邊補了一句,“看起來倒是欠揍的。”
梁春堰道:“裏麵寫著秦蘭蘭的死因,還有葉家對秦蘭蘭出手的原因。”
蔣宿多知道蕭矜最近幾日都在忙此事,但他毫幫不上忙,也就偶爾問上兩句,蕭矜不會說太多,但若是查到了也會告訴他。
沒想到梁春堰會遞來這麽個東西。
他想了想,還是手接下,但以防萬一他將子扭過去快速拆開了信封,將裏麵的信出來抖了抖,確認沒有藏什麽末毒之後,才又將信放回去,有些尷尬地看向梁春堰。
“……我打小就比較細心。”蔣宿為自己辯解。
“那你一定很討姑娘家歡心。”吳運笑著往他心窩上刀子,“你若是去猜燈贅的話,一定不會被護衛扔出門外吧?”
蔣宿暗罵一聲,這兩個混球。
他揣著信出了門,往樓下去,與此同時陸書瑾也將二十盞燈全部解完。
中年男子問道:“公子好才識,若再解一燈便有了迎娶我家小姐的機會,可還要繼續?”
大多數男子參與猜燈謎,都是奔著這貌的姑娘而來,否則也不會十兩銀子做這閑事。
猜你喜歡
-
完結645 章

惡妃重生后只想虐渣
上輩子,她為他付出所有,助他一步步位極人臣,卻比不上她的好姐姐陪他睡一覺。當溫柔繾綣的夫君取她性命時,她才知道自以為的情深似海都是笑話。含恨而終,陸襄憤恨詛咒,要讓負她害她之人不得好死……再睜眼,她回到了十四歲那年,同樣的人生,她卻帶著滿腔仇恨而歸。夜黑風高,陸襄撿到了被人追殺重傷的楚今宴,兩眼發亮。“誒喲,金大腿!”于是二話不說把人拽到自己屋里藏好。“今天我救你一命,日后你要答應我三個要求。”楚今宴:他并不是很想被救……再后來,楚今宴拍拍自己的大腿,勾勾手指:“愛妃,來,孤的大腿給你抱。” *** 她:陰險,詭詐! 他:卑鄙,無恥! 路人甲:所以是天生一對? 路人已:呸,那叫狼狽為奸!
112.5萬字8.18 81453 -
完結15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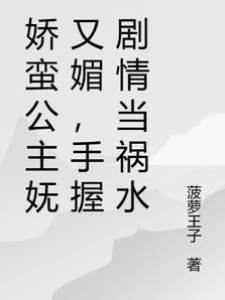
嬌蠻公主嫵又媚,手握劇情當禍水/嬌蠻公主以色爲誘,權臣皆入局
【釣係嬌軟公主+沉穩掌權丞相+甜寵雙潔打臉爽文1v1+全員團寵萬人迷】沈晚姝是上京城中最金枝玉葉的公主,被養在深宮中,嬌弱憐人。一朝覺醒,她發現自己是活在話本中的惡毒公主。不久後皇兄會不顧江山,無法自拔地迷上話本女主,而她不斷針對女主,從而令眾人生厭。皇權更迭,皇兄被奪走帝位,而她也跌入泥沼。一國明珠從此被群狼環伺羞辱,厭惡她的刁蠻歹毒,又垂涎她的容貌。話本中,對她最兇殘的,甚至殺死其他兇獸將她搶回去的,卻是那個一手遮天的丞相,裴應衍。-裴應衍是四大世家掌權之首,上京懼怕又崇拜的存在,王朝興替,把控朝堂,位高權重。夢醒的她勢必不會讓自己重蹈覆轍。卻發覺,話本裏那些暗處伺機的虎狼,以新的方式重新纏上了她。豺狼在前,猛虎在後,江晚姝退無可退,竟又想到了話本劇情。她隻想活命,於是傍上了丞相大腿。但她萬萬沒有想到,她再也沒能逃出他掌心。-冠豔京城的公主從此被一頭猛獸捋回了金窩。後來,眾人看著男人著墨蟒朝服,明明是尊貴的權臣,卻俯身湊近她。眼底有著歇斯底裏的瘋狂,“公主,別看他們,隻看我一人好不好?”如此卑微,甘做裙下臣。隻有江晚姝明白,外人眼裏矜貴的丞相,在床事上是怎樣兇猛放肆。
27.8萬字8 450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