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塑料竹馬閃婚了》 第133頁
季旸太了解了,看起來沒心沒肺,其實很能扛事,裝得若無其事,無非是不想大家都愁云慘淡的,反正哭也是一天,笑也是一天,哭一哭也不能疼一點。
但……
“哭一哭也沒什麼,你還是最厲害的,一點都不損你的形象。”季旸抬手,了一下的臉,滿是心疼。
梁思憫的眼淚瞬間滾落,好像臉都瞬間蒼白了幾分,說:“我好疼……”
季旸抓住的手,抵在邊親吻安,然后出給眼淚。
梁思憫哽咽了兩句,護士突然推門進來,模糊聽到剛喊疼了,安道:“麻藥過了,這是正常的,如果實在疼得不了,記得按鈴我,我讓醫生再給你開點止疼的。”
說完又吼了句:“16床,你怎麼又下來。”
他搬到16床了還是沒躲得過護士的火眼金睛。
-
一個半月后。
私人醫院的vip病房,梁思憫坐在那兒看電視,屋里黑漆漆的,只屏幕一點亮。
云舒還在公立醫院,那里有許多認識的人,不愿意轉過來,周邵紅跟梁思諶就沒強求,倆人今晚得了空,先去看了云舒,然后順道過來看看這倆人。
Advertisement
倆人底子都好,恢復得也快,這家醫院是季家投資的,醫生毫不敢怠慢,從住進來就得到了心的照料。
但明達許多事,季旸本逃不開,就算他爺爺子骨還朗,還能再出山,但他自己也不愿意放下手,正是關鍵時候,這時候松懈,很可能他之前所做的所有努力都會付之東流。
他這人,只要沒死,一切都放不下手,注定是心的命。
于是每天病房里公司的人來來去去,這里仿佛了他第二個辦公室,本來季旸是打算和梁思憫暫時分開兩個病房,但梁思憫不愿意,于是這里每天就是季旸跟人在客廳談公事,梁思憫旁若無人地出現在任何一個地方。
梁思諶每次見了,都忍不住出大拇指,贊嘆的親妹妹真是個臉皮極厚心理素質極佳的奇子。
梁思憫一點也不擔心別人怎麼看,最近很憂愁的一件事是,每天吃了睡睡了吃,長胖了。
杜若楓和路寧來看,非常委婉地贊嘆一句:“哇,寶貝你現在就很妖嬈。”
梁思憫痛定思痛,決定理戒斷小零食,比如看兩部恐怖片,最好是那種尸山海帶點惡心人的東西。
好不容易找來幾張碟片,大晚上又不敢自己看,于是搬了張凳子,讓季旸坐在凳子上,坐在他上,面對著屏幕,趴在他肩膀上看,季旸扯了一張移桌子,背對著屏幕,抱著,對著電腦屏幕理郵件。
兩個人姿勢實在詭異,季旸不用看就知道影片的驚悚程度,那取決于梁思憫摟著他脖子的力道有多。
比如現在,他抬手扣在梁思憫手臂:“你再勒點,明天你就沒有老公了。”
梁思憫正看的迷,本沒聽見,于是季旸把手從電腦鍵盤上移開,一手掐著的腰,一手朝著屁拍了一掌。
確實胖了點兒,但不上手也不出來,可能是閑太久了有點焦慮。
從去年到今年,第二次出事了。
雖然上不說,其實心里難過的。
周邵紅和梁思諶敲了門進來的,倆人誰也沒聽到。
“咳——”
梁思諶咳嗽了聲,提醒某人。
屋是智能控制,有個全屋控制的遙控,季旸起來,把客廳的燈打開了,扯了扯梁思憫,對方毫無反應,于是無奈坐著打了招呼:“媽,哥……”
周邵紅湊過去擰了下梁思憫的耳朵:“你還越來越肆無忌憚了。”
折騰起季旸來真是花樣百出。
梁思諶在旁邊沙發坐下來,翹著二郎,一副看熱鬧的架勢,偏頭跟季旸對視上:“你也真慣著。”
這一個多月里,但凡梁思憫想干的事,季旸就沒有反駁過,恨不得把慣出病來。
梁思憫毫從季旸上下來的意思都沒有,仗著自己是病號,理所應當地裝起了弱:“媽,我好虛弱,我不想。”
“說得好像就你生病了似的。”周邵紅沒忍住又拍一掌,“你看你像什麼話。”
梁思憫裝聽不見,依舊趴在他肩上。
季旸覺得實在恥,可也不忍心把扯下來,最近經常口悶,坐著總不舒服,這麼趴在他肩背,還好些,就總是這麼坐著,而他正好也可以順便理點公務。
其實談不上縱容不縱容,不過是你我愿罷了,他甚至很這種被依賴的狀態。
梁思憫順便問了句云舒的況,周邵紅沖著梁思諶的方向抬了下下:“下次不用問我,看你哥的狀態就知道。”
說得也是,梁思憫扭頭看了梁思諶一眼:“哦,春風滿面,看來恢復得很好。”
母子兩個實在沒眼看,寒暄幾句就離開了。
臨走的時候周邵紅說:“你倆這,可千萬別要小孩,指不定慣什麼樣。沒一個靠譜的。”
梁思憫撇撇,嘀咕了句,也不想要小孩。
倆人走了,季旸卻沉默了,半晌問一句:“你不喜歡小孩?”還是不想要跟他的小孩……
“不是啊!”梁思憫覺得他真的很敏,扭頭親了親他的臉,“我還沒過夠二人世界,小孩嘛……順其自然就好。”
小士:如果覺得不錯,記得收藏網址 或推薦給朋友哦~拜托啦 (>.
猜你喜歡
-
完結271 章

且以深情共余生
相似的聲音,相似的容貌,遇見了同一個他。兜兜轉轉,走走停停,時光不改蹉跎。如果上天再給她一次重新選擇的機會,她一定奮不顧身愛的更加用力!
50萬字8 9205 -
完結378 章

玄門回來的假千金又在擺攤算卦了
肖梨在玄門待了一百年,同期進來的那條看門狗小黑,都已經飛升上界,她還只能守著觀門曬太陽。老祖宗顯靈告訴她,“肖梨,你本來自異界,塵緣未了,若想飛升,还得回去原来的地方,了却凡尘杂事,方可勘破天道!” 回到现代,肖梨成了鸠占鹊巢的假千金,这一世,没有留念,两手空空跟着亲生父母离开肖家。 圈内人都在等着,肖梨在外面扛不住,回来跟肖家跪求收留。 却不想…… 肖梨被真正的豪门认回,成为白家千金,改名白梨。
64.4萬字8 60458 -
完結189 章

荒腔
沈弗崢第一次見鍾彌,在州市粵劇館,戲未開唱,臺下忙成一團,攝影師調角度,叫鍾彌往這邊看。 綠袖粉衫的背景裏,花影重重。 她就那麼眺來一眼。 旁邊有人說:“這是我們老闆的女兒,今兒拍雜誌。” 沈弗崢離開那天,州市下雨。 因爲不想被他輕易忘了,她便胡謅:“你這車牌,是我生日。” 隔茫茫雨霧,他應道:“是嗎,那鍾小姐同我有緣。” 京市再遇,她那天在門店試鞋,見他身邊有人,便放下了貴且不合腳的鞋子。 幾天後,那雙鞋被送到宿舍。 鍾彌帶着鞋去找他。 他問她那天怎麼招呼都不打。 “沈先生有佳人相伴,我怎麼好打擾。” 沈弗崢點一支菸,目光盯她,脣邊染上一點笑:“沒,佳人生氣呢。” 後來他開的車,車牌真是她生日。
28.8萬字8 1773 -
完結19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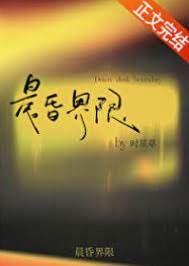
晨昏界限
林霧有些記不太清自己和陳琢是怎麼開始的,等她後知後覺意識到事情變得不對勁時,他們已經維持“週五晚上見”這種關係大半年了。 兩人從約定之日起,就劃分了一條明顯的,白天是互不相識的路人,晚間是“親密戀人”的晨昏界限。 而這條界限,在一週年紀念日時被打破。 - 人前不熟,人後很熟的故事TvT
27萬字8 564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