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步深陷》 第121章 舍棄
我從未見過這樣的林宗易。
坦,溫暖,干凈,甚至是明。
他所有的罪錯,像是謊言。
我恍惚失神,面下進鍋里,幾滴熱水濺出,我條件反甩手,他偏頭,“是不是燙著你了。”
林宗易牽起我手,吮著微微發紅的皮,昏黃的燈影籠罩住他側臉,他仿佛一個神莫測的故事,渾鍍著一層驚心魄的,是的陳舊的味道,明又。
“你竟然會煮飯。”
他齒含著我指尖,“期待嗎?”
我嗅了嗅空氣,“沒什麼香味。”
他關掉煤氣爐,“我只會煮清水面,也只給你煮過。”
我在原地呆滯了好一會兒,直到林宗易喊我去餐廳,我才回過神。
他看著我吃第一口,手拭我角沾染的蔥末,“好吃嗎。”
說實話,他的手藝不適合下廚,適合給敵人下毒,可不曉得為什麼,我一口接一口沒停,越吃越抑,像一只尖銳的鉗子扼住了心臟,混著那酸一起吞,“好吃。”我咬斷沒滋味的面條,“要是加點,就更好吃了。”
林宗易的袖卷起了半截,帶著一令人沉迷的煙火氣,他重新放下袖口,“這是我最艱難的日子,連續四年的晚餐。”
我一愣,“林家不是很富貴嗎?”
對于殷沛東和林宗慧的婚姻,我其實有耳聞,殷沛東也是靠老婆發家的富商,林家當初做半導行業,又轉行餐飲,涉獵雜的。那年代的小城市,煙草業和歌舞廳最暴利,也最高貴,林家算不上高門大戶,不過有錢,7、80年代的百萬富翁。
Advertisement
“林澤坤是我繼父。我母親為討好他,保全林家的面子,改了我的姓氏,對外說林澤坤老來得子。”
我著筷子,“他對你不好。”
林宗易眼睛里沒有一溫度,沒有,像幽邃沉寂的深淵。
“十五歲,我跟著蟒哥去云城,他做皮生意,后來我自己回到濱城,開會館干買賣。”
我著他,“蟒哥?”
林宗易焚上一支萬寶路,“大家都稱呼他蟒哥,我最小,開始稱呼蟒叔。他什麼買賣都干,好的,壞的,在東南亞發家。兒有神病,去歐洲治療了,有一回看見蟒叔教訓保鏢,把保鏢打出了,刺激了。”
我默不作聲攪拌面條。
林宗易叼著煙,十指握抵在眉心,遮住了半張臉,“韓卿,你恨我嗎?”
我低下頭,面條吸干了湯,一泡發膨脹,我沒回應。
我去嬰兒房給林冬喂,林宗易在浴室洗澡,我返回房間發現他站在臺上吸煙,濃重的夜吞噬了他廓。
他換了黑的襯和西,系著條紋領帶,異常沉悶,很重的心事。
手機在旁邊反復響,他沒有接。
我走過去提醒,“宗易,你的電話。”
他吐出一團煙塵,一言不發。
我瞥來顯,是鄭寅,打了17個。
林宗易銜著煙,手臂搭在桅桿上,火苗被呼嘯的江風吹滅,又掙扎著死灰復燃,像我們之間的婚姻,也像他自己。
“韓卿,你之前問我,有沒有過人。”
我原本要走出臺,聞言作一頓。
他輕笑,“我這種人,大起大落半生,真心和良心,早已舍棄了。”
我攥著拳。
他倚住磚墻,“就算一分喜歡,我也拼了全力,再多一些,我實在給不起。”林宗易低聲笑,煙灰墜江水,毫無水花,他面容也波瀾不驚。
“我不懂什麼是仁慈,我只懂掠奪。”他嘶啞說,“你睡吧。”
#每次出現驗證,請不要使用無痕模式!
br> 我垂下的拳隨即一松。
林宗易碾滅煙頭,邁步和我肩而過,離開臥室。
我追出,“宗易!”
他止步,轉過笑,“怎麼了。”
我抖著,五臟六腑和孔都在抖,我沖到他面前,“你——”
他含笑凝視我。
我腔憋得發堵,像錘子狠狠撞擊,我用力要說什麼,舌尖盤旋了一圈,終是又咽回,“我也會煮面,你嘗嘗嗎?”
林宗易凝視了我許久,“不嘗了。”
我眼眶有點紅,“趕著出去啊。”
他嗯了聲,“辦點急事。”
我嚨干,分明大口呼氣還堵得難,“慢點開車。”
他臉上是極淺的笑意,“好。”他我眼角的淚痣,“我初次見你,便覺得它很。”
我說,“我只覺得你眼力毒,三言兩語的對話就能識破我撒謊了。”
他笑意轉濃,“走了。”他收回手,毫無留。
“林宗易。”我朝他背影喊,“我沒有希你死,我僅僅希你放過我。我有時太畏懼你了,我真的不敢想象和你過一輩子還會遭什麼。”
他已經走到玄關,再次駐足。
我抹了一把眼淚,“我是恨你,但從這一刻,我原諒你了。”
他背對我佇立了好半晌,拔寬闊的脊背不斷起伏,從輕微到劇烈,又徹底平靜。
不知過了多久,林宗易說,“你恨著吧。”
他進主臥,“我落下一件東西。”
片刻后林宗易又出來,自始至終沒再看我一眼。
我好像喪失了全部力氣,在門關上的時候,整個人沿著墻壁下。
樓下傳來汽車發的聲響,我爬起,撥通蔣蕓的號碼,“蕓姐,把證銷毀吧。”
蔣蕓在酒吧,dj舞曲震耳聾,“燒不了,我遞上去了。”
我手一哆嗦,“你遞上去了?”
說,“估計明天開始查了。”
我沒吭聲。
“心了啊?”蔣蕓避到一個安靜的地方,“沒你這份證據,林宗易照樣躲不掉。他想藏在幕后,但會館經營得那麼紅火,私下搶了多商人里的食,聯手找茬要分一杯羹,鄭寅扛不了,林宗易只能親自出馬,皮子嗎?要真格的,輸了,滾蛋,贏了,名聲大噪。他從沒輸過,能藏得了嗎?早就被盯住,只不過現在馮斯乾得他浮出水面了。”
我依然沉默。
蔣蕓說,“他折騰得你夠嗆,你臨了也將他一局泄恨,從此扯平了,誰也別埋怨誰了。你想要,心腸越越好,你以前對付男人哪次手了?”
我心煩意掛斷電話,又想起什麼,拉開床頭柜底層的屜,林宗易的婚戒還在,我們的合照沒了,我把家里各個角落翻了個遍,確實不見了。
我在客廳坐著,蘇姐凌晨回來了,跟我說老家的侄今天在江城生孩子。
我沒理會那些,“你收拾屋子了。”
蘇姐外套,“您是了什麼嗎?”
“床頭柜你了嗎?”
搖頭,“您的臥室,我只地板了。”
我心不在焉垂眸,看著一束搖曳的月,“沒事了。”
第二天中午我接
到一個陌生電話,來自濱城的號碼,接聽是王晴娜,在那頭大吼,“何江綁架了林恒!”
我當即撂下筷子,“林恒找著了?”
緒激質問,“你本不清楚他的下落,你從頭到尾在詐我對嗎!”
玩命按喇叭,在下高速路。
“我沒有詐你,我的確安排了眼線跟蹤林恒的去向,可中途出岔子了。”
王晴娜崩潰哭著,“馮斯乾派人帶走林恒,我收到錄像了,在湖城高速。”
果然去湖城了。
我二話不說掐了通話,直奔華京大樓,車沒停穩就跳下去,巡視的保安認出了我,沒阻攔。
我闖進七樓董事長辦公室,正在匯報工作的下屬被踹門的巨響打斷,紛紛看向我。
我停在那,和馮斯乾對視著。
他示意部下,“會議推遲半小時。”
他們目不斜視離開,辦公室只剩我們兩人,我走向他,“何江去湖城了。”
馮斯乾若無其事簽文件,“我知道你想問什麼,林恒是我在手上。”
我奪過他的筆,“你綁架了林恒?”
“不是綁架。”他漫不經心糾正,“林宗易麻煩纏,作為林恒曾經的姐夫,我照料他,不應該嗎?”
這一句姐夫莫名逗笑了我,“你不提我都忘了,林恒是你的表弟。”
馮斯乾審視著我難以自控的明笑臉,“有趣嗎。”
我一邊笑一邊點頭,“有趣。”
“還有更有趣的。”他傾,“你的肩帶,笑崩開了。”
我笑容頓時一收,直起腰,神恢復一本正經,“林恒只是孩子,大人的恩怨,別牽扯無辜。”
“只是孩子?”馮斯乾叩擊著手邊的煙灰缸,“王威挾持馮冬,脅迫林宗易娶王晴娜,利用我兒子時,他心留了嗎。”
我將簽字筆扔在桌上,“他沒得逞,而且惡有惡報了。”
馮斯乾拾起筆,繼續簽署合同,“那是我拖延住他,提前救下了馮冬。林宗易有本事從我手上弄走林恒,我也可以放人。”
我坐在高腳椅上,“他如今哪還顧得上林恒。”
馮斯乾簽完幾份文件,招呼市場部書進來,“林宗易按兵不,是因為他看了你的子,有你在,林恒出不了事。”
我環顧這間辦公室,“殷沛東退位了。”
馮斯乾笑著說,“是不夠資格在董事長的位置了。”
馮斯乾持有華京集團40的份,占據半壁江山,別說殷沛東了,再加上大東章徽榮,也撼不了分毫。
“你籌謀很久了。”
他云淡風輕,“一年,從你懷孕就在部署,等時機,等這一天。”
我視線定格在馮斯乾上。
他目雖然深沉,卻帶笑,“屬于我的,接下來我會一點點拿回。”
我站起,“我和王晴娜談了一筆易,把林宗易證據給我,我把林恒給。”
“給不了。”馮斯乾當場駁回,“林宗易不倒,林恒必須在我手中。”
我注視他,“馮冬同樣也在林宗易手中,他沒打算對孩子怎樣。”
我回憶他昨夜的樣子,林宗易似乎放棄了。
“是嗎?”馮斯乾眼里噙著笑,“你確定馮冬在他手中嗎。”
我被他問得一怔,早晨蘇姐抱著孩子去兒醫院打針了,我出門還沒回。
“難道在你手中?”
#每次出現驗證,請不要使用無痕模式!
馮斯乾說,“不錯。”
蘇姐在這時正好打來電話,我接通,語氣焦急,“太太,馮先生的人帶走林冬了!還打昏了保鏢,我聯絡先生,始終聯絡不上他。”
我深吸氣,直接掛了。
“你和我商量了嗎。”
“韓卿。”他神喜怒不辨,“什麼關頭了,馮冬養在林宗易的邊,會為威脅我的刀。”
馮斯乾起,“你傷痊愈了嗎。”
我不解,“什麼傷?”
“在馬場不是蹭傷了嗎。”
我沒個好臉,“都一星期了,早愈合了。”
馮斯乾笑出聲,“什麼狗脾氣。”
他走過來,抬手解我的扣,我立馬攏住領,瞟了一眼門外來來往往的員工,“你干什麼。”
馮斯乾手指修長,骨節有力,輕輕一撥,我手便被迫松開,“我檢查你的傷,真好了嗎。”
“我的傷在腳背和小。”
馮斯乾面無表向我,“我怎麼記得在口。”
他沒記錯,口的最嚴重,被樹杈割破了,倒是沒留疤,可出了,白的割痕起碼還要十天半月消褪。
我朝門口走,“好了就是好了。”
馮斯乾住我,“你也搬回瀾春灣,我讓何江明早去接你。”
我沒說話。
晚上我昏昏沉沉剛睡著,樓道傳出一陣噗滋的噪音,像電閘壞了,沒完沒了響,我煩躁蒙住頭,可聲音越來越大,震得天花板的吊燈直晃悠,我下床掀窗簾,并沒有雷雨,四周一片靜謐。
“蘇姐!”我坐回床上,“是總閘出問題了嗎?”
蘇姐跑到樓道查看,我等了好久,沒靜了。
我走出房間尋,單元門此時完全敞開,狂風刮起客廳的落地白紗,聲控燈失靈,整條走廊像一個漆黑死寂的無底。
我不由慌了神,路過廚房抄起菜刀,一步步蹚著走,“蘇姐?”
我覺自己踩到什麼,趴趴的一坨,我索到壁燈的開關,正要按下,那坨抓住我腳踝,痛苦,“太太,快逃”
我大驚失,急忙反鎖門,忽然一道人影閃過,速度極其迅猛躥到我眼前,我都沒來得及看清,額頭頃刻間被一個冰涼的抵住。
我是有一些見識的,這是麻醉,西北農戶打獵用的,把擊昏,關進籠子里,醒了也跑不了了。
我猝不及防一僵。
男人一副啞的公鴨嗓,尤其在深更半夜,尤為瘆人,“嫂子,您別害怕,我有件事求您。”
嫂子。
林宗易的人。
我面慘白,“你是誰。”
男人不是鄭寅。
“嫂子,我是白喆。”
“吧嗒——”他話音才落,拉保險栓,我不頭皮發麻,全也繃。
察覺我的反應,白喆笑了,“嫂子,我告訴過您,只要配合我,您不用吃苦頭。”他將口挪向我后腦勺,頂住我進電梯,“跟我走一趟。”
我眼神敏捷一掃,電梯里的攝像頭被磚石砸爛了。
白喆是什麼人,我一清二楚。和鄭寅齊名,在濱城,同行發怵他的,手也絕對狠,馮斯乾能制服十個八個保鏢,連白喆三分之一都制服不了,不是一個水平線的對手,白喆就靠過的手闖出名堂。
電梯下降到2樓,我問他,“宗易知道你這樣做嗎。”
白喆沒回答,推著我坐進一輛吉普車。
猜你喜歡
-
完結12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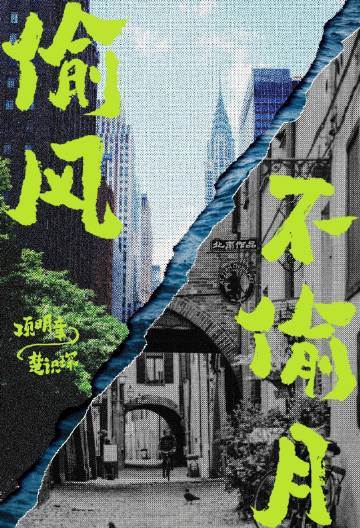
偷風不偷月
穿越(身穿),he,1v11945年春,沈若臻秘密送出最后一批抗幣,關閉復華銀行,卻在進行安全轉移時遭遇海難在徹底失去意識之前,他以為自己必死無疑……后來他聽見有人在身邊說話,貌似念了一對挽聯。沈若臻睜開眼躺在21世紀的高級病房,床邊立著一…
39.3萬字8 6359 -
完結170 章

離婚后,秦少夜夜誘哄求復合
薄棠有一個不能說的秘密:她暗戀了秦硯初八年。得知自己能嫁給他時,薄棠還以為自己會成為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直到,他的情人發來一張照片秦硯初出軌了。 薄棠再也無法欺騙自己,秦硯初不愛她。 他身邊有小情人,心底有不可觸碰的白月光,而她們統統都比她珍貴。 恍然醒悟的薄棠懷著身孕,決然丟下一封離婚協議書。 “秦硯初,恭喜你自由了,以后你想愛就愛誰,恕我不再奉陪!” 男人卻開始對她死纏爛打,深情挽留,“棠棠,求求你再給我一次機會好不好?” 她給了,下場是她差點在雪地里流產身亡,秦硯初卻抱著白月光轉身離開。 薄棠的心終于死了,死在那個大雪紛飛的冬天。
30.6萬字8 5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