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締婚》 第375章 愛情和友情,你選哪一個【6】
且不說。
還有最後一張底牌呢。
寧萱命不久矣。
而寧蘅此刻躺在醫院,就算是醒了,也得半死不活的躺上至半個月。
現在是虛弱的時候。
們倆,到底鹿死誰手。
還不一定。
不過。
不管如何,都怕是再也看不到了……
‘哐啷’一聲,鐵閘門的又被關了起來。
安漾西跌跌撞撞的倒在地上,眼前發虛,眼睜睜看著警員越走越遠
那一刻,恍惚看到了的父親林淮。
當年那場車禍。
是的父親一手促。
為的是徹底滅S國皇室,然後取而代之。
曾勸阻過。
可是父親沒聽。
然後,父親便過勞猝死,悲痛絕下,決意永遠藏這個……
卻不想。
原來傅瑾州早就知道了。
他們的這一生,也不過是一場徒勞的笑話罷了。
應該很快。
就要真正見到他了。
見到他,這一次一定要勸阻他,不要再那麽傻,不要把豺狼當白兔,不要招惹傅家這群人。
Advertisement
還有母親。
忽然記起,甚至還沒來得及跟母親好好告個別。
惟願。
黛娜夫人看在母親服侍多年的份上。
予餘生以長寧。
……
林肯車行駛在通幹道,腳下一片葳蕤流淌的,不停的聚合,離散著。
約莫半小時之後。
傅瑾州回到醫院。
在途中。
他已經向被他派去醫院的元卿詢問過醫院的況。
他並沒有急回到病房。
興許。
是不懂得如何麵對。
途經長廊,長廊傳來一陣嘈雜吵嚷聲,幾個護士推著一位手上掛著點滴的正在搶救的病人,病人臉上帶著氧氣麵罩,護士邊跑邊喊:“趕把呼吸機和除儀都拿過來,旁邊的都讓一下!”
路過傅瑾州旁邊的時候。
傅瑾州側避讓。
無意之間,他瞥了眼病床上正在被搶救的人,病人臉蒼白,脖頸甚至泛紫,看起來像是因為窒息而憋的。
而最重要的是。
這個人……是安容。
傅瑾州下意識眉心微凜,腦中驀地閃過昨天安容被薛知棠推倒在地的那一幕。
他一時竟不知什麽心。
他能理解薛知棠,他同樣想懲罰安容,可是家有家法國有國規,薛知棠三番兩次出手狠辣,未免太不把S國法律放在眼裏。
恰巧。
元卿看見他,走過來,又順著男人的視線,看了眼被推車推走的方向,說道:“剛才安管家想要進夫人的病房,但是被寧夫人趕出去了,隨後沒走兩步,就開始到底呼吸不順,嚨裏像是鯁了東西一樣。”
頓了下。
元卿道:“就和當初蔣翰林的癥狀一模一樣,而且大概率……”
大概率會窒息而死。
大概率是救不回來了。
除非薛知棠給出解藥。
但是薛知棠會給麽?
顯然是不可能。
而且。
憑借醫院這些人,恐怕……
寧遠國還真是有命,竟然這麽放任著這麽一個危險至極的人在邊養著。
這也不知道薛知棠從哪兒學的這些東西,但凡傳揚出去,都是能驚全國駭人聽聞的大事件。
這就是條麗的毒蛇。
一下就咬死人的那種。
元卿想想就心裏發怵。
元卿現在都不想靠近三尺。
元卿甚至覺得這醫院走廊上都不安全了,高低得噴點消毒劑,裏裏外外消一遍毒,不然鼻子裏嗅點不幹淨的,指不定下一個死得就是他。
傅瑾州眉梢輕擰。
這時候。
元卿忽然說道:“對了,閣下請不要擔心,剛才醫生來過了,夫人……剛剛好像醒了。”
猜你喜歡
-
連載601 章

這主播真狗,掙夠200就下播
189.5萬字8.18 8119 -
完結866 章
晝夜關系
追妻火葬場失敗+男主后來者居上+先婚后愛+隱婚+暗戀甜寵+1v1雙潔季璟淮覺得,司意眠是最適合娶回家的女人,他手機里有故事,有秘密,兩個他都不想錯過。可等司意眠真的嫁給了顧時宴,季璟淮才知道,自己到底錯過了什麼,他終究丟了他年少時最期盼的渴望。再次狹路相逢,她如遙不可及的那抹月光,滿心滿眼里都是另一個男人。他的未婚妻,最終成了別人捧在心尖上的月亮。宴會散場,季璟淮拉著她,語氣哽咽,姿態里帶著哀求,紅著眼質問道“你是真的,不要我了。”司意眠只是那樣冷冷看著他,被身邊矜貴冷傲的男人擁入懷中,男人微微抬眼,語氣淡然,“季總,我和太太還趕著回家,請自重。”她曾以為自己是全城的笑話,在最落魄時,被僅僅見過數面的男人撿回了家。后來她才知道,有人愛你如珍寶,你的每一滴淚,都是他心尖肉,掌中嬌。他不舍讓你受一絲委屈。(白日疏離,夜里偷歡,折我枝頭香,藏于心中眠。)豪門世家溫柔專一貴公子x云端跌落小公主一句話簡介京圈太子爺為愛做三
80.9萬字8 80674 -
完結19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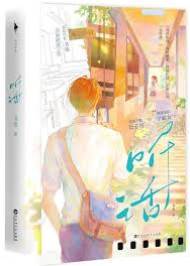
聽話
那不是程歲寧第一次見周溫宴。 她見過他意氣風發,見過他浪蕩不羈,見過他懷裏女孩換了一個又一個。 只是那次,她心動最難捱。 那天室友生日她走錯包間,偶然窺見他懶懶陷在沙發裏,百無聊賴撥弄打火機。 火苗忽明忽暗身旁女生和他說話,他勾着笑半天敷衍回個一字半句。 她回到包廂裏第一次鬼迷心竅主動給他發了信息,【今天聚會好玩嗎?】 下一秒,他回:【你不在沒意思。】 後來他們分手,多年後在風雨裏重逢,她被男友差遣輕視狼狽不堪。 他跨過一衆圍着他殷勤討好的人羣,不顧目光,拉住她的手,塞進一把傘。 冬夜昏天暗地光線裏,他垂眼看她,聲音淡淡:“撐傘,別淋雨。” 那一刻她這才知道,除了他以外都是將就。 朋友問那再後來呢?她淺笑着沒說話。 只是每年西園寺,雲蒸霞蔚煙火繚繞的銀杏樹下多了個虔誠的少女。 那天年初一,青衣僧人說有緣人贈了她一張紙條。 展開一看,字體熟悉,上面寫着‘一歲一禮,得償所願。’ 她下意識回頭,人海茫茫裏,一眼只看見他溫柔背影。
34.2萬字8.18 6027 -
完結192 章

和塑料竹馬閃婚了
樑思憫閒極無聊決定跟季暘結個婚。 儘管兩個人從小不對付,見面就掐架,但沒關係,婚姻又不一定是爲了幸福,解解悶也挺好。 果然,從新婚夜倆人就雞飛狗跳不消停。 一次宴會,兩人不期而遇,中間隔着八丈遠,互相別開臉。 周圍人小聲說:“季總跟他太太關係不好。” “樑小姐結婚後就沒給過季總好臉色。” 邊兒上一男生聽了,心思浮動,酒過三巡,挪去樑大小姐身邊,小聲安慰,低聲寒暄,委婉表達:“男人都不是好東西,但要是我,肯定比季總聽話,不惹您生氣。” 季暘被人遞煙,散漫叼進嘴裏,眼神挪到那邊,忽然起了身,踢開椅子往那邊去,往樑思憫身邊一坐,“我還沒死呢!” 樑思憫嫌棄地把他煙抽出來扔掉:“抽菸死的早,你再抽晚上別回家了,死外面吧。” 季暘回去,身邊人給他點菸的手還懸在那裏,他擺了下手:“戒了,我老婆怕我死得早沒人陪她逗悶子。” 看身邊人不解,他體貼解釋:“她愛我。” 周圍人:“……”無語。
29.4萬字8.18 353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