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先生別虐了,夫人白月光不是你》 第237章 你是誰!你想做什麼?
可前後不過五分鍾,霍喻便發了信息過來。
他隻說自己這兩天有事要做,三天後會來看。
那人總是心,知道溫會有負罪,總會瞎想一些,他說——
小,哥哥很好,有你就算是有了家。
簡單一句話,溫險些淚目。
這幾天經曆的事太多,讓人有種跌宕起伏之。
溫雖然什麽也沒做,但卻累的筋疲力竭。
晚上,洗漱過後就坐在床上任由霍斯年給吹頭發,男人手法嫻溫,眉眼間一派平靜。
溫被霍斯年伺候的有些昏昏睡,瞇著眼打哈欠,眼皮正要瞌下去,耳邊吹風機的翁翁聲忽然停了。
迷迷糊糊睜開眼,霍斯年已經摁著的後腦勺近。
他角勾著笑,上白襯衫還沒下,此刻,溫看到霍斯年這副模樣,臉後知後覺的紅了。
“想你。”
他眼底寫著明晃晃的,這種令人無法忽視的愫湧出雙眸。
他開口,嗓音滿是暗啞。
他輕輕的笑,額頭上溫的額頭,那雙眼底寫滿珍視。
“溫,很想你,很想。”
溫紅著臉蛋咬了咬下,太久沒和霍斯年親近,雖未曾說出那些難以啟齒的話,但每每看到霍斯年,總會一些歪心思。
譬如此刻,盯著麵前男人的模樣,幾乎是克製不住自己心底的衝,先他一步將自己的瓣了上去。
Advertisement
他們雖然做了這麽多年夫妻同床共枕這麽久,再多親的事也早已做過。
可溫向來臉皮薄,幾乎從未有過這樣主的時刻
此時,看到迫不及待吻上來,那一雙眼眨著,瓣上來之後便沒了靜,霍斯年便想笑。
可,僅僅隻是鼓起勇氣做了這樣一個作,自己便已經丟盔棄甲。
他瓣蠕。
“乖乖,閉上眼。”
溫很聽話的將眼睛閉上眼,霍斯年輕笑著,一隻手扣住的後腦勺,另一手將腰錮,近,幾乎是將從床上拽到了自己上。
溫驚呼一聲,心底有些擔憂,害怕自己會弄疼了霍斯年。
可霍斯年毫不在乎,他狠狠吻上來,呼吸急促。
溫被他吻的,很快,白襯衫領口地袖子被扯掉幾顆……
臥室裏,床頭櫃上兩盞睡眠燈散發出淡淡暖黃暈,那一圈圈芒暈染開,增添幾分曖昧的氣氛。
那致的小粒紐扣在兩個人逐漸重的息聲中不知掉到了哪兒。
那細微清脆的聲音惹得霍斯年笑起來。
“那麽急啊?”
溫眼底滿是似水,眼底甚至出一茫然迷醉的姿態。
霍斯年本借著這個機會逗逗他,可誰知自己本堅守不住……
他抓住的手,放到腰間……
“給你,都給你……”
——
解決了梅蘭這個大麻煩,連帶著南梔也沒了,京城的天似乎格外晴朗。
碧空如洗,萬裏無雲。
溫看著手機上的時間,一直等著霍喻出現。
隻是……
距離約定的時間已經到了,霍喻還沒來……
——
這邊,霍喻想走失,卻發現自己渾燥熱,異常已經走不了了。
他隻記得和溫雅雅之間三天約定的期限已經到了,等到兩個人像是完了約定分道揚鑣時。
溫雅雅提出喝一杯。
“沈喻寒,我還是勸你不要逞強,畢竟有些事的真相未必是你能承得住的。”
從三天的假扮男友故事中出來,他便又恢複了往日裏的模樣。
“溫雅雅,希你能說到做到,是時候該兌現你的承諾了,告訴我當年那場突然燒起的無名火究竟是誰放的?”
溫雅雅看著相了三天,以男友視角溫關心了自己三天的人,此刻就那樣決絕的從故事中,恢複了以往的模樣,心中酸痛。
也不該再用這些事綁著他了,是時候該告訴他了。
這三天的快樂時就當是做了一場夢吧。
緩緩開口:“霍喻,你跟我心不在焉,相了三天,其實那個答案早就已經在你心裏了,不是嗎?”
霍喻不可置信的盯著。
“其實,有些時候連我自己都不知道是該你霍喻呢還是沈喻寒。”
“那我是誰?”
這個問題就像是個未解之謎,或許那個答案就在心口呼之出,可他卻膽怯,不敢說出口。
“那把火是梅蘭放的……”
溫雅雅不再賣關子吊人胃口,皺眉,回憶起當年的那件事,那塊在自己心口未挪的巨石……
藏在心底這麽久的終於要和盤托出,隻要說出口了,自己是否也能輕鬆一些?
當年,溫雅雅做了一些虧心事,害怕被人發現便小心翼翼的藏著,躲著。
可誰知有人比還要小心。
抱著懷裏那些東西,在好奇心的驅使下忍不住跟上腳步。
那是自家最近召進來的傭人阿姨。
隻是此刻,那個平日裏低著頭,劉海幾乎蓋住半張臉,在家裏沒什麽存在的傭人阿姨有些鬼鬼祟祟。
當時好奇心重,也不知道怎麽就跟了上去。
剛剛幹了些壞事,本應該往自己房間裏躲,可此刻卻抱著懷裏一堆東西跟上那個傭人。
傭人淡淡笑著,是往溫的房間裏走,溫雅雅更加懷疑了。
隻是,當看到打火機燃起火苗,那火苗點燃了不知道何時已經準備好的引子……
火星子躥,火舌跳躍著,很快邊衝燃上紗製窗簾,一點點朝著書桌上的孩兒燒過去。
當時,溫雅雅親眼目睹了那一幕,竟不知自己為何會袖手旁觀,現如今想起來也隻是因為嫉妒心作祟。
的住了一隻惡魔,而那時,那隻惡魔不斷的在耳邊煽風點火……
“燒吧,燒死那個人!隻要這個討厭的人死了,就沒有人可以跟自己搶哥哥了!”
於是,溫雅雅看著,任由火越來越大。
忽然,麵前的人一點點扭頭,臉上洋溢著病態不正常的笑,那樣令人骨悚然的笑幾乎嚇哭了溫雅雅。
“你是誰,你想做什麽!”
那個人緩緩抬手,食指抵在了邊。
猜你喜歡
-
完結269 章

替嫁豪門,惡魔總裁追逃妻
「少爺,少奶奶逃了!」 「抓回來!」 「少爺,少奶奶又逃了!」 「抓!!!」 「少爺,少奶奶已經沏好茶了,就等著您回家呢。」 「哦?這麼乖?」 …… 一覺醒來,她落入他手中,起初,以為是劫難,原來是她的港灣。 霸道冷酷總裁寵妻成癮,同時化身醋精本精……
66萬字8.53 258553 -
完結692 章

強勢暖婚:總裁別撩我
作為一個編劇居然要,現場指導情色片!還碰上一個帥的驚天地泣鬼神的男神! 白木嵐,你這都是什麼運氣啊,臉都沒了! 回家還被逼婚,什麼?結婚對象是那個聽到我說騷話的男神! 不可能吧! “這是真的哦,你已經被你的家人賣給我了哦!” 天上掉餡餅了?...
92.3萬字8 23722 -
完結494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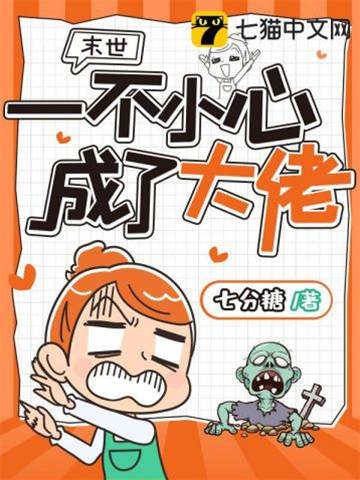
末世一不小心成了大佬
她在末世掙扎五年,殞命瞬間卻回到了末世剛開始,恰逢渣男正想推她擋喪尸。她踹飛喪尸,準備再掀一次渣男的天靈蓋!囤物資,打喪尸,救朋友,她重活一次,發誓一定不會讓任何遺憾再次發生。不過周圍的人怎麼都是大佬?殊不知在大佬們的眼里,她才是大佬中的大佬。
75.3萬字8 11226 -
完結121 章

吻奈
[嬌軟可人妹妹VS溫潤如玉哥哥] [7歲年齡差、相互治愈] [男主後期開葷後屬性變狼狗] [女主患有輕度抑鬱癥和重度幽閉恐懼癥] “怎麽了?不舒服嗎?” 林景明俯下身,手悄悄摩挲著桑奈的細腰。 “哥哥……” 男人臉上卻一本正經地問道。 “哪裏不舒服?” 桑奈看了一眼落地窗外來來往往的人,又將目光移向林景明。 “別......” 桑奈的聲音帶了一點哭腔。 哢噠一聲,空氣跟著靜止了。 “外麵能看見。” “是單麵。” 林景明的吻落下。 他向來是溫潤如玉,自持風度。 但此時的他已經失去理智。 “乖,叫我名字。” …… 從那年小桑奈遇見林景明。 兩人不死不休的羈絆就開始了。 桑奈受了傷永遠隻會偷偷躲起來舔舐傷口。 後來,有人看穿了她的脆弱,她緊緊抓住了那雙手。 她一直纏著他叫哥哥,哥哥一直想方設法地保護好妹妹。 殊不知桑奈早就已經芳心暗許。 桑奈此生,非景明不嫁。 到後來… 景明此生,非桑奈不娶。 想吻你,奈我何。
20.9萬字8.18 5769 -
完結39 章

封爺,你家夫人野翻了
表面上秦忘憂是個智力低下的傻子,可誰都不知道這個傻子在私底下有多麼的殺伐果斷。傳言中能從閻王手里搶人的神醫,是她!讓人驚訝的商圈新秀天才投資人,是她!一己之力把股市攪的天翻地覆的人,是她!以為就這麼簡單?那你錯了,神級作家,秀翻全場的電競之王,酷跑達人,頂級電腦高手Q神也是她!
6.3萬字8 7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