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溫誘吻》 第104章 他不冷淡
江喬還沒反應過來。
裴知鶴滾燙的薄落下,疏離的木質香水味與酒氣融,鋪天蓋地覆蓋下來。
江喬微的杏眼驀地睜大,卻怎麽也對不上焦,恍惚間貝齒被輕易撬開,所有的緩衝和準備時間都被清零,一切的領地被男人瞬間侵占。
他骨節分明的大手用力。
指尖一點巧勁,就讓被迫仰起臉,脖子也隻能按照他的意願,乖乖迎接這場突如其來的驟雨。
腦子裏暈暈的,約約地覺得不太公平。
的“親一下”隻是帶著點試探的小打小鬧,而裴知鶴所謂的親一下,和所想的完全是兩碼事。
太兇猛,也太焦灼。
不加掩飾的掌控,像是一種真正的教育或懲戒。
的而麻,子也快要被碎在他的懷裏,從未有過的窒息,但又奇異的安全。
像是要溺斃在一片洶湧的海水裏,齒間無意識地溢出黏膩的鼻音,耐不住地了兩下,被裴知鶴的大手牢牢地鉗住。
“別。”男人修長的指尖揩去角的水,聲線得極低,帶著金屬質地的顆粒。
江喬恍然記起自己還在飛機上,乎乎地和他抗議:“……我想睡覺了。”
裴知鶴黑眸微瞇,很好心地提醒道:“剛剛不是還說,想和他親親?”
江喬頓了一下,含著水汽的雙眸失了神。
像是很認真地思考了一會,最後發現他好像說的全是真的,不是會隨意哄騙的壞人。
然後,全然忘記了自己仍在發麻的舌,咽了下嚨,很慢很乖地,輕輕點了下頭:“要親親的。”
裴知鶴勾起角,聲線溫到極致:“喬喬好乖。”
細的驟雨又下了起來。
像是限時複活的夏夜,落在寒冷的西伯利亞上空。
Advertisement
近到不能再近的距離裏,裴知鶴金屬質地的鏡架冰冷,偶爾會涼到的臉,激靈一下,好像快要醒了,轉瞬又被上潤的熱源占據。
思維被甜甜的酒麻痹,的腦子裏像是有草莓油味的蒸汽雲,蓬鬆鬆的一朵又一朵,互相撞又彈開,讓陷了越來越深的混沌。
意識的最後幾秒清明,好像聽到他輕歎了一聲。
-
江喬睡醒的時候,已經是柏林時間早上七點。
屏幕上的小飛機終於移到歐洲大陸。
今年的聖誕季有雪,實時天氣圖上雲籠罩,大大小小的雪花落下。
頭倒是不怎麽疼,就是困。
江喬瞇著眼睛,本能地去手機。
手在毯子下麵越越遠,手機沒到,先到了一條屬於年男人的大。
羊西裝的昂貴質,布料下的溫熱,結實而有彈。
幾乎是一瞬間。
僅存的睡意飛得無影無蹤,騰得一下坐起子,毯落,細白的手臂猝不及防地接到變冷的空氣,起了一層皮疙瘩。
“冷的話就穿上。”
邊人遞過一件西裝外套,熨燙得,沒有一褶皺。
慌慌忙忙地披上,轉過看他。
江喬瞬間僵住:“?”
才這個點,他怎麽已經是一副充滿了電的模樣,這人完全不睡覺的是嗎?
裴知鶴還穿著昨天那件襯衫,上直,袖口和領帶一不茍,溫莎結拉到最上,挨著飽滿的結。
冷白的手指修長,翻書頁的間隙裏,很自然地,輕輕推了一下金邊鏡架。
疏離的高嶺之花,完到無懈可擊。
除了……他襯衫的肩膀,明顯到讓人無法忽視的褶皺。
那個形狀,比起睡覺出來,好像更像是……被誰抓出來的。
江喬心虛地咽了一下口水。
裴知鶴緩緩轉過頭,在辦公燈的冷裏微側過臉來看,語氣平和而尋常:“洗漱一下,回來吃早餐。”
江喬:“……好。”
拎著洗漱包快步走去洗手間,鏡子明亮而幹淨,映出白的一張小臉。
隻有一點點的浮腫,看起來還可以。除了頭發有點,下有一道很細小的傷口,子也起了皺。
頭發用鯊魚夾簡單攏起,清涼的水撲在臉上,零星回憶的細節慢慢浮現在腦海。
好像是先看了電影,一邊哭一邊喝了一瓶酒,然後話比較多找裴知鶴……聊了兩句?
又……抱著人家睡了一覺?
可到底聊了什麽,中間又做了什麽啊……
江喬拿起巾臉,蘋果皺一團,心中大呼救命。
是喝到斷片了,但是裴知鶴滴酒未沾,全程都清醒得很。
不過看他剛剛那個態度。
應該也……沒做什麽特別過分的事。
看來人真的不能未經測試就過於相信自己的酒量,小時候還覺得江玉芬兩杯啤酒就倒很誇張,如今想來,自己也好不到哪裏去。
回到包廂裏,早餐已經送了過來。
裴知鶴拉開桌板,長指將兩份餐都推到江喬麵前,讓先選:“想吃哪份,中式還是西式?”
江喬是完完全全的東方胃,西餐不是不能吃,但連吃不了太久。
想到接下來接近半個月的行程,沒怎麽猶豫,慢吞吞地湊過去,接過那個致的漆餐盒。
坐下時,綠的開衩款擺,泄出一線雪般的潔。
裴知鶴很自然地接了挑剩的西點,藝品般漂亮的手指拿起刀叉,吃相矜貴優雅。
江喬夾起一隻蝦餃,咬了一小口,努力表現出自然的樣子:“……晚上的歡迎宴會,我有什麽需要注意的嗎?”
“一直跟在我邊,別走遠,幾個歡迎致辭盡量翻,可能還有一點很隨意的際,不用張。”裴知鶴輕啜一口咖啡,抬眸看,又斂下去。
唔,聊工作話題的裴醫生。
好。
江喬眼神落到他眼瞼下的淚痣上,纖長的睫抖了抖,強行控製著自己,不在他麵前出太癡漢的表。
可能是的視線太熱切。
裴知鶴側過臉來垂眸看,眼角有些玩味地微抬,讓心尖一麻:“還有一件最重要的事,希江小姐能注意一下。”
被這個過於鄭重的稱謂點到,江喬猛地坐直:“……你說。”
他剔亮的眸子從鏡片後掃了一眼,莞爾道:“別喝酒。”
“除了在我邊三步以,一滴都不許喝。”
他頓了一下,語氣極認真地補上:“旁邊如果有長得像我的男人,絕對,不許帶酒的飲料。”
江喬眼前一黑,心虛得恨不得原地開窗跳下去。
徹底完了。
雖然也沒聽懂,什麽長得像他不像他的。
但剛剛的覺良好純屬自負行為,昨天晚上絕對是發表了什麽虎狼之詞。
絕對的。
以至於連裴知鶴都擔心國出醜,親自來酒執法了。
“那什麽……”眼睛心如死灰地閉了閉,嚅囁道,“……我昨天還幹了什麽大逆不道的事,你直說好了,長痛不如短痛,我承得住的。”
上鬆鬆披著他的正裝外套,很寬大,兩隻手像小孩子一樣在袖子裏,隻出在外麵的一點點指尖。
裴知鶴玉白的指關節屈起,好整以暇地抵在下上,像是認真地思考了幾秒,才道:“其實也沒你想的那麽糟糕。”
江喬鬆了口氣。
可一口氣還沒下去,就聽見男人慢悠悠繼續道:“也就是提了幾個問題。”
“有的小朋友昨天喝醉了,所以現在告訴。”
前敞開的前襟倏地被拉起,頓時愣住。
西裝冰涼的襯很,過口的理,將那片綠的春意遮住。
江喬下意識地往後麵了。
但退一寸,那隻漂亮的大手便進一寸,直到前襟中間的一顆扣子被鎖住,緩慢而紳士地扣好。
他的袖口平整地住腕骨,一皮都沒有出,但那雙冷白的手背上青筋凸起,蟄伏的脈絡明晰,有一種斯文而矛盾的。
裴知鶴疏淡狹長的黑眸認真看著,直到耳朵都快要燒起來了,才沒頭沒尾地說:“我不冷淡。”
江喬沒聽懂,但臉頰依然不由自主地發紅,口問:“……什麽?”
他視線掃過下上的小傷口。
眸微暗,角卻紳士地勾起,溫文雅重:“沒什麽。”
猜你喜歡
-
完結23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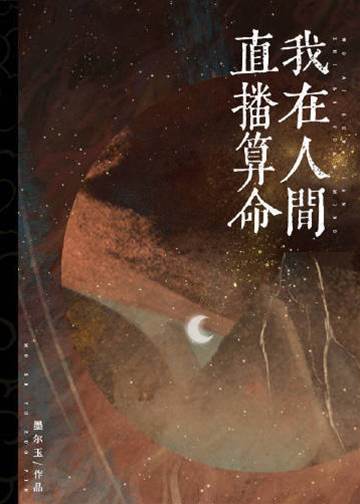
我在人間直播算命[玄學]
安如故畢業回村,繼承了一個道觀。道觀古樸又肅穆,卻游客寥寥,一點香火錢也沒有。聽說網上做直播賺錢,她于是也開始做直播。但她的直播不是唱歌跳舞,而是在直播間給人算命。…
134.6萬字8 8284 -
完結89 章

婚后肆愛
趙璟笙初見顧筠,是在父親的壽宴。狗友指著一女孩給他看,戲謔:“二哥不上去打個招呼?保不齊就是您未來小嫂子。”女孩挽著他大哥,玉軟花柔,美艷動人。他冷漠地喝光杯中酒,生平第一次對女人動了心思。既然想要,就奪過來。…
35.8萬字8 32625 -
完結232 章

閃婚,一窮二白的老公露出真麵目
【極致婚寵,追妹火葬場,又撩又欲,高甜爽】薑笙是薑家流落在外的女兒,卻因為養女的受寵,永遠得不到薑家人的正眼相待。為了徹底擺脫薑家,她選擇了相親。一場相親宴,她認錯了人,挽著最神秘也最尊貴的男人領了證。謝家,華國最神秘也最富庶的家族,在謝時景眼裏,薑笙纖腰撩人,身嬌體軟,在他心尖縱了一把火。在薑笙眼裏,他隻是個普通醫生。誰知表麵衣冠楚楚,私下是個餓壞了的野狼。謝時景低笑:“謝謝夫人,讓我可以身體力行地疼愛你一輩子。”當她決定徹底遠離薑家,哥哥和父母,卻後悔了……
41萬字8 70988 -
完結744 章

他的金絲雀又嬌又軟
【偏執/火葬場/甜虐/重生/瘋批】 祁湛嘴角噙著一抹耐人尋味的笑,跨著步子將她逼到了角落。 沈書黎臉色慘白,紅潤的嘴唇顫抖著。身體抖如篩子。男人愛極了她這副模樣,抬手就撫摸上她柔軟的臉頰。 溫熱的觸感讓她眼眶濕潤,腳開始發軟,跑不掉了這一次,徹底跑不掉了…… “乖乖,我想你了。”他的聲音,讓女人整個人往后跌去,這是絕望最后的吶喊,也是她失去自由的開始。 男人上去攬住她纖細的腰肢,將她整個人拉了回來,他身上沁人的古龍水香味,讓她打了個冷顫,這個惡魔他追過來了。 “放了我吧。”她哀泣,梨花帶雨的倒進了他寬闊的懷抱里,痛苦間又無可奈何。 “乖乖,你永遠都只能留在我身邊。” “當我一輩子的乖乖,給我生個孩子。” “好不好?”
78.3萬字8.18 813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