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玉翻香》 第十八章 重生(十七)
嚴祺從小自視甚高,覺得自己這等出,定然不能被那些不如自己的人比了下去,建功立業,將高侯的門楣發揚大。到那時候,所有人都會對他畢恭畢敬,不會再有人嘲笑他是個外戚紈绔。
然而這志向雖大,奈何嚴祺確實是個外戚紈绔。他有許多小聰明,卻不肯放在正道上,只想著與高門結,互相吹捧。嚴祺自己也知道,自己當下的職,是皇帝看在年之誼的分上給的,可他對此沾沾自喜,覺得這也是自己的本事。
“既如此,你可想好了,漪如說的那滅門之禍,又當如何去解?”容氏毫不客氣地將一盆涼水當頭澆下。
嚴祺愣了愣,不由看向案頭那本當寶貝一般捧著的《解夢方要》。
容氏嘆口氣,將那些神仙畫卷和書都收起來。
“你啊,”說,“總琢磨這些有的沒的是。子不語怪力神,果真有捷徑,也要你憑本事去走一走才能知道。天下第一,豈有在家抱著兒就能贏過別人的?”
Advertisement
嚴祺一時說不過容氏,見繃起臉,只得討好道:“道理我自是知道,不過想一想罷了,急什麼。”
容氏見他擺出一副賴皮臉,頗是無奈。
心里念著漪如,也不多言,起走到漪如房里。
*
如容氏所料,漪如還未睡去。
向來如此,到了晚上總要纏著陳氏或容氏,讓們講故事,哄著睡。
不過今日卻是不一樣。陳氏在外間已經睡得沉沉,漪如躺在里間,仍然睜著眼。
“怎還不睡?”容氏和躺下,問道,“可是帳中進了蚊子?”
漪如著,眼睛里閃著奇異的。
“不過是太熱了,睡不著。”說。
容氏笑了笑,將一旁的葵扇拿起來,輕輕扇。
涼風在紗帳里流,帶著容氏上的香味。
漪如呼吸著,忽而有了些恍惚之。
這景,似乎并非在眼前,而是隔了許多年。
那時,容氏就是這樣輕地說著話,伴著睡。漪如每每閉上眼睛,總是說不出的安穩。
忍不住,出手,環在容氏的腰上,與在一起。
“怎麼了?”容氏笑嗔道,“方才說熱,著母親便不熱了?”
“不熱。”漪如道,“母親,我想以后日日這麼跟著你睡。”
“冤家。”容氏道,“你跟著我睡,阿楷怎麼辦?腹中還有你三弟,你們姊弟三人在一,母親便要熱死了。”
你腹中的不是三弟,是三妹。漪如不由地在心里道,臉上卻出笑意,將容氏抱得更。
容氏一手打著扇子,一手輕輕地了的頭發,片刻,輕聲道:“漪如,你在你父親面前說的那些話,都是真的?”
漪如抬頭。
容氏看著,目認真。
漪如知道,母親和父親不一樣,不容易被唬住。“自是真的。”漪如委屈道,“母親不相信我?”
容氏低低嘆了口氣。
“母親怎會不信你?”說,“你雖總惹禍事,但在母親面前未曾說過謊話。我是怕你心里藏了什麼事,不敢跟母親說,卻拿那什麼仙人來唬人。”
猜你喜歡
-
完結1099 章
鳳女重生:侯爺夫人要複婚!
前世,許瑾瑜將豺狼虎豹當成了良人,闔府被斬首,自己也落得個葬身火海的下場。最後她才知,那個冷心冷情的人將自己愛到了何等地步。重活一世,許瑾瑜想要馬上上了花轎,跟那人和和美美的過完這一生。可是還冇走兩步,就看到了那人,一本正經的說道。“雖家父與叔父早已有言在先,可婚姻大事並非兒戲,既大姑娘不願,我亦是願意就此解除婚約。”許瑾瑜握緊了自己的小拳頭,眼裡起了一層薄霧,直接噠噠噠的走了過去。“侯爺戰功顯赫,為世人敬仰,理應知道流言不可儘信,現如今又怎可因為流言就要解除婚約呢?”孟敬亭冷心冷情,從未對任何人動過心,可是卻被這眼前的小姑娘給軟了心腸。
131.7萬字8 50226 -
完結77 章

奪金枝(重生)
虞莞原本是人人稱羨的皇長子妃,身披鳳命,寵愛加身。 一次小產后,她卻眼睜睜看著夫君薛元清停妻再娶,將他那個惦記了六年的白月光抬進了門。 重活一次,本想安穩到老。卻在父母安排的皇子擇婦的宴會上,不期然撞進一雙清寒眼眸。 虞莞一愣。面前此人龍章鳳姿,通身氣度。卻是上輩子與薛元清奪嫡時的死敵——模樣清冷、脾氣孤拐的的薛晏清。 迎上他的雙目,她打了個哆嗦,卻意外聽到他的一句:“虞小姐……可是不愿嫁我?” - 陰差陽錯,她被指給了薛晏清,成了上輩子夫君弟弟的新娘。 虞莞跪于殿下,平靜接了賜婚的旨意。 云鬢鴉發,細腰窈窕。 而在她不知道的上輩子光景里—— 她是自己的長嫂,薛晏清只能在家宴時遠遠地看她一眼。 再走上前,壓抑住眼中情動,輕輕喚一句:“嫂嫂。” 【又冷又甜薄荷糖系女主x內心戲起飛寡言悶騷男主】 1V1,男女主SC 一些閱讀提示:前期節奏有些慢熱/女主上輩子非C,介意慎入 一句話簡介:假高冷他暗戀成真。 立意: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
20.2萬字8 39694 -
完結139 章
我以為我拿的救贖劇本
一朝穿越,虞闕成了修真文為女主換靈根的容器。好消息是現在靈根還在自己身上,壞消息是她正和女主爭一個大門派的入門資格,她的渣爹陰沉沉地看著她。虞闕為了活命,當機立斷茍進了一個不知名的小門派。入門后她才發現,她以為的小宗門,連師姐養的狗都比她強…
62.6萬字8.33 16859 -
完結10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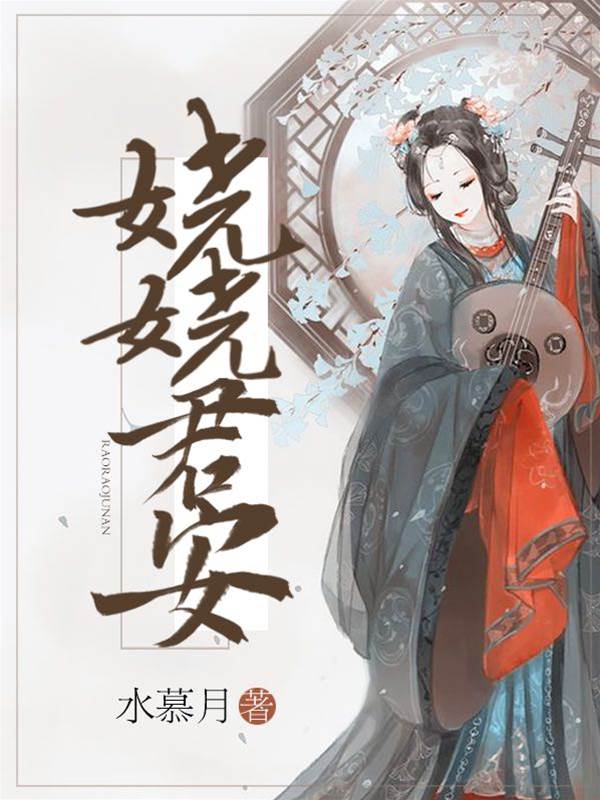
嬈嬈君安
原想著今生再無瓜葛,可那驚馬的剎那芳華間,一切又回到了起點,今生他耍了點小心機,在守護她的道路上,先插了隊,江山要,她也絕不放棄。說好的太子斷袖呢!怎麼動不動就要把自己撲倒?說好的太子殘暴呢!這整天獻溫情的又是誰?誰說東宮的鏡臺不好,那些美男子可賞心悅目了,什麼?東宮還可以在外麵開府,殿下求你了,臣妾可舍不得鏡臺了。
16.6萬字8 1482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