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明后認錯夫君》 第243頁
青年沒有回應。
阿姒搖搖頭,看來他是真累了。
翻個,亦合上眼。
.
醒來后,晏書珩已不在。
阿姒一問,才知道在此期間,城外經歷了數度戰,胡人見周軍士氣正盛,已向東南退至潁。
殷犁打算乘勝追擊,把他們趕出潁川。兵貴神速,當日,大軍便出離了翟,出城十里,經過陳家祖墳時,晏書珩握住阿姒的手。
“形勢多變,這一去,恐怕又要一年半載才能回潁川,要再去祭拜祭拜岳丈大人麼?”
阿姒白他一眼,在反相譏和裝聾作啞中選了后者。
長指挑開簾子又落下:“不必,爹爹若在天有靈,只會催我們快些行軍,莫誤了戰事。”
兵馬趕到潁。
殷犁的確用兵如神,雖人數限制,但只三日,便把潁的胡人擊退至臨潁。大軍亦隨其后,跟到了臨潁,與胡人決一死戰。
這日黃昏,天邊云霞如火。
兩軍暫且休戰,都雙方迎來了短暫的息時刻。
晏書珩回來了,還帶回些炙烤過的野味,及兩壇三春寒。
Advertisement
看到三春寒,阿姒很是驚訝:“這不是我挖出的那兩壇酒,先前落在了翟,怎會落你手里?”
晏書珩溫和解釋:“從翟回來的探子捎帶回的。戰事正,今日先不飲酒,飲些茶水吧。”
阿姒接過兩個酒壇收好。
晏書珩耐心給把山的骨頭剔去,小心得仿佛是三歲孩,還懵懂得不能自己吃飯。
阿姒夾著香噴噴的,吃得有滋有味,上卻說:“不必如此,我哪有這麼氣?”
晏書珩又剔去一塊骨頭,漂亮的長指連沾著油腥都是賞心悅目的:“并非阿姒氣,是我想讓你盡可能無憂無慮,什麼都不必擔心。”
阿姒手中筷子在空中頓了下。
這幾日他的確是什麼也不讓管,連問起戰況,他都只說:“一切皆好,不必擔憂。”
甚至還以貌若神,出門會讓將士們分心、讓他吃味為由,哄著好好在宅邸中歇息休養。
念在他辛苦的份上,阿姒也順著他的心思去了。
咽下一口。
晏書珩遞來一杯剛泡好的茶水:“油膩,飲些茶解解膩。”
阿姒端起茶杯,放到邊,嗅了嗅:“這茶真好聞。”
晏書珩寵溺笑笑:“這是方圓十里最好的茶,僅此一杯。”
阿姒淺淺抿了口,輕嘆:“想想你待我可真是不錯,只是你現在對我越好,將來一旦稍有松懈,我可就要認為你是變了心了。”
說完,指尖在桌上敲點。
“知道了麼?”
晏書珩好脾氣道:“在下教,必謹記阿姒教誨,持之以恒。”
阿姒以袖掩面,毫無閨秀之儀地把茶一口飲盡,又了角的水漬:“我還要吃。”
晏書珩又剝了些遞上。
茶足飯飽,他溫的目也看得阿姒飄飄然打了個哈欠:“我倦了,你且忙自個的去吧。”
起到躺椅上歇息,晏書珩并未離開,他看了看周遭,并無茶水傾倒的痕跡,上亦干爽。
想來是真喝完了。
晏書珩目沉浮,靜靜凝著,從烏黑的發,到纖細腰肢。
把的背影一遍遍刻在腦海。
仍是覺得不滿足。
他起,來到安睡的郎跟前,握住的手,竊奪屬于的溫度。
還是不夠。
晏書珩抱起阿姒,摟在懷中。
他細細端凝的眉眼。
在上面落下輕吻。
末了,又更地把摟懷中,仿佛這是他們之間的最后一刻。
如何相擁才不會留有憾?
十指與的扣嵌合,深深吻住,舌與的纏,直到氣息微,晏書珩才離,他眉目溫地替阿姒把衫和釵發理好。
“對不起,又騙了你。”
他抱著阿姒走到外頭馬車上。
輕放下沉睡的郎,又替蓋上薄薄一層蠶被。
晏書珩召來侍婢:“該吩咐的我已吩咐過。記得好生照顧郎,脾胃差,每日叮囑睡前進食。”
侍婢恭謹應下,青年俯,想在阿姒額上落下一吻。
但最終他只輕臉頰。
“又不是再也見不到,我究竟在不舍些什麼……”
他自哂輕嘆著,下了馬車。
破霧已在旁候著。
晏書珩道:“你們都是我心栽培的銳,我的人便托付給諸位了。”
破霧拱手:“屬下遵命。”
馬車駛離,車后護送的數百銳的影也消失在窄道中。
晏書珩看了眼,毫不猶豫地翻上馬,隨護衛離去。
.
回到營帳,殷犁神凝重。
“依照探子的消息,羯人的確是說服了慕容凜,難怪他們僅剩三萬兵馬,竟有底氣在此僵持!”
晏書珩看著輿圖:“祁家太過急功近利,一心要先奪立威,羯人和北燕想必也看出來了,在此時趁機奪潁川,還可截斷祁家退路,可謂一舉兩得。對祁家而言也是如此,他們知道我們會死守潁川,因此毫無顧忌,想借我們消耗羯人。”
殷犁忍不住啐了一口:“當初雍州之戰時,殷家從中作梗,我和二公子便是因這樣的原因延誤了戰機!如今殷氏倒了,又來個祁氏!”
小士:如果覺得不錯,記得收藏網址 或推薦給朋友哦~拜托啦 (>.
猜你喜歡
-
完結1463 章

農女福妃名動天下
一朝穿越溫暖成了十裡八鄉有名的瘟神、短命鬼,一家人被她拖累得去住草棚,許多人等著看這一大家子熬不過這個冬天,不是餓死就是凍死! 可是等著等著,人家買屋買田買地又買鋪.....
265.7萬字8.46 593469 -
完結120 章

深宮繚亂
我見過最壯麗的河山,也擁抱過最美的情郎。 *雙向暗戀,非宮斗, 架空清,不喜勿入 。
46.8萬字8 7413 -
完結936 章

腹黑毒妃她又甜又颯
醫學博士南宮毓實驗過程中意外死亡,誰知道意外綁定系統空間,一穿越過來就被渣王慘虐?真以為她好欺負?不過不怕,系統在手,應有盡有,且看她如何玩轉皇宮。渣王有白月光?她還就不想做這朱砂痣,帶著崽游走四方暢快淋漓,某王在家哭到扶墻,“愛妃,本王有疾,需良藥一伎。”
87.1萬字8 35362 -
完結52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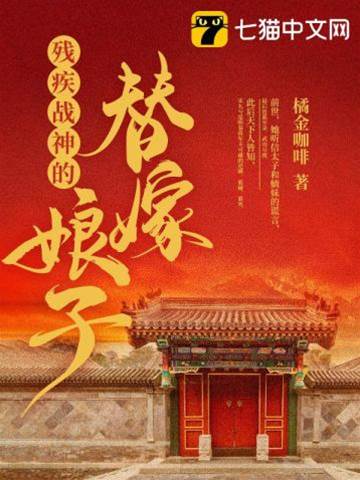
殘疾戰神的替嫁娘子
【重生+男強女強+瘋批+打臉】前世,她聽信太子和嫡妹的謊言,連累至親慘死,最后自己武功盡廢,被一杯毒酒送走。重生后她答應替嫁給命不久矣的戰神,對所謂的侯府沒有絲毫親情。嘲笑她、欺辱她的人,她照打不誤,絕不手軟。傳言戰神將軍殺孽太重,活不過一…
97.6萬字8.18 35390 -
完結187 章

清穿團寵小皇后
佟佳玥作為家中這一輩唯一的女孩子,從小過的那就是團寵的生活。姑姑佟佳皇后深受皇上寵愛,把佟佳玥捧在心尖尖上,宮里只要有人敢欺負她,第一個站出來整肅后宮。祖父佟國維權傾朝野,朝中哪個蠢貨敢說一句他孫女不好的,他便聯合門生,彈劾他祖宗十八代。哥哥舜安顏文武雙全,深得康熙爺喜歡,更是個護妹狂魔,妹妹喜歡什麼,他全都記在心尖尖上。至於表哥愛新覺羅胤禛?從小跟她一起長大,永遠站在前頭保護著她,只是外人都說佟佳玥表哥為人冷漠,不苟言笑?那都是假的!在她面前,表哥就是全天底下,最最溫柔的人!
57.6萬字8 12194 -
完結729 章
東風第一枝
葬身火場的七皇子殿下,驚現冷宮隔壁。殿下光風霽月清雋出塵,唯一美中不足,患有眼疾。趙茯苓同情病患(惦記銀子),每日爬墻給他送東西。從新鮮瓜果蔬菜,到絕世孤本兵器,最后把自己送到了對方懷里。趙茯苓:“……”皇嫂和臣弟?嘶,帶勁!-【春風所被,第一枝頭,她在他心頭早已綻放。】-(注:無血緣關系無血緣關系無血緣關系,重要的事情說三遍!)
97.7萬字8 897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