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聽風聽雨,卻不聽我愛你》 全部章節 53
從牛排店運著麻袋到了若河,車上的人下來,直接抬著麻袋裝著的人往暗窯子去。
徐五混跡於若河多年,周圍的人都是悉的,突然看到這幾個人肩而過時,徐五皺了皺眉。那四個人抬著一個被黑麻袋罩著的人,從徐五邊路過時,聽到裏頭傳來的細微聲響,讓他判斷出,裏麵被抬著的是個人。
若河這一帶的暗窯子不,裏麵的人有的是從外地被拐來,有的是無家可歸主過來的,徐五自小被季鬆救下來之後,他常常施以援手,徐五從暗窯子手上放走的人不在數。
正在前麵帶路的人見徐五停下來,不由得問道,“五爺,看什麽呢?”
徐五收回視線,拍了拍他的肩膀,“沒事,走吧。”
然後在暗地裏給鬆子比手勢,鬆子跟著他這麽多年,早就對他悉的很,見他停下來,鬆子就知道他要幹什麽了。見到他的手勢,鬆子會意,連忙悄無聲息的從徐五後離開,跟上了剛剛那些人。
鬆子悄無聲息的跟在他們後,四個人轉悠了兩圈,就走到了一家暗窯子前,三個人看著麻袋裏的人,另一個則去敲門了。現在是白天,暗窯子的營業並不分晝夜,有人來就營業。幾個人等了一會兒,就有個三十多歲的男人,著眼睛拉開門。
他們這些暗窯子裏人的來源,一向都和比較悉的人易來的,老板表閃了幾分厭惡,很快就收斂起來。
“你們可好久不來了,這次送來的又是什麽貨啊?”
“羅老板,這次送來的可是個極品。”
被稱為羅老板那人呸了一聲,“你們次次這麽說,不就是想多要點錢嘛,說吧,這次要多?”
“這次不要錢,上頭的和有仇,要讓被**之後再要的命。你一次多安排幾個人,給來點刺激的,到時候直接把人弄死就好了。”
Advertisement
他們做這門子生意的,為了多賺錢,肯定是希們接的客人越多越好,哪會有想直接弄死的。
羅老板皺眉,“這的給戴綠帽子了?這麽恨。”
“這我們哪知道啊,上頭怎麽吩咐就怎麽辦事唄。羅老板,要不先驗驗貨?”
說著,四個人合力,將麻袋給掀開,出裏麵的人來。裏麵的人披散著頭發,皮白皙帶著彈,五致的如同雕琢過,材苗條,卻凹凸有致,該瘦的地方瘦,該滿的地方滿的很,就是右手上著夾板綁著繃帶。
見羅老板目都看直了,那人嘿嘿一笑。
“羅老板,我說是個極品吧?”
羅老板收回視線後,眉頭皺的更深了,這個人雖然看著狼狽,但上的服卻看得出來很昂貴,不像是普通人。他能在這紮多年,多半原因是新宮的庇佑,但現在新宮被毀了,他有些猶豫了。如果,不小心得罪了得罪不起的人,他會不會連立足的地方都沒有。
心裏雖然想了這麽多,但臉上並沒有表現出來,讓他們將人抬進了屋裏。
鬆子在暗呆著,清楚的看到了麻袋裏麵的人,臉上的嬉笑轉為震驚,他剛剛沒看錯吧,那個人竟然是季煙?
這是得罪誰了?怎麽才幾天不見,就淪落到這個地步了。
等到人都走完了,鬆子才從暗走出來,敲開剛剛那家暗窯子的門。
羅老板以為他們去而複返,罵罵咧咧的打開門,“你們幹事就他媽不能利落點……”見到是鬆子,羅老板止住了聲音,愣了愣,飛快的回過神,隨即像是明白了什麽,“你認識那的?”
鬆子沒瞞,“老羅,是三爺的兒。”
羅老板麵異,徐五在他這裏帶走的人也不了,但從來沒用過這樣的借口,“你唬我呢,季三離開若河多久了,兒怎麽會在這裏。”
鬆子不知道該怎麽和他解釋季煙來的原因,他隻知道,現在必須把人帶走。要是被傅容兮找到這裏,他那個睚眥必報的格,老羅在這裏絕對沒活路了。
若河這條巷子的人,生活的久了,都互為相依為命的兄弟,鬆子可不想他因此喪命。
“你趕把人給我吧,不會讓你吃虧的。”
鬆子不由分說的進了裏麵,季煙昏迷不醒,正躺在一張木板床上。鬆子走過去探了探的鼻息,確定還有呼吸,倒了杯水喂到裏。
正昏迷著,水出來大半,隻有小半喂進了裏。
這點水已經像是救命稻草了,季煙被水滋潤後,暈暈乎乎的覺唄衝散了些,睜開眼睛,視線迷離的掃了一圈,最後目落在鬆子臉上。
試探的了一聲,“鬆子?”
聲音又輕又啞,又咕嚕咕嚕灌了好幾口水,再重新開口時,語調變得正常了許多,“我怎麽會在這裏?”
“我還想問你呢。”鬆子沒好氣的說。
一直被忽視的羅老板咳嗽了兩聲,外麵突然傳來砰砰砰的敲門聲,鬆子連忙將季煙扶起來,張的說,“不會是他找來了吧。”
“我去看看是誰敲門,你們先去裏麵的屋子。”
羅老板看著鬆子和季煙進了裏麵的屋裏,才走到門口,剛把門打開了一半,裏麵的人就衝進來,“剛剛給你的人呢?”
衝進來的人,正是剛剛將季煙送過來的那四個人。羅老板見他們去而複返,就知道這件事鐵定不簡單。既然鬆子說那是季三的兒,他現在肯定是向著鬆子這邊的。
羅老板冷哼,“你們這人都送過來了,哪還有帶走的道理,我都已經安排好人了。”
一聽說他已經安排了人,害怕這人真被弄死了,到時候那位可就換不回來了。想到那位的子,幾個人臉變了變。著急的拉著羅老板,“不,現在還不能傷。現在在哪裏,趕帶我們過去。”
羅老板哼聲更大,“你們可真有意思,一會兒讓人把往死裏弄,一會兒又說不能傷。你們當我這裏是菜市場啊,還能討價還價的?”
能和他們合作這麽久的人,他們自然不會輕易撕破了臉皮,能好好出來他們也省事一點。
“您把人出來,我們按人頭折算就好了。”
“這還差不多。”
羅老板帶著人上了樓,在路過一樓房間的時候,過門使勁對鬆子使眼。
鬆子一直趴在門口注意外麵的靜,接收到老羅的暗示,看著幾個人的影在樓梯上消失後,才帶著季煙走出屋子。
剛走出大門,卻發現那幾個人回來時,並不隻有四個人。門外還停著一輛車,裏麵不知道坐了幾個人。鬆子乍一看見外麵的車子,嚇得了回來。
好險季煙還沒走出去,不然他們肯定被發現了。
“怎麽了?”季煙蒼白著臉,張不已。
好在這屋子還是有後門的,鬆子沒說話,直接帶著往後門走。羅老板那邊不知道能拖多久,他們必須要加快腳步才行。想著,鬆子腳下步子加快,帶著到了後門口。
打開門確認沒人以後,才溜了出去,鬆子代道:“季小姐,等下你出去以後,往南邊小巷子走。五爺正在那邊和人談事,他見到你一定會找你的。”
聽出他話裏的意味,季煙皺眉,“那你呢?”
不會是想讓跑了,鬆子留下來吧。雖然不知道那些人到底幹什麽的,但是一看就不是什麽好人。如果鬆子落到他們手裏,還不知道會變什麽樣。
鬆子嬉笑道,“你擔心我幹什麽,我在這附近混的這麽了,他們不會我的。趕的,可別耽誤時間了。”
先進來的四個人中,有個突然從樓上走了下來,一眼就看到了才踏出前腳的季煙。他連忙大喊一聲,“人在這裏,快來人。”
鬆子大驚失,注意到那個人在腰間索的作,鬆子抄起手邊的板凳就丟了過去,板凳穩穩的砸中了他的腦袋,瞬間就形了一個窟窿,那人嚎一聲,握著流的腦袋倒在地上。
樓上的人聽到靜,都跑下來,見到自己兄弟傷,上前查看況,從他裏得知了季煙他們逃走的消息。立刻整頓了隊伍,留了個人在這看著,其他人都追了出去。
鬆子帶著季煙走了一路,就聽到後麵的腳步聲。季煙畢竟才剛剛清醒過來,上殘留的藥效還在,腳踝之前又過傷,腳步不夠靈活,很快就被人追了上來。
“你快走,我去拖住他們。”
將季煙推到拐角的巷子裏,鬆子準備轉對應對那些人,季煙連忙拉住他,“不行,他們手上有槍,你一個人怎麽對付他們?我們先去找個地方躲一躲,我不見了,傅容兮一定會找過來的,隻要等到他們過來,我們就沒事了。”
鬆子一把甩開他的手,臉上掛起厭惡,“你們人可真麻煩,我是真的不想過來的。你囉嗦了趕走吧,見著就煩。”
看到鬆子決然的背影,季煙明白他是不想讓有心理力,所以才故意這麽說的。這樣一來,更加不能辜負他爭取出來的時間了。一咬牙,忍著腳踝傳來的劇痛,一瘸一拐往前走。
可惜,天不遂人願,那些人對若河一帶也是相當悉的,季煙剛拐了個彎,就撞到了包抄過來的人。
猜你喜歡
-
完結1497 章

天才雙寶:傲嬌前妻抱回家
一場意外,她懷了陌生人的孩子,生下天才雙胞胎。為了養娃,她和神秘總裁協議結婚,卻從沒見過對方。五年後,總裁通知她離婚,一見麵她發現,這個老公和自家寶寶驚人的相似。雙胞胎寶寶扯住總裁大人的衣袖:這位先生,我們懷疑你是我們爹地,麻煩你去做個親子鑒定?
267.8萬字8 65089 -
完結100 章
萌妻迷糊︰第一暖男老公
他陰沉著臉,眼里一片冰冷,但是聲音卻出其的興奮︰“小東西,既然你覺得我惡心,那我就惡心你一輩子。下個月,我們準時舉行婚禮,你不準逃!” “你等著吧!我死也不會嫁給你的。”她冷冷的看著他。 他愛她,想要她。為了得到她,他不惜一切。 兩年前,他吻了她。因為她年紀小,他給她兩年自由。 兩年後,他霸道回歸,強行娶她,霸道寵她。
8.9萬字8 26664 -
完結77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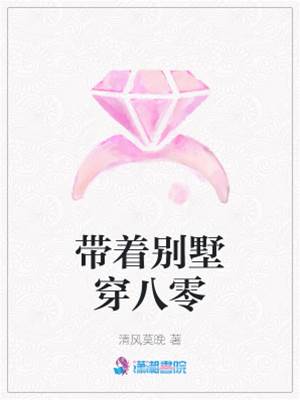
帶著別墅穿八零
二十一世紀的蘇舒剛繼承億萬遺產,一睜眼穿成了1977年軟弱可欺的蘇舒。在這個缺衣少食的年代,好在她的大別墅和財產也跟著穿來了。然后她就多了個軟包子媽和小堂妹要養。親戚不懷好意上門說親,想讓她嫁給二婚老男人,一進門就給人當后娘。**梁振國退役轉業后,把戰友的兩個遺孤認養在名下,為了更好的照顧兩個孩子,他想給孩子找一個新媽。人人都說鎮上的蘇舒,膽子小,沒主見,心地善良是個好拿捏的,梁振國打算見一見。**為了帶堂妹逃離老家,蘇舒看上了長得高大英俊,工作穩定的梁振國。一個一帶二,一個一帶一,正好,誰也別嫌棄誰...
60.8萬字8 59526 -
完結332 章

辣妻致富1990
身價千億的餐飲、地產巨亨顧語桐,訂婚當天被未婚夫刺殺! 再次醒來的她,發現自己竟然穿越到了生活在1990年的原主身上! 原主竟然跟一個傻子結了婚? 住進了貧民窟? 還在外面勾搭一個老流氓? 滿地雞毛讓她眉頭緊皺,但她顧語桐豈會就此沉淪! 一邊拳打老流氓,一邊發家致富。 但當她想要離開傻子的時候。 卻發現, 這個傻子好像不對勁。在
61.2萬字8 14929 -
完結921 章

一胎三寶:夫人又又又帥炸了
被設計陷害入獄,蘇溪若成為過街老鼠。監獄毀容產子,繼妹頂替她的身份成為豪門未婚妻。為了母親孩子一忍再忍,對方卻得寸進尺。蘇溪若忍無可忍,握拳發誓,再忍她就是個孫子!于是所有人都以為曾經這位跌落地獄的蘇小姐會更加墮落的時候,隔天卻發現各界大佬紛紛圍著她卑躬屈膝。而傳說中那位陸爺手舉鍋鏟將蘇溪若逼入廚房:“老婆,什麼時候跟我回家?”
229.5萬字8 73055 -
連載342 章

從摸魚開始成為學霸
【校園學霸+輕松日常+幽默搞笑】“你們看看陳驍昕,學習成績那麼優異,上課還如此的認真,那些成績不好又不認真聽課的,你們不覺得臉紅嗎?”臺上的老師一臉恨鐵不成鋼地
83.3萬字8.18 413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