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宮殺,公子他日日嬌寵》 第39章 跪下
小七只以為那人要拿書簡砸,駭得一激靈,下意識地抬起袍袖遮住臉,子不由自主地便往后退去。
許瞻見狀愈發生氣,一雙眸薄怒涌,當即起了命道,“跪下!”
小七不敢忤他,忙跪了下來。
上的不適比方才更加難以忍耐,愈是屏氣斂聲愈不過氣來,不得不微微俯下子,一手撐著木地板,一手按住口,低聲下氣地認錯,“公子恕罪,奴知錯了”
那人雖還著臉,但到底語氣比方才和了幾分,“你怎會錯?”
“奴不該在背后議論公子”
那人雖還凝著眉,但語氣分明又緩了幾分,“僅是議論?”
在人屋檐下,小七也不得不低頭,只得昧著良心說,“奴不該在背后說公子壞話。”
心里卻是不服氣的,說的是實話,是真話,怎麼會是壞話。
那人眸漸斂,角淺淺地溢出一笑意來,很快又埋頭批閱案上的案牘去了,不再理會小七。
小七幾乎跪不住,猶豫再三終是啞著嗓子說了句,“公子公子再不許奴出去,奴奴就要吐出來了”
“你敢!”
許瞻聲忽地又冷戾起來,生生端出了危險。
是了,那人的潔癖已經到了令人發指的地步,向來是最怕臟的。
小七忍得眼眶泛紅,抬袖掩,可可憐憐地著許瞻,“公子給小七一口水喝罷!”
Advertisement
那人淡淡地“嗯”了一聲,隨手推了一下手邊的牛角杯。
小七跪行上前,慌地拾起牛角杯幾口便飲了個干凈,似火燒灼般的五臟肺腑這才被一杯水澆滅下去。
待好一些,取出帕子將他的杯沿仔細拭凈了,這才送還到了青銅長案上。
這大半日過去,人已是累極乏極,困頓不堪,見許瞻有萬機要忙,并不怎麼理會。小七趁他不備便悄悄臥下
蜷了起來,茶室的席子亦是有一清香,旦一闔上眸子,須臾之間便睡著了。
口憋悶得十分難,夢里亦是不過氣來,尤其心里又不踏實,那人偶爾翻閱竹簡的聲音亦能將驚得醒來。
若那人并不斥責,便繼續睡去。
仿佛睡了很久,也好似只是瞇了不過半盞茶的工夫,醒來的時候,上竟蓋著一張茸茸的毯子。
那燕國公子正在旁垂眸細看,眉眼中有幾分繾綣,見睜眸,那繾綣便立刻斂得干干凈凈,半分也瞧不出了。
那人清清冷冷地問,“誰許你罰時睡的?”
小七面如紙白,上陣陣打著冷戰,待分辨清楚他的話,恍然想起自己在此罰的因由,歉然撐起來,“公子恕罪小七知錯了”
的眉頭皺得舒展不開,想起槿娘與鄭寺人的提醒,趕忙改口道,“奴知錯了”
那人這才打算饒了,單手挑起的下來,冷聲冷氣地嚇唬道,“再敢背后非議,便將你的死。”
小七上已經沒有半分氣力,任由他挑著,低聲細語應道,“小七再不敢了”
好一會兒沒聽見那人再說話,的卻被開了,繼而一苦的藥湯緩緩注進間,又緩緩在肺之間延漫開來。
一時嗆咳起來,還未來得及吞咽下去的藥湯便從角淌了下去。
淌在了那人手上。
黑白分明。
亦是十分可怖。
那人擰眉看去,指尖輕,面龐結了冰般冷著,但到底沒
有松開手去。
待將整碗湯藥飲完,又緩上了好一會兒,小七才恢復了幾分神。
但見那人一雙目微瞇,面晦暗,“魏俘,你弄臟我了。”
小七心口一窒,忙取出帕子要去給他拭。忽又想到初見時他因水土不服干嘔著,上前便去為他輕拍脊背,那時那人十分嫌惡地將推開,斥“誰許你我”,還斥“你可知自己多臟”。
攥著帕子的手便頓在了那人面前。
那人不著痕跡地掃了一眼,語氣有幾分不耐,“不會侍奉人?”
小七低聲辯白,“奴怕再弄臟公子。”
那人神愈發難看,小七不去他的霉頭,趕忙垂頭為他仔細拭了起來。
那人指尖的微涼過帕子很快便遞到手心里去了。
那真是一雙完無瑕的手呀,很大,修長白皙,指節分明。
那是一雙十分貴氣的手。
是從小養尊優,不曾勞作半分的手。
小七在這樣的雙手面前自覺形穢,忽聽那人問道,“我真有那麼不好?”
聲中有些難掩的偏執,但到底不再似先前的冷漠了。
就連那雙手也不再似方才那般涼,甚至很快溫熱起來。
小七趕回道,“公子很好,十分好。”
那人笑了一聲,語氣淡淡,“不好你也得著。”
是了,不好也得著。
不著又有什麼別的法子。
小七心里一松,知道今日這事總算是過去了。
完了罰,他竟還破天荒地許乘步輦回去。
這可是從來沒有的恩遇。
他
生來金尊玉貴,素來霸道無禮,絕不是一個為旁人著想的人,定然是他良心發現。
小七暗自揣著,許瞻雖不好,但好似也沒有太壞。
自然也不能指他與大表哥相比。
這世上終究是沒什麼人能比得上大表哥的。
那人還許回聽雪臺靜養,好久也不再見他傳召。聽說大多時候都在宮里,大抵是因燕莊王病重,他需宮主持國政,因而很忙。
只是苦了槿娘,雖仍舊每日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早出晚歸地在前院晃,卻總不見許瞻人影。
槿娘是個鍥而不舍的,有自己信奉的人生信條,曾無數次起誓要靠自己的智慧與貌改變命運。
因而即便許瞻總不在蘭臺,也總能尋到各種由頭在前院出沒,抓一切可能的機會面見許瞻。
有一回果然在青瓦樓前見到了許瞻,確定許瞻也看見了自己,因為他頓住了步子,目在上逗留了好一會兒才抬步走了。
若不是看上了,怎麼會端量這許久?
槿娘喜不自勝,一顆滾熱的心幾乎要從嗓子眼兒里迸將出來,在這青石板上彈跳幾下,再一躍而起,猛地彈到云間,最后彈到九霄云外去。
那可是這燕國最最尊貴的男子。
而槿娘亦是如花似玉,段風流。
蘭臺夫人的位子是不敢想,但總配得上做他的姬妾。
待回了聽雪臺,槿娘的一張臉仍舊紅得要滴出來,在銅鏡前扭腰肢左右欣賞自己總有大半個時辰,眉飛舞道,“你等著信兒吧,公子就要納我為姬妾了。”
小七便問,“公子可說了?”
槿娘奇怪地看,“自然,不是公子說的,難道還是我自己發癲不?”
猜你喜歡
-
完結475 章
廚女當家:山裡漢子,寵不休
一朝穿越成食不裹腹,家徒四壁的農家貧戶,還是一個沖喜小娘子。 陳辰仰天長嘆。 穿就穿吧,她一個現代女廚神,難道還怕餓死嗎? 投身在農門,鄉裡鄉親是非多,且看她如何手撕極品,發家致富,開創一個盛世錦繡人生。 唯一讓她操蛋的是,白天辛苦耕耘賺錢,晚上某隻妖孽美男還要嚷嚷著播種種包子。 去他的種包子,老孃不伺候。
87.3萬字7 49745 -
完結1071 章

權寵天下:本候要納夫!
忠遠侯府誕下雙生女,但侯府無子,為延續百年榮華,最後出生的穆千翊,成為侯府唯一的‘嫡子’。 一朝穿越,她本是殺手組織的金牌殺手,女扮男裝對她來說毫無壓力。 但她怎麼甘心乖乖當個侯爺? 野心這東西,她從未掩藏過。 然而,一不小心招惹了喜怒無常且潔癖嚴重的第一美男寧王怎麼辦? 他是顏傾天下的寧王,冷酷狠辣,運籌帷幄,隻因被她救過一命從此對她極度容忍。 第一次被穆千翊詢問,是否願意嫁給她,他怒火滔天! 第二次被穆千翊詢問,他隱忍未發。 第三次,他猶豫了:讓本王好好想想……
102萬字8 40383 -
完結11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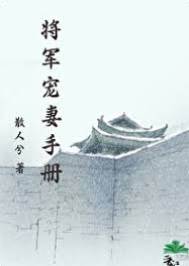
將軍寵妻手冊
雲府長女玉貌清姿,嬌美動人,春宴上一曲陽春白雪豔驚四座,名動京城。及笄之年,上門求娶的踏破了門檻。 可惜雲父眼高,通通婉拒。 衆人皆好奇究竟誰才能娶到這個玉人。 後來陽州大勝,洛家軍凱旋迴京那日,一道賜婚聖旨敲開雲府大門。 貌美如花的嬌娘子竟是要配傳聞中無心無情、滿手血污的冷面戰神。 全京譁然。 “洛少將軍雖戰無不勝,可不解風情,還常年征戰不歸家,嫁過去定是要守活寡。” “聽聞少將軍生得虎背熊腰異常兇狠,啼哭小兒見了都當場變乖,雲姑娘這般柔弱只怕是……嘖嘖。” “呵,再美有何用,嫁得不還是不如我們好。” “蹉跎一年,這京城第一美人的位子怕是就要換人了。” 雲父也拍腿懊悔不已。 若知如此,他就不該捨不得,早早應了章國公家的提親,哪至於讓愛女淪落至此。 盛和七年,京城裏有人失意,有人唏噓,還有人幸災樂禍等着看好戲。 直至翌年花燈節。 衆人再見那位小娘子,卻不是預料中的清瘦哀苦模樣。雖已爲人婦,卻半分美貌不減,妙姿豐腴,眉目如畫,像謫仙般美得脫俗,細看還多了些韻味。 再瞧那守在她身旁寸步不離的俊美年輕公子。 雖眉眼含霜,冷面不近人情,可處處將人護得仔細。怕她摔着,怕她碰着,又怕她無聊乏悶,惹得周旁陣陣豔羨。 衆人正問那公子是何人,只聽得美婦人低眉垂眼嬌嬌喊了聲:“夫君。”
17萬字8.33 5690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