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總他嗜妻如命》 第019章
三個人一起去了樓上包廂,當賀十方推開包廂大門,安笙抬眸一眼看清楚里面坐著的幾個人時,當即就有種調頭離開的沖。
原來夏憐星時說的“二哥”不是別人,竟然是薄景遇。
好像,薄景遇上面還有一個大哥,他在薄家排行老二。
此刻的包廂里,人不多,三男一,男的自然是薄景遇、夏祁楓,還有故遲,上次在賀家,安笙見過。
就是人長的正經,但不太正經的那位。
他們幾個正在玩骰子。
薄景遇坐在沙發最中間的位置,敞著一雙長,斜勾著半邊角,薄間咬著燃了三分之一的香煙,黑眸微瞇,右手摟著邊人的肩膀,左手正“哐哐”搖著骰盅。
薄景遇摟著的人,安笙也見過,前些天帶著迦南去醫院,當時和薄景遇在一起的,也就是這個人。
在大門推開的下一秒,薄景遇手里的骰盅“嘭~”的一聲落在大理石的茶幾臺面上,爾后掀眸朝門口看了過來。
短短一秒,安笙心思已是千回百轉。
正當轉想走的時候,薄景遇淡薄的視線已經掃了過來,正好和安笙的目對上。
“二哥。”
在安笙渾有些僵住的時候,夏憐星已經拉著,興地進了包廂。
Advertisement
“二哥,你不厚待呀,都回來多久了,也不給我準備禮喊我吃飯。”
薄景遇拿下角的香煙捻滅在面前的煙灰缸里,掀眸覷著面前的人笑了起來,“禮有,飯也有,就差你的人。”
“呦,這不安老師嘛,我還以為憐星帶了哪個沒見過面的小妹妹來,怕把人給嚇著。”
故遲認出安笙,立刻雙眼放。
安笙看向故遲,朝他微笑點頭,然后又旁邊的夏祁楓一聲“夏大哥”。
“怎麼,你們都認識安笙?”夏憐星好奇。
“不認識。”故遲還沒說話,薄景遇搶答了。
話落,他長臂帶著邊的人,往沙發里靠去。
人順勢進他的懷里,抬眸意味深深地看他一眼。
明明上次在醫院——
不僅
是薄景遇懷里的人搞不懂薄景遇葫蘆里賣的什麼藥,賀十方跟故遲更不懂。
畢竟,上次在賀家,薄景遇可是追著人一路出去的。
“嘿,二哥,這是我閨,安笙。”
只有夏憐星傻傻被人騙,拉著安笙向前一步,“這是薄氏的新任總裁,薄景遇,也是我二哥,當然不是親的哈,但跟親的一樣。”
在薄景遇幽深又淡涼的目下,安笙沖著他微微一笑,也不知道哪來的膽子,竟然說,“薄總記真不好,我們見過的。”
“哦,是麼?”薄景遇角勾起一抹漫不經心的混笑,“忘了。”
他這樣說,幾個人都裝傻充愣,不揭穿。
“忘了?”夏憐星不信,但看著薄景遇一直摟在懷里跟心肝寶貝似的人,立刻就懂了,哈哈笑道,“二哥,這位大人是誰呀?不會是……”
“當然是二嫂。”故遲接話。
“故太抬舉我了。”人終于開口。
拿開薄景遇搭在自己肩膀上的手,段優雅地站了起來,笑意盈盈地朝安笙和夏憐星點頭,“二位人好,我是臻,是薄氏旗下的影視公司新簽約的藝人。”
臻一襲火紅的長,配上烈焰似的紅,簡直火玫瑰般的妖治。
“原來二嫂是星銳影視的藝人。”
論夏憐星拍馬屁的功夫,那也是一流,“嘖,就二嫂這條件,一年之不國頂流都沒天理,更何況還有二哥在。”
“那當然。”薄景遇對臻一臉寵溺,“沒你二哥,怎麼有你二嫂。”
——沒你二哥,怎麼有你二嫂。
安笙眉梢微挑,眼底劃過一抹厭惡。
這抹厭惡,一閃即逝,別人或者都沒有注意到,但薄景遇注意到了。
“安笙,別站著,隨便坐。”夏祁楓坐在薄景遇另外一邊,對著安笙開口。
“謝謝夏大哥。”安笙點頭,和夏憐星一起落坐。
因為包廂的沙發是呈u字形的,好巧不巧,安笙坐的位置,正好斜對著正中央的薄景遇。
“臻臻,坐。”
安笙無意抬眸的時候,就
看到薄景遇長臂去勾住了臻的柳腰,將往懷里帶。
臻臻依偎進他的懷里,優雅,風無限,不過倒沒再有任何曖昧舉。
“十方,你遲到,怎麼罰,自己說。”夏祁楓說著,拿了酒瓶倒酒。
賀十方笑,將西裝外套隨手扔到沙一角,坐到夏憐星邊,“我這不是把安老師和憐星帶來了嘛,就不能將功抵過?”
“賀十方,你這功勞也來的太便宜了吧,我可不認。”夏憐星斜著邊的賀十方,角了。
賀十方端起服務生剛拿過來的酒喝一口,笑說,“那你們想怎麼罰吧?”
“簡單,來一首唄。”故遲不懷好意。
薄景遇搖頭,“你們這是不怕他謀財,更不怕他害命。”
“怎麼,賀總的歌如此迷人?”臻在薄景遇的懷里,笑容俏。
“哈哈哈——”故遲大笑了起來,“何止迷人,簡直能把人迷死。”
“那可未必,等著。”賀十方忽然對自己的歌聲異常自信。
在眾人好奇的目下,隔著夏憐星,他看向安笙,“安老師,幫個忙怎麼樣?”
安笙本來想盡量降低自己的存在,但忽然被點名,也只能笑著接話,“賀總您說。”
“救我一次,陪我唱一首。”賀十方真誠邀請。
有一次下班早,他無意聽到安笙教賀奕可唱西班牙語歌,簡直跟天籟一樣。
安笙張了張,拒絕的話到了邊,卻又生生吞下,改而點頭說,“好,賀總想唱什麼歌?”
賀十方笑,“就你教奕可唱的那道《dueleela
呵——有意思。
斜對面,某個男人黑眸幽暗,淺淺睨著安笙和賀十方,意味難明地勾。
“靠,賀十方你什麼時候變得這麼有眼了?”
夏憐星看異類一樣看賀十方,“安笙要是出專輯,那絕對首首圍華語金曲。”
“嗯,這還得多謝你。”賀十方說著,站了起來向安笙手,做出請的姿勢。
安笙微笑著點了下頭,站起來……
猜你喜歡
-
連載1504 章

夫人她A爆全世界
【甜寵,重生,虐渣,馬甲,團寵】“還逃嗎?”秦初使勁搖頭:“不逃了。”放著這麼好看的男人,她再逃可能眼睛真有病,前世,因錯信渣男賤女,身中劇毒鋃鐺入獄,自己最討厭的男人為替自己頂罪而死,秦初悔不當初,重回新婚夜,秦初緊抱前世被自己傷害的丈夫大腿,改變前世悲慘人生,成為眾人口中的滿級大佬。人前,秦初是眾人口中秦家蠢鈍如豬的丑女千金,人后,秦初是身披各種馬甲的大佬,某天,秦初馬甲被爆,全
135.4萬字8 16222 -
完結14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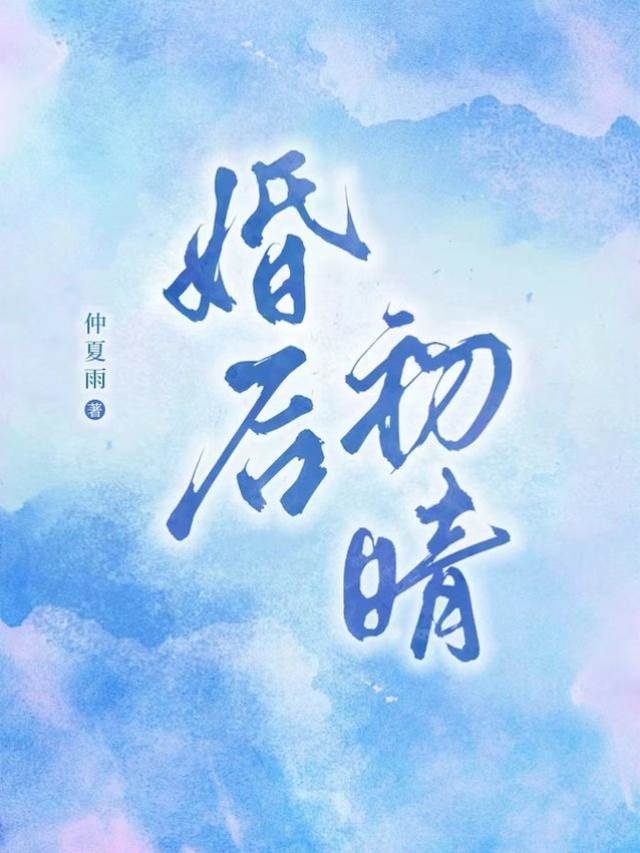
婚後初晴
沈頤喬和周沉是公認的神仙眷侶。在得知沈頤喬的白月光回國那日起,穩重自持的周沉變得坐立難安。朋友打趣,你們恩愛如此有什麽好擔心的?周沉暗自苦笑。他知道沈頤喬當初答應和他結婚,是因為他說:“不如我們試試,我不介意你心裏有他。”
27.2萬字8 490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