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外懷孕後,禁欲前夫真香了》 第144章 親一個小嘴
“神經病。”
天已晚,溫暖不想和他多說一句話,朝另外的方向走去。
楊囂不管三七二十一攔住的去路。
“去哪裏?”
男人森的臉看起來格外恐怖,特別是他的目下流齷齪,溫暖怎可能看不出。
“滾開。”
溫暖緩緩後退。“公園裏人來人往,你敢輕舉妄,就等著在鐵窗裏踩紉機。”
楊囂獰笑,步步近。“威脅我?老子是嚇大的?那一晚,我就敢,今天算什麽?”
他猖狂至極,這已經不是第一次,當然也不可能是最後一次。
“什麽那一晚?”
溫暖抓住重點,想起第一天到祁肆做護工回來的晚上,走在暗巷裏,突然竄出一個男人,捂住的,錮自己的手腳。
天太黑,那裏又沒有路燈,溫暖看不清他的臉,男人一直沒說話,但各種表現都是企圖想對·······
一直以為是哪裏的瘋子,現在聽到他的話,不脊背發涼。
林晚晴帶過他去們租住的房裏,他也知道回家必經那條暗巷。
楊囂顯然愣住,居然說出來了,當時會遇到溫暖,完全就是意外。
Advertisement
那天晚上,他本想留宿在那,林晚晴擔心回來,偏要讓他回去。
求不滿的自己看到溫暖,又是他肖想已久的人,便起了歹念,隻是那一次被這個人掙,連都沒親到。
溫暖的猜想在看到他慌張閃躲的表時得到證實,怒不可遏的撿起地上的石頭砸過去。
“人渣,去死。”
“還不是你,是你的錯。”
楊囂惱怒的抓住溫暖的手,把往角落裏拖。
“賤人,你還不是為了錢?裝什麽貞節烈,既不是完璧之,玩玩又如何?”
這裏沒其他人,既然已經猜到,楊囂也不裝了,破罐子破摔,事暴那他更要得到這個人,用“本事”征服。
讓嚐到銷魂的滋味,徹底臣服在自己腳下。
溫暖手裏著石頭,隻等他不備時,砸破他的腦袋。
“嗬,你都準備好了?”楊囂激萬分。“放心,我會好好對你。”
男人鉗住的下顎,熏心的靠近,溫暖心一橫,正要砸過去。
“對你妹。”
“啊~~~~,痛!”
一道人影閃現,楊囂直接飛了出去,然而他還來不及反應,拳頭如雨般落下。
“啊啊~~~~~~救命~”男人的哀嚎聲不絕於耳。
“老子的人,你也敢,媽的。”祁肆打紅了眼,拳拳到。
聽到他的聲音,溫暖回神,見他發了瘋似的打地上奄奄一息的男人,心裏一暖。
“祁肆。”小手覆在他的手上,不想他把渣男打死擔責。
“媽的,老子打死你。”
男人走火魔,仿佛沒聽到的聲音,甩開邊的障礙,此時地上的男人已經被打的失去意識,全上下沒一完好。
溫暖被用力一甩,絆倒在地。
發了瘋的男人像是想到什麽,猩紅的眼看向“障礙”。
高大的軀一,他急忙奔過去抱住小人。“暖暖,對不起,我該死,我不知道是你,我有沒有傷到你,我們去醫院。”
祁肆慌張的抱起小人,溫暖到他的服被浸,全都是汗。
“我沒事,不用去醫院,你有沒有怎樣?”
隻是部著地有點痛而已。
“你怎麽可能沒事?我剛才不知輕重,你傷到哪裏?我看看。”
祁肆急於尋找傷,抱著的手不斷移,溫暖麵紅耳赤,抓住他的手,認真的看著他。“我真的沒事。”
他抱住懷裏的小人,埋首在頸窩,聲音哽咽。“對不起,我來晚了。”
溫暖心中的某,不自的拍拍他的背。
“沒有,你來的及時,謝謝。”
“對不起,對不起。”
祁肆無法言說當看到被該死的人錮時心想要殺人的衝。
他的在抖,在為自己擔心,他抱的很,像是要進裏。
溫暖的回抱,輕聲安。“我真的沒事,謝謝你。”
······
按照祁肆的個,哪可能會讓警察來理,但邊的小人執意要報警。
他們在警局錄完口供出來後,某男徹底發了。
“這麽重要的事你怎麽不告訴我?他之前居然還敢對你······,我剛才怎麽沒弄死他,不行,我要去殺了他。”
半死不活便宜他,要讓他不得好死。
男人怒氣衝天,闖進警局,溫暖急之下,抱住他瘦的腰。“別因為渣男做作犯科之事,不值得。”
第一次這麽主,卻是在這樣的場景下,祁肆不知道該怎麽形容心裏的覺,又不想讓擔心。
“媽的,老子要讓他牢底坐穿。”最後,他妥協了。
“嗯,好。”溫暖鬆開他。
祁肆卻一把拉住,將小手繼續放在自己的腰間,抱住,瓣唰過白潔的耳廓。“暖暖,我是真的真的喜歡你,做我朋友好不好?我想保護你。”
麵對他深表白,溫暖隻是怔怔的看著他,許久,淡淡道:“快走了。”
“不走。”祁肆知道自己小人,想得到的認可。
“你不要這麽無賴。”溫暖嗔。
祁肆歎氣,又退了一步,卑微問:“暖暖,那能不能親一個小?”
於是,某人被踹了,而肇事者還走了。
“暖暖,親一個吧?”祁肆追上去。
“滾~~~~”
猜你喜歡
-
完結367 章

前妻,敢嫁別人試試
三年前,她在眾人艷羨的目光里,成為他的太太。婚后三年,她是他身邊不受待見的下堂妻,人前光鮮亮麗,人后百般折磨。三年后,他出軌的消息,將她推上風口浪尖。盛婉婉從一開始就知道,路晟不會給她愛,可是當她打算離去的時候,他卻又一次抱住她,“別走,給…
95.4萬字8 74666 -
完結11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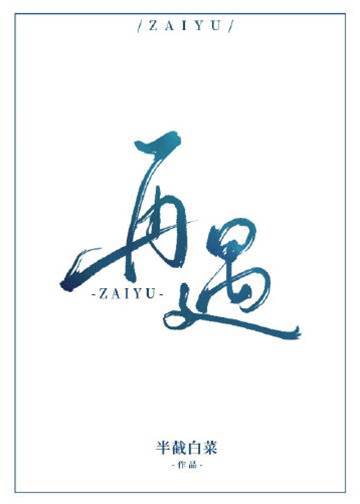
再遇
孟淺淺決定復讀,究竟是為了自己還是為了應浩。她也不知道。但是她成功考上了應浩所在的大學。一入學便得知,金融系應浩正跟金融系的系花談戀愛。-周喬曾說應浩不是良人,他花心,不會給她承諾以及未來。孟淺淺其實明白的,只是不愿意承認,如今親眼所見,所…
38.8萬字8 18890 -
完結641 章
重返七零之空間小辣妻
末世大佬唐霜穿到年代成了被壓榨的小可憐,看著自己帶過來的空間,她不由勾唇笑了,這極品家人不要也罷; 幫助母親與出軌父親離婚,帶著母親和妹妹離開吸血的極品一家人,自此開啟美好新生活。 母親刺繡,妹妹讀書,至于她……自然是將事業做的風生水起, 不過這高嶺之花的美少年怎麼總是圍著她轉, 還有那麼多優秀男人想要給她當爹,更有家世顯赫的老爺子找上門來,成了她的親外公; 且看唐霜在年代從無到有的精彩人生。
121.5萬字8 68733 -
完結2314 章

第一名媛:奈何嬌妻太會撩(盛莞莞凌霄)
“我愛的人一直都是白雪。”一句話,一場逃婚,讓海城第一名媛盛莞莞淪為笑話,六年的付出最終只換來一句“對不起”。盛莞莞淺笑,“我知道他一定會回來的,但是這一次,我不想再等了。”父親車禍昏迷不醒,奸人為上位種種逼迫,為保住父親辛苦創立的公司,盛莞莞將自己嫁給了海城人人“談虎色變”的男人。世人都說他六親不認、冷血無情,誰料這猛虎不但粘人,還是個護犢子,鑒婊能力一流。“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是什麼?”“哪怕全世界的人都說你不好,那個人依然把你當成心頭寶。”
426.6萬字8 3977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