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夫無情,和離後她怒嫁暴君》 第34章 因為你是司徒韞
“韞兒!你怎麽來了?老是說你和小——”
太皇太後話還沒說完,虞玥麵緋紅,急忙打斷。
“沒沒什麽!”
司徒韞眼眸晦暗,就像平靜的湖麵下暗藏的洶湧。
清冷的目不輕不重的落在虞玥上,男人好看魅的眼尾輕調,盛著星星點點的笑意。
虞玥有些幹,莫名到如芒刺背。
不知為何,每次遇到他時,總是不慌。
而他,好整以暇,遊刃有餘。
每次無聲的對峙中,好似都被他上一頭。
“韞兒,你來的及時,快讓小虞氏教教你,以後你會了這葉子牌的話,老在宮裏也不至於這麽無聊。”太皇太後眼珠一轉,妙計閃現。
司徒韞淡淡一笑,擺擺手,“孫兒對這賭一竅不通,而且近日前朝之事繁忙,恐怕沒時間與祖母一起。”
就在太皇太後嘟著,有些難過時,司徒韞接著道:“不過......以後沈夫人可以多進宮裏陪陪您。”
頃刻之間,太皇太後像個小娃娃一樣,眉飛舞,又憧憬了起來。
“當真?”
因為虞玥不是閨中未嫁的子,已嫁沈府,是府中的當家主母,考慮到已為人妻的關係,一直召人家進宮,怕是不合規矩,有些不太好。
“千真萬確,有什麽朕擔著。”
司徒韞負手而立,話語中著不容逾越的威嚴。
太皇太後一聽,恍若吃了一顆定心丸,都合不攏。
“真是哀家的好孫兒!”
虞玥瞟了一眼司徒韞,暗自歎這個暴君的心計。
表麵上是為了太皇太後把召宮,實際上,也方便了他們二人的聯絡。
接下來的一個時辰,司徒韞和太皇太後聊了些家常。
“韞兒,哀家實在無趣得很,你這後宮是一個妃嬪也沒有,你也正值壯年,是開枝散葉的時候,可是這些年喊你選秀,喊你納妃,你都不願。”太皇太後揮著芭蕉扇,哀聲連連,“哀家太想抱重孫了,哀家其他幾個姐妹都有重孫抱,就哀家沒有。”
Advertisement
太皇太後作勢悵然,明眼人都看出來是在催司徒韞快婚娶。
偏生司徒韞揣著明白裝糊塗,溫和道:“那朕有機會定要和襄王和盛王說說,他們若是有相中的姑娘,便早日婚娶,讓皇祖母早日抱上重孫。”
太皇太後一聽,恨鐵不鋼地剜了司徒韞一眼,便也知曉他的心思,不再繼續念叨此事。
虞玥這才想到,不管是夢裏,還是現實,司徒韞都不曾婚娶,諾大的後宮是空無一人。
曆代的君王,可都是三宮六院,夜夜笙歌。
當真是奇怪……
一個荒謬的想法在虞玥的腦袋裏乍現,
古書上有記載,數男子會有短袖之癖。
司徒韞,不會是有龍之好吧?
虞玥心一,手上撚的珠子都掉在了地上。
珠子落在地上的聲音清脆至極,司徒韞被吸引過來,他環著手,淡定地看著虞玥慌無措的樣子。
“你怎麽了?”
男聲冷冽,虞玥一抬眼,便看到那妖孽蠱的容。
半是影半是下,他麵平靜,下頜鋒利,墨發如瀑,額前一縷碎發隨風微揚,態橫生,又清雋無雙,堪稱絕代風華。
這樣好的相貌,竟是喜歡男子,真真是可惜了。
“沒沒什麽……”
虞玥擺手,強笑著解釋。
一陣寒暄後,夜渾濁,漆黑無邊,唯有一玄月掛在天際。
為了皇宮安全,外來之人一般都會被安排在常亦宮休憩。
就在虞玥退下時,司徒韞也起作別。
兩人剛走出元喜宮,肩而過的瞬間,司徒韞輕聲道:“到書房找我。”
—
書房。
虞玥待夜深人靜時,才小心翼翼地來到約定的地方。
畢竟和司徒韞,一個是君,一個是臣妻,若是被撞見了,那後果當真不堪設想。
虞玥左顧右盼,輕輕敲門後,屋傳一聲咳嗽。
虞玥便慢慢推門而,然後又轉迅速關上門。
所有作,一氣嗬,沒有半點猶豫。
“陛下,您此次找妾所為何事?”虞玥氣籲籲,心驚未餘。
司徒韞此時正擲著筆寫字,幹淨整潔的宣紙上,筆翼鋒利,揮斥方遒。
他緩緩放下筆,起走到虞玥跟前,神凝重。
“朕有件事要托付給你,沈黯最近新招了一些門客,這些門客博學多才,集思廣益。為了以防萬一,你必須把門客的姓名名單找出來。”
虞玥幾乎激地要哭出來。
看來的話他都聽進去了,這個暴君終於知曉了要防範,以後他和都不至於落到那般結局。
虞玥心底歡喜,麵上卻堅定冷靜,“謹遵陛下所命。”
“行吧,那便退下吧。”
就在司徒韞揮手,示意虞玥離開時。
屋外如墨天劃過一道亮,頓時雷聲轟鳴,大雨淅瀝傾盆而下。
司徒韞自如的神態一瞬消失,他的臉頓時煞白,眼神飄忽不定,邪肆麗的麵孔變得猙獰痛苦,像是水裏將死的魚兒,瀕臨絕境。
男人迅速用手扶住書案,死死撐著子,才不至於跌落在地。
虞玥眼疾手快,急忙攙扶住司徒韞,不斷用手扶著他的後背,安他的緒。
“快出去!給我出去!”
司徒韞暴怒出聲,帝王的自尊心作祟,他不想讓別人看到自己的醜態。
看到他,作為一個九五至尊,竟然會害怕下雨打雷。
實在稽。
可是不管司徒韞怎樣歇斯底裏的喊、虞玥還是一不。
天邊再次劃過一道亮,雨下得越來越大,大有與天地殊死搏鬥的氣勢。
又一聲雷鳴下,司徒韞終是撐不住,整個人無力地跌在桌角,子不停發抖、呼吸聲也愈發急促。
想起在紀遠宮裏看到的一切,再看看眼前蒼白無力的人。
虞玥不由心疼,隨後蹲下子,也顧不了什麽禮儀世俗。
狂風吹開了窗戶,也把桌案上的蠟燭一並吹滅。
黑暗中,抱住他。
冰冷被溫暖所覆蓋。
司徒韞指尖的冰涼好像消失了一些,他微微抬頭,畔無意間過的耳廓。
一瞬間,相,溫熱劃過。
兩人皆是一怔,子都有些僵。
反應過來之後,司徒韞還是極力想推開。
推開虞玥。
他不適應,不適應和晦暗中忽然有溫暖的覺。
可是不管他如何推,那個板極小的,還是吃力地抱著他。
絕不放手。
昏暗下,映襯著倔強倨傲的臉。
第一次,有人堅定的選擇他。
不管他如何推開,還是沒放棄他。
許久,司徒韞心跳逐漸恢複穩定,除了有些虛弱,神也穩定不。
“你不害怕我嗎?”
“不怕。”
“為什麽不離開?”
“我想保護你,司徒韞。”
聲音清澈,回響在暗夜中,也回響在他耳畔。
溫熱的氣息灑落在頸間側臉,心跳在這一刻猛烈加速。
就像一片冰川漂浮的汪洋,有船來航,在一片驟雨暴風中翻了個徹底。
“我這樣醜陋的樣子,你見了一次又一次,沒有笑話我,還真是見。”司徒韞自嘲地笑了笑。
九五之尊鮮的外殼下,依舊掩不住那顆曾經被欺負、被折磨得千瘡百孔的心。
在別人眼裏,他殺伐果決,威名遠揚。
可是裏,他的暗、他的自卑、他的絕,無遁形。
虞玥又想起了宮說的那些話,一陣心酸湧上,有些哽咽。
心中一,把他抱得更,語氣真摯和。
“司徒韞,你不許這樣想,這是你的病癥,不是你的錯,你不必因此自責。
你相信我,我會站在你的後,我會治好你的病。”
沒有用禮節上的稱呼。
用的是“你”,用的是“我”。
此刻,一切都安靜了下來,暗夜中,他們隻有彼此。
真誠地告訴著他。
在他後。
司徒韞頭哽住,一時說不出話。
隻是心海早已浪濤翻湧,再也不能平靜。
許久,他子逐漸恢複,緒也穩定如常。
見司徒韞轉好,虞玥也慢慢放開了他。
一陣靜默後,他緩緩出聲。
“你為何要如此對我?”
手不見五指的漆黑中,他看著,夜也擋不住眼眸裏閃爍的,擋不住的明眸皓齒的豔麗與赤誠。
就猶如天邊的皎日,永不停歇,永不熄滅。
“因為你是司徒韞。”
虞玥一字一句,沒有半點猶豫和暫停。
因為他是看似殘暴,卻一心為民,勤政理國的司徒韞。
因為他是唯一能夠改變拯救命運的暴君司徒韞。
因為他是……
在夢中騎著高頭大馬來舍命救的司徒韞……
雨聲順著屋簷滴落,滴滴答答,格外清響。
司徒韞的手頓時,心中沉睡已久的冰山漸漸融化。
他偏過頭,逃離這場對視。
過往的對陣中,他常常是倨傲者的姿態,稍使手段,便讓其方寸大。
而現在,他不再是清冷的常態,而是捉襟見肘的慌和張。
窗外雨聲漸小,鶴唳風聲也戛然,雷鳴消失得無影無蹤。
一切逐漸恢複如常。
沒了雨聲的遮蓋,室漸漸被放大。
大概是意識到現在的姿態有些過於親和逾矩,虞玥撐著子,想要起去點亮燭火。
就在即將站起來的時候,腳上一麻,虞玥又重重地跌下去。
急之下,為了防止屁開花的局麵,虞玥手想要抓住桌角,漆黑中,急忙一抓。
豈料,這個手,還有些不一樣……
“虞玥……放手……”
耳邊傳來男人克製沉悶的聲音,虞玥大腦頓時空白。
紅迅速爬滿了虞玥白玉般的頸部,後知後覺發現自己犯下了彌天大錯。
虞玥愧地想找個地鑽進去,就在想要抬起手時,猛然發現,手筋了……
“如果我說我手筋了,不了,你相信嗎……”虞玥小心翼翼地問道。
某人臉沉得如一潭死水。
“你說呢?”
就在下一瞬,司徒韞果斷拉開了虞玥的手,心複雜至極。
虞玥真是第一次到如此窘迫,簡直不敢正眼看司徒韞,老臉都沒了。
心中焦急難當,管他腳麻不麻,虞玥使足吃的力氣,想要趕快站起來逃離現場。
老天爺就是這麽奇妙,世界上就是有這麽多巧合。
虞玥好不容易站起來,怎料腳上好像被絆到了什麽。
隨後,整個人直直撲向司徒韞。
本來不及調整和控製,虞玥撲在司徒韞上,正巧與之相。
畔傳來溫熱的,的,帶著薄薄的涼意,卻又和骨,人沉迷。
兩人目相撞,彼此都能看到對方瞳孔中放大的驚訝和張。
靜謐中,距離近在咫尺,他和鼻尖相對,呼吸灼熱。
一切都靜了下來,輕合的畔,將兩人之間的親和溫暖無限放大。
空氣中,充斥著彼此纏的呼吸,還有一拍又一拍強烈的心跳。
就在積蓄已久的理智一點點瓦解時,虞玥猛然被推開。
司徒韞僵起,急忙去點燃燭火,好似想要這火焰照亮屋,將方才的失態與心跳一同燃盡。
一片無聲中,虞玥砸砸,哭無淚,“你聽我解釋,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解釋就是掩飾,掩飾就是事實。”
回到有的地方,司徒韞又恢複了平日慵懶高傲的模樣。
他眼皮微抬,漫不經心,“你若是喜歡我,想占我的便宜,直說就行,不必彎彎繞繞。”
虞玥此時心冤屈,覺得自己簡直比竇娥還冤。
可是剛剛一而再再而三,就算解釋不是故意的,恐怕司徒韞也不會相信。
算了,如果能讓司徒韞覺得世界上有個人在喜歡著他,在意著他,他心裏應該就沒這麽孤獨難了。
抱著將錯就錯的心態,虞玥破罐子破摔,瞇瞇一笑,“對,我就是喜歡你,想占你便宜,嘿嘿。”
司徒韞:“……”
良久,司徒韞背過去,潔白的耳廓帶著微紅。
“無恥。”
無恥?
虞玥子一怔。
猛然想到方才的無意一抓……
好像真的無恥的……
猜你喜歡
-
完結159 章

嫁給奸臣沖喜后
傅瑤要嫁的是個性情陰鷙的病秧子,喜怒無常,手上沾了不知多少人的血。賜婚旨意下來后,不少人幸災樂禍,等著看這京中頗負盛名的人間富貴花落入奸臣之手,被肆意摧折。母親長姐暗自垂淚,寬慰她暫且忍耐,等到謝遲去后,想如何便如何。傅瑤嘴角微翹,低眉順眼地應了聲,好。大婚那日,謝遲興致闌珊地掀開大紅的蓋頭,原本以為會看到張愁云慘淡的臉,結果卻對上一雙滿是笑意的杏眼。鳳冠霞帔的新嫁娘一點也不怕他,抬起柔弱無骨的手,輕輕地扯了扯他的衣袖,軟聲道:“夫君。”眾人道謝遲心狠手辣,把持朝局,有不臣之心,仿佛都忘了他曾...
46.3萬字8 58850 -
完結36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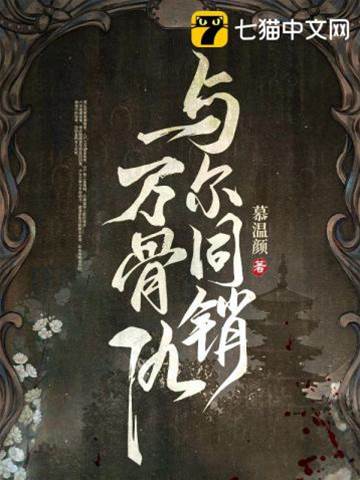
與爾同銷萬骨仇
深山荒野狐狸娶親,人屍之內竟是魚骨,女屍愛上盜墓賊,吊滿詭異人影的地宮...... 六宗詭譎命案,背後隱藏著更邪惡的陰謀。 少女天師與年輕尚書,循著陰陽異路解決命案,卻每每殊途同歸。 暗夜中的枯骨,你的悲鳴有人在聽。
32.6萬字8.18 8221 -
完結191 章

妾身嬌貴
莊綰一直以為,她會嫁給才華冠蓋京城的勤王與他琴瑟和鳴,為他生兒育女。然,一夕之間,她想嫁的這個男人害她家破人亡,救下她後,又把她送給人當妾。霍時玄,揚州首富之子,惹是生非,長歪了的紈絝,爛泥扶不上牆的阿鬥。初得美妾時,霍時玄把人往院裏一扔讓她自生自滅。後來,情根已深種,偏有人來搶,霍時玄把小美人往懷裏一摟,“送給爺的人,豈有還回去的道理!”
51.9萬字8.18 18298 -
完結347 章

囚她
施家二小姐出嫁一載,以七出之罪被夫家休妻,被婆婆請出家門。 無子;不事舅姑;口舌;妒忌。 娘家一席軟轎把她帶回。 她住回了自己曾經的閨房。 夜裏,她的噩夢又至。 那人大喇喇的端坐在她閨房裏,冷笑睨她。 好妹妹,出嫁一年,連自己娘家都忘了,真是好一個媳婦。 她跪在他身前,眼眶皆紅。 他道:“不是想要活着麼?來求我?” “你只許對我笑,對我體貼,對我賣弄,對我用十分心計,藉由我拿到好處。”
56萬字8.18 325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