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爺狠戾恣狂!私下夜夜求親親》 第176章 情有獨鍾
男人的短發似乎都要些,每次賀妄的黑發蹭過沈清蕪的脖頸,都能讓到被刺撓得又疼又。
沈清蕪把賀妄胡蹭的腦袋推開了一點,“賀妄,你幾歲了?”
後者神玩味,“十八,男大學生。老板滿意嗎?”
三言兩句間把兩人之間的關係說得像極了錢易。
賀妄做事本來就天馬行空,時不時就會一時興起搞些奇怪的cosplay,沈清蕪已經能做到應對自如了。
冷漠地回手,“不滿意,太小了。”
“不小呢老板。”賀妄又再一次將攏進了懷抱裏,兩著,單薄的料抵擋不了源源不斷的溫傳遞,“你試試。”
他一直都是氣旺盛的類型,一年四季全上下都是暖的,現在擁著,讓沈清蕪恍惚間覺得自己在被烘烤一般。
熱,臉也熱,輕罵了一句,“不正經。”
賀妄挑了挑眉,“你不是早就知道了嗎?”
這時候,一輛奔馳開了過來,司機停下車,打開了後座車門。
他勾了勾沈清蕪的手,“老板,跟不跟我回家?”
不遠的司機正好把這句話聽了個正著,縱然他心中已經起了驚濤駭浪,但超高的職業素養還是讓他麵不改。
沈清蕪上車後給穗安打了一通電話,後者語氣裏帶著雀躍,“我知道啦,你們放心地去約會吧,我又不是小孩子了,不用太擔心我啦。”
Advertisement
仍舊叮囑了些注意事項才掛斷了通話,在電話剛剛掛斷下一秒,旁邊的賀妄就出手,確地圈住了的腰肢,將人整個抱了起來,放到了自己的上。
他的臂力一向出奇的驚人,手臂廓清晰,屬於不隻是在健房勤鍛煉就能練出來的。
而沈清蕪材偏瘦,平時的運也就是慢跑和瑜伽,手臂纖細白皙。之前穿著外套不太能看出他們型上的差距,但今天兩人都穿的短袖,現在又著,小麥的實壯的手臂和雪白纖細的手臂相,形的對比異常鮮明。
賀妄輕輕著的下,順勢低頭湊了上去吻上了心心念念的,沈清蕪被自己親手調的皮革調男香包裹了,像是跌了那款香水形的深海中。
車靜謐,他們齒之間的纏發出的嘖嘖水聲又曖昧地撥著神經。
這輛車並沒有隔板,所以前麵專心致誌開車的司機隻要抬頭看一眼就能將兩人擁吻的場景盡收眼底,這一認知在某個方麵為了這個吻的燎焰,替曖昧繾綣的氛圍增添了兩分刺激。
其實司機隻要稍微有點腦子,還想要這份工作,他就算聽到後座傳來八十分貝的高音,恐怕也不會回頭看一眼的。
沈清蕪不是沒有想到這一層,但依舊會忍不住擔心。
在一個綿長熱烈的吻結束後,賀妄迫不及待地想要接第二個吻時就被無拒絕了。
他烏沉沉的眸落在的臉上幾秒,就明白了此刻的顧慮,輕笑了一聲,“乖乖,有擋板和沒擋板其實沒多大區別。”
有隔板的時候兩人的確能有看似獨的私空間,但換個角度一想,他們把隔板升上去的那一刻,不管他們有沒有做一些親的舉,但在別人眼裏他們肯定都是做了。
沈清蕪輕飄飄地瞥他一眼,“道理我都懂。”
但別人猜測他們接吻和親眼看到他們激吻還是有本質上的差別的。
自認為還沒有擁有一顆如此強大的心髒,或是一張和賀妄相同厚度的臉皮能夠坦然地接後一種況。
賀妄的那座莊園是對外開放的度假酒店,頂樓依舊留了出來為他的私人領域,電梯是刷房卡到對應樓層的設置,除了每天來打掃的工作人員,其他人都沒有上頂樓的權限。
在兩人上電梯前,他順手把沈清蕪的權限也加了上去,“都說你和你姐姐住這兒了,方便還省錢。”
“穗安說我們還是男朋友關係,住你家不太好。”
賀妄用深邃幽暗的眼眸攫取住,“我可以理解為,姐姐是在催我們盡早結婚嗎?”
一提到這個話題,他就展現出了妙的打蛇上的天賦,甚至還暗把“你姐姐”改了“姐姐”來拉近關係。
沈清蕪破他的想象,“你還真能聯想。”
房間裏的裝修是標準的法式貴族風,熠熠閃的支形水晶吊燈,複古奢侈的kingsize大床,鑲嵌著鍍金狀似的家以及價值不菲的古董擺件都無一不昭示著主人的奢華。
但偏偏外麵的環境又是浪漫如油畫一般的,秀麗和雅致中和了莊園的富麗堂皇,增添了幾分優雅。
沈清蕪站在拱形落地窗前俯視著後麵那四百英畝的花園,回頭睨了一眼後的男人,似笑非笑地問,“不是說帶我來賞花嗎?怎麽直接帶著我上樓了?”
夜晚的燈是暖黃調的,籠罩整個莊園可可風華麗的外觀襯得更加輝煌磅礴,這時候的花園也被披上了一層濾鏡,和白天的氛圍明顯不同。
賀妄輕咳了一聲,對著茶幾揚了揚下,“那兒也有花。”
彩瑰麗的石鑲木鎏金圓桌上放著一個鏨刻水晶花瓶,瓶子裏著十幾支豔滴的重瓣型芍藥,有淺淡的香味。
沈清蕪恰好認識這一品種的芍藥花。
蝕刻鮭魚,被稱為芍藥中的馬仕,也是一種能變的芍藥,在最初盛開時是三文魚的桃紅,後麵會逐漸褪香檳。
的確還好看。
賀妄上前一步擁住了,“知道芍藥的花語嗎?”
“不知道。”沈清蕪對花沒那麽了解。
賀妄一瞬不眨地注視著,嗓音帶笑,“親我一下,我就告訴你。”
沈清蕪哂笑一下,“那算了,我也不是很想知道。”
說完作勢就要從他懷裏出來,但摟著的雙臂力道實在有些大,沒能功。
賀妄的親了親的耳廓,嗓音低沉,“有獨鍾。”
猜你喜歡
-
完結271 章

且以深情共余生
相似的聲音,相似的容貌,遇見了同一個他。兜兜轉轉,走走停停,時光不改蹉跎。如果上天再給她一次重新選擇的機會,她一定奮不顧身愛的更加用力!
50萬字8 9205 -
完結378 章

玄門回來的假千金又在擺攤算卦了
肖梨在玄門待了一百年,同期進來的那條看門狗小黑,都已經飛升上界,她還只能守著觀門曬太陽。老祖宗顯靈告訴她,“肖梨,你本來自異界,塵緣未了,若想飛升,还得回去原来的地方,了却凡尘杂事,方可勘破天道!” 回到现代,肖梨成了鸠占鹊巢的假千金,这一世,没有留念,两手空空跟着亲生父母离开肖家。 圈内人都在等着,肖梨在外面扛不住,回来跟肖家跪求收留。 却不想…… 肖梨被真正的豪门认回,成为白家千金,改名白梨。
64.4萬字8 60458 -
完結189 章

荒腔
沈弗崢第一次見鍾彌,在州市粵劇館,戲未開唱,臺下忙成一團,攝影師調角度,叫鍾彌往這邊看。 綠袖粉衫的背景裏,花影重重。 她就那麼眺來一眼。 旁邊有人說:“這是我們老闆的女兒,今兒拍雜誌。” 沈弗崢離開那天,州市下雨。 因爲不想被他輕易忘了,她便胡謅:“你這車牌,是我生日。” 隔茫茫雨霧,他應道:“是嗎,那鍾小姐同我有緣。” 京市再遇,她那天在門店試鞋,見他身邊有人,便放下了貴且不合腳的鞋子。 幾天後,那雙鞋被送到宿舍。 鍾彌帶着鞋去找他。 他問她那天怎麼招呼都不打。 “沈先生有佳人相伴,我怎麼好打擾。” 沈弗崢點一支菸,目光盯她,脣邊染上一點笑:“沒,佳人生氣呢。” 後來他開的車,車牌真是她生日。
28.8萬字8 1773 -
完結19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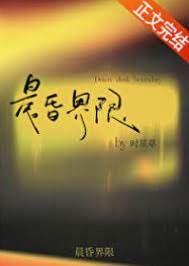
晨昏界限
林霧有些記不太清自己和陳琢是怎麼開始的,等她後知後覺意識到事情變得不對勁時,他們已經維持“週五晚上見”這種關係大半年了。 兩人從約定之日起,就劃分了一條明顯的,白天是互不相識的路人,晚間是“親密戀人”的晨昏界限。 而這條界限,在一週年紀念日時被打破。 - 人前不熟,人後很熟的故事TvT
27萬字8 564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