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妻薄情》 第 307 章 瑣事多
m.kelexsw.com
謝玄英認真考慮了程丹若的建議,而后道:“寨堡改制要上奏朝廷,但屯田可以清查,若以此收編土兵,倒也不是不能試試。”
他這次的主要工作,就是清理軍役,包括了篩查軍戶編制和屯田。
只要愿意查,沒有查不出問題的,這次邊墻寨堡引發了叛,怎麼都得給朝廷一個代。
他越想越覺得可行,不由住的背:“這是個好辦法,我試試。”
“必須雙管齊下。”程丹若叮囑道,“讓土司管理苗人,我們去教苗人耕作,讓他們不再茹飲的生活,時間久了,自然就與漢人融合。”
解決西南的本之策是什麼?扶貧。
“這我知曉。”謝玄英道,“昔年明先生在龍場便是如此,我亦心向往之。”
縣衙一刻鐘的路程,兩人便匆匆商議定了方向,隨后各自行事。
謝玄英接管了清平縣的防務,第一時間便征召民夫鄉勇干活,清理排水道,換值守,安民眾。
程丹若暫時在縣衙的花廳安頓下來,詢問傷者被送往何,人提著準備好的藥前去問。
傷的主要是普通兵卒。
他們被安頓在縣里的一義學,因為謝玄英了大夫,此時已有一個大夫并兩個學理傷口。
程丹若進去的時候,聽見他們說:“放心吧,這是我師傅的獨門藥,好好敷著就不易潰爛。”
好奇地瞥了眼,發現是一團綠的藥糊,便問:“這是用了什麼藥材?”
“這是方!”學警惕地說。
“臭小子,別胡說八道。”正拿刀切除碎的大夫回答,“加了百蟲倉,傷口容易好。”
這是個土名,程丹若稍微用了用金手指,才知道是五倍子,產于云、黔、蜀,算是本地的藥材,北方見。
Advertisement
“原來如此,倒是一味好藥。”笑笑,見大夫裹傷的布條都是士兵裳上撕下來的,忙阻止道,“傷口需要清洗,再用干凈的布條裹好。”
大夫淡淡道:“哪有什麼干凈布條?”
程丹若:“我帶了一些。”
示意家丁搬來箱子,又命人打水,等煮開了加鹽糖包,為傷者補。
大夫這才正眼瞧,有點疑:“夫人是誰?”
“我姓程,也是大夫,略有家學。”程丹若遞上《外傷治療圖》,“煩請按照這上頭的步驟治傷,至于藥,這邊的水土養出來的,自然更適合這里的傷,就用您的吧。”
這《外傷治療圖》,其實就是外傷急救的容,簡單的文字并簡易的圖案,命工匠雕了版,印刷了幾十張帶在邊,以備不時之需。
當然,雕版也一同帶走了,以如今的印刷能力,有現的雕版,一夜間便可印出大量圖紙。
大夫接過圖紙,最初表看起來有點過分平靜,好像在思考怎麼敷衍,但看了會兒,眉梢微微松開,點點頭:“盡力而為。”
程丹若道:“趙。”
“夫人。”今年堪堪二十歲,當年趙護衛的弟弟趙上前半步。
道:“你留在這,有什麼短缺的盡量補上。這里的人是為了百姓才的傷,不要虧待他們。”
趙道:“是。”
“污及時人清理干凈。”程丹若簡單囑咐兩句,“缺人手就雇百姓,先給他們一半的銀錢。”
“屬下明白。”趙還很年輕,以前都是跟在錢明后打下手。如今錢明回京辦事,他也是時候獨當一面了。
理掉傷患的安頓問題,天已經轉暗。
天的夜晚總是來得格外早。
回到縣衙,差役們正一盞盞點起路燈,為省油,三個里只點一個,昏暗得很。
程丹若趁天邊還有一余,趕去探張佩娘。
縣令自覺搬到了前院,將后頭空置的東西廳讓給了他們,張佩娘就住在西花廳那邊,丫鬟們都在廂房里。
雖然局促了些,可經歷過野外宿的窘迫,這也不是不能忍。
“妹妹一切可好?”程丹若關切地問。
“多謝姐姐關心,一切都好。”回到悉的世界,張佩娘立即恢復如常,安頓好里里外外,“我廚房煲了湯,一會兒給姐姐送過去。”
程丹若確實沒來得及顧及吃飯問題,欣然道謝:“多虧了妹妹。”
“姐姐不嫌棄我愚笨才好。”
雙方寒暄兩句,默契地打住。
“不打擾妹妹休息了。”
“姐姐慢走。”
程丹若穿過廳堂,回到東廳,丫鬟們已經收拾好床鋪,擺好了膳食。
瑪瑙端上藥:“夫人。”
“唉。”程丹若額角,先掉滿是塵土的外衫,才接過來將藥一飲而盡。
人參的苦味在口腔彌漫,但喝完,渾都洋溢著暖意,不由松了松領口。
“這是什麼?”謝玄英剛好走進來,一眼瞧見頸邊的青紫,“又傷了?”
“不是。”程丹若解釋,“鎖子甲太沉,蹭破皮了。”
前段時間一直生病,型消瘦,金屬制的鎖子甲沉甸甸地在上,皮薄的地方就易青紫,領口因為磨蹭,刮破了皮。
“給我瞧瞧。”他拿過燈,解開紐扣,仔細看了半天,“涂藥沒有?”
“清理過了,這些傷不需要敷藥。”說,“快吃飯吧,我也了。”
謝玄英搖搖頭,依先用飯。
張家的廚子保持了一貫的水準,鴿子蟲草湯燉得清淡鮮香。
“今兒又沾了。”程丹若喝了口湯,不由道,“佩娘真是周到。”
謝玄英道:“世家貴,都有這八面玲瓏的本事。”
奇怪:“你似乎對頗有不滿?”
謝玄英當然不滿意,城里說不上彈盡糧絕,可也算不上富裕,倒好,住下就霸占灶頭,燉湯、炒菜、要熱水,聽說張家丫鬟還出去買,說今晚要喝糜粥。
然則口中道:“別家之人,有何滿意不滿意之說?”
“別生氣了。”程丹若給他舀個鴿子蛋,“人家自己的廚子,自己的錢,你管吃喝呢。”
“我也沒說什麼。”謝玄英把蛋夾回碗里,“你吃。”
“我已經吃了一個。”說。
他言簡意賅:“吃掉。”
程丹若不不愿地又夾起來。需要補充蛋白質,但在路上,牛和羊都不易保存,還是蛋類更好。
“算了。”謝玄英不忍地看著。他到現在還記得,在婚后是怎麼自己吃蛋的,“我吃吧。”
然后,就著的手吃了。
程丹若一下輕松,多吃了兩片火。
謝玄英又給夾了兩筷炒片。
“夠了夠了。”
今晚的菜不多,就鴿子湯、炒片和兩道素菜,兩人很快吃完,喝茶消食。
稍稍歇了會兒,程丹若了熱水洗漱。
“丹娘。”謝玄英立在簾子后,“我想看看你的傷。”
程丹若左右看看,覺不嚴重,起簾子:“只是傷。”
謝玄英放下手中的燭臺,解開的抹系帶,立馬就看見后背的淤青:“背上是怎麼回事?”
“背上也有?”怪不得平躺有點痛。
解釋,“轎子上坡下坡容易晃,大概不小心撞到了吧。”
他出手,輕輕的瘀傷:“痛嗎?”
程丹若搖搖頭。
“我給你。”謝玄英不容分說地拿起布巾,擰得半干,慢慢拭的皮。有淤青,他就把熱巾敷在上面一會兒。
孔舒展的覺很好。
程丹若被裹在的布巾里許久,才穿好裳。“好了。”他說,“去帳子里坐著,小心蟲咬。”
小小的飛蟲圍繞著書燈盤旋。
拿起桃木梳,鉆實的帳中,慢慢梳發通頭。
沒一會兒,謝玄英也洗漱完畢,坐進帳子。
程丹若問:“要梳嗎?”
他點頭,取下網巾,打松發髻。
烏黑的頭發散落,與的發混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用了同樣的頭油,連香氣都是如出一轍的芬芳。
他個子高,哪怕坐著,程丹若也夠得費力,干脆坐到他上,一下一下慢慢梳。
謝玄英摟住的腰,覺到淺淺的呼吸撲在耳邊,心里漸漸寧靜。
奔波三日,他也疲倦不已,只不敢于外人面前。
“這次的差事,怕是不容易。”他開口。
程丹若平靜地說:“我看出來了。”
“丹娘……”
“沒有后悔。”
微風吹青的紗帳。
謝玄英低頭,在朦朧的燭中,輕輕吻住的。
他們換了一個淺淺的吻,不帶任何,只有無邊的。
“睡吧。”程丹若的眼皮忽而沉重,“我困了。”
謝玄英吹滅燈燭,攬懷:“你后背有瘀傷,靠著我睡。”
“嗯。”
--
次日早上,程丹若朦朦朧朧地醒來。
晨照亮窗邊,瞇著眼,看見謝玄英正坐在案前寫折子,便含糊地問:“你在寫什麼?”
“寨堡的事。”他說,“還早,你再睡會兒。”
見奏折才起頭,程丹若的眼皮又變得沉重。翻個,很快再度夢。
半個時辰后,謝玄英擱筆,奏疏擬完了。他從頭到尾看了兩遍,吹干墨跡,將奏疏折起,放到了枕邊。
程丹若睡得正香,微穿過紗簾的空隙,落在被子上變無數個點。微微蜷,雙手錯擱在前,被角出舒展的腳趾頭。
謝玄英撓撓的腳底心。
果然,馬上把腳回去了,但并沒有醒。
謝玄英微微彎起角。
他知道,只要是他做的小作,無論發出什麼聲響,都不會輕易驚醒,但如果是丫鬟們,再輕手輕腳的,也會很快睜眼。
仔細捻好被角,謝玄英過的臉龐,悄悄離去。
今天還有很多事要做。
影漸亮。
一刻多鐘后,程丹若回籠覺睡醒,轉頭就看見枕畔的折子。
撐起,不梳頭也不洗臉,先把折子看了。
謝玄英的奏疏是他既往的風格,言辭優,態度懇切,仿佛能看見一個儀態典雅的貴公子不卑不地陳述著什麼。
容大意是:
他在上任的路上遇到了苗人作,起因是寨堡的軍侵占苗田,(在詢問過寨堡游兵殘部后),他確認苗人所陳述的冤屈確有其事,寨堡深苗疆腹地,消息閉塞,許多軍懈怠本職,耽于樂,致使沖突。
故此,提議清理貴州寨堡,命各地長司治理,征召土兵充實寨堡,以夷治夷,既分化苗部,也可減緩漢苗沖突,平衡各方勢力。
平心而論,謝玄英的奏疏完善了程丹若昨天的提議,但看完后,卻決定把這封奏折一。
黔東南就這麼復雜,之后指不定還有什麼事兒,現在提這個沒什麼用,還是再等等。
猜你喜歡
-
完結159 章

嫁給奸臣沖喜后
傅瑤要嫁的是個性情陰鷙的病秧子,喜怒無常,手上沾了不知多少人的血。賜婚旨意下來后,不少人幸災樂禍,等著看這京中頗負盛名的人間富貴花落入奸臣之手,被肆意摧折。母親長姐暗自垂淚,寬慰她暫且忍耐,等到謝遲去后,想如何便如何。傅瑤嘴角微翹,低眉順眼地應了聲,好。大婚那日,謝遲興致闌珊地掀開大紅的蓋頭,原本以為會看到張愁云慘淡的臉,結果卻對上一雙滿是笑意的杏眼。鳳冠霞帔的新嫁娘一點也不怕他,抬起柔弱無骨的手,輕輕地扯了扯他的衣袖,軟聲道:“夫君。”眾人道謝遲心狠手辣,把持朝局,有不臣之心,仿佛都忘了他曾...
46.3萬字8 58850 -
完結36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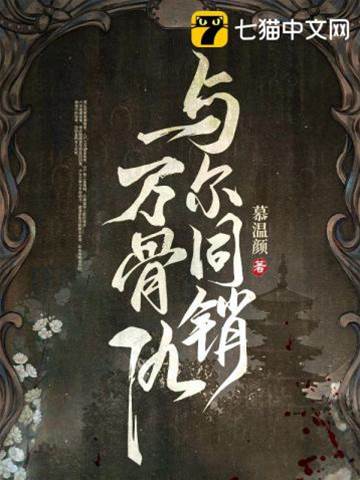
與爾同銷萬骨仇
深山荒野狐狸娶親,人屍之內竟是魚骨,女屍愛上盜墓賊,吊滿詭異人影的地宮...... 六宗詭譎命案,背後隱藏著更邪惡的陰謀。 少女天師與年輕尚書,循著陰陽異路解決命案,卻每每殊途同歸。 暗夜中的枯骨,你的悲鳴有人在聽。
32.6萬字8.18 8221 -
完結191 章

妾身嬌貴
莊綰一直以為,她會嫁給才華冠蓋京城的勤王與他琴瑟和鳴,為他生兒育女。然,一夕之間,她想嫁的這個男人害她家破人亡,救下她後,又把她送給人當妾。霍時玄,揚州首富之子,惹是生非,長歪了的紈絝,爛泥扶不上牆的阿鬥。初得美妾時,霍時玄把人往院裏一扔讓她自生自滅。後來,情根已深種,偏有人來搶,霍時玄把小美人往懷裏一摟,“送給爺的人,豈有還回去的道理!”
51.9萬字8.18 18298 -
完結347 章

囚她
施家二小姐出嫁一載,以七出之罪被夫家休妻,被婆婆請出家門。 無子;不事舅姑;口舌;妒忌。 娘家一席軟轎把她帶回。 她住回了自己曾經的閨房。 夜裏,她的噩夢又至。 那人大喇喇的端坐在她閨房裏,冷笑睨她。 好妹妹,出嫁一年,連自己娘家都忘了,真是好一個媳婦。 她跪在他身前,眼眶皆紅。 他道:“不是想要活着麼?來求我?” “你只許對我笑,對我體貼,對我賣弄,對我用十分心計,藉由我拿到好處。”
56萬字8.18 325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