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梟寵成癮:病嬌少帥的嬌妻是大佬》 第38章 舊識
席蘭廷有事,雲喬起回。
不想,席蘭廷直接當著雲喬的麵問:“什麽客?”
“北平來的貴客,薑總長家的夫人和爺小姐。督軍不在,他們過來拜訪老夫人。薑與小姐都是年輕人,老夫人讓您去款待。”席榮細細回稟。
席蘭廷頷首。
他站起,複又看了眼雲喬:“一起去吧,你也該多結識些朋友。”
雲喬搖頭:“我不跟這些高子弟打道,不去了。”
說罷,轉,利落走了。
回到了四房,家裏鬧哄哄的,年輕男談笑聲幾乎衝破屋頂。
雲喬愣了愣。
婢靜心早已瞧見回來,急忙到門口迎接,低聲向說明屋況:“九小姐的同學,男男來了十幾人。”
席家子排序,是大家族一起,故而席文瀾被人稱“九小姐”。
Advertisement
隻是家裏孩子太多了,記住們的名字,反而比記住們的排行容易。
大部分傭人稱呼席文瀾都是一句“文瀾小姐”。m.X520xs.Com
雲喬心中了然。
盡可能低調,打算悄悄進屋,悄悄上樓。
不想,客廳裏幾名男學生,在雲喬進門瞬間,都看向了。
雲喬生得極其打眼,年輕人閱曆淺薄,還沒見過太絕的人,故而目不轉睛。
席文瀾的笑聲,在後響起:“雲喬,你回來了?”
然後向同學介紹,“這是我妹,雲喬。對了雲喬,你姓什麽?你是跟外婆姓,還是跟媽姓?”
同學們很費解。
席文瀾丟下一個疑團,卻不解釋。
雲喬沒什麽表示,對席文瀾暗中將和席家撇清的言語,也不放在心上。
人人都知席家人尊貴。
席家的便宜,豈是那麽容易占?
待要上樓,倏然餘瞥見一人。
那人站在客廳長窗邊,鋪陳了他滿。他穿一件咖啡平紋襯衫、深咖西,站得筆直,近乎鋒利。
瞧見雲喬轉臉,他笑了起來,出了一口白森森的牙。
他瞳仁漆黑,像是想要把什麽都吸,剝皮拆骨碾齏,毫不掩飾他渾的侵略氣息。
雲喬眼神一。
席文瀾察覺到了,笑問:“徐同學,你認識我妹妹?”
徐寅傑往前走了幾步,低頭看著雲喬,鋒眉舒展,可笑容卻帶著嗜般的進攻:“不太認識。不過,這位小姐倒好像認識我。”
雲喬轉,快步上樓。
輕輕按了下口。
怎麽回事,徐寅傑怎麽跑到燕城來了?
更休息,拿出書來看。這次看的,是一本英文小說。
半個小時後,樓下響起了鋼琴聲與歌聲,更加熱鬧了。
雲喬的房門卻被輕輕敲響。
以為是長寧,起開了門。
門口站著的,卻是徐寅傑。
他衝笑,一口白牙幾乎能閃爍寒芒,像是隨時要咬雲喬一口:“喬喬,好久不見。”
雲喬:“……”
“躲我做什麽?”他仍是笑著,哪怕眉目舒展,他麵部線條也比旁人鋒利幾分,“怕我?”
“誰怕你?”雲喬板著臉,“手下敗將,你還敢搞鬼不?”
徐寅傑爽朗笑起來,舉了舉手:“是是是,不敢搞鬼。敗將親自上門了,不請我吃個飯、喝杯咖啡?”
。您提供大神明藥的梟寵癮:病帥的妻是大佬
猜你喜歡
-
完結11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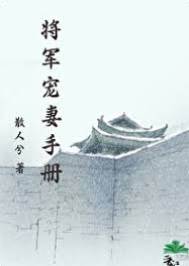
將軍寵妻手冊
雲府長女玉貌清姿,嬌美動人,春宴上一曲陽春白雪豔驚四座,名動京城。及笄之年,上門求娶的踏破了門檻。 可惜雲父眼高,通通婉拒。 衆人皆好奇究竟誰才能娶到這個玉人。 後來陽州大勝,洛家軍凱旋迴京那日,一道賜婚聖旨敲開雲府大門。 貌美如花的嬌娘子竟是要配傳聞中無心無情、滿手血污的冷面戰神。 全京譁然。 “洛少將軍雖戰無不勝,可不解風情,還常年征戰不歸家,嫁過去定是要守活寡。” “聽聞少將軍生得虎背熊腰異常兇狠,啼哭小兒見了都當場變乖,雲姑娘這般柔弱只怕是……嘖嘖。” “呵,再美有何用,嫁得不還是不如我們好。” “蹉跎一年,這京城第一美人的位子怕是就要換人了。” 雲父也拍腿懊悔不已。 若知如此,他就不該捨不得,早早應了章國公家的提親,哪至於讓愛女淪落至此。 盛和七年,京城裏有人失意,有人唏噓,還有人幸災樂禍等着看好戲。 直至翌年花燈節。 衆人再見那位小娘子,卻不是預料中的清瘦哀苦模樣。雖已爲人婦,卻半分美貌不減,妙姿豐腴,眉目如畫,像謫仙般美得脫俗,細看還多了些韻味。 再瞧那守在她身旁寸步不離的俊美年輕公子。 雖眉眼含霜,冷面不近人情,可處處將人護得仔細。怕她摔着,怕她碰着,又怕她無聊乏悶,惹得周旁陣陣豔羨。 衆人正問那公子是何人,只聽得美婦人低眉垂眼嬌嬌喊了聲:“夫君。”
17萬字8.33 56909 -
連載222 章

危情:賜她囚籠
簡介: 他從地獄而來,誘她入局。初次相見,她成了砧板上的魚肉,任他宰割。蘇桐:“為什麽是我?”顧聞景的目光有些駭人,他皺了下眉,思緒被拉離到過去,片刻後他俯視著眼前的蘇桐:“男人都好美色,我也是個膚淺的人。”“顧總身邊的美女無數,這個理由也太牽強。”顧聞景笑了笑,她果然聰明又警惕,和小的時候一模一樣。“美女雖多,可像你這般聰明的卻少,我喜歡聰明的女人。”顧聞景說這話時,又點了一支煙。……後來她成為他的私有物品。她以為她能夠在他身邊慢慢豐滿羽翼,她以為能夠展翅高飛,可他卻賜予她囚籠,將她傲骨斬斷,羽翼折斷,玩弄於股掌之間。“顧聞景,放過我吧。”“蘇桐,我是個生意人,不做虧本的買賣。”她看著麵前像惡魔的男人,無奈地苦笑,如果當初她識破那場騙局,如果當初她選擇逃離,一切就不會是這種局麵。
42.7萬字8 1708 -
連載575 章

孕吐後奉子成婚:孩子是死對頭的
紈絝浪子小少爺vs外冷內熱事業女先婚後愛 奉子成婚 閃婚 日久生情 暴力禦夫術 紈絝少爺 女強人花鬱塵被誤診孕吐,陰差陽錯的發現淩苗懷孕了。沒錯,孩子是他的。但是,他們是一言不合就開罵的死對頭 滿京城的人都知道,花鬱塵是花家三代單傳的獨苗苗,身份金貴,妥妥的紈絝子弟一個。 而且還有個明戀了好多年的白月光。喜當爹?花鬱塵才不想英年早婚。 他不喜歡淩苗,可敵不過家裏人喜歡。 老爺子更是氣不過,揚言要打死他這個始亂終棄的兔崽子。 ———— 淩苗是個硬骨頭,覺得奉子成婚,會被人詬病她把花家當成搞事業的墊腳石? 誰知道花家爺爺明說,墊!讓她墊!花家就做她的墊腳石。 淩苗心一狠!嫁! 以後她就是花家的少奶奶,紈絝子弟?狐貍精?她黑帶三段,who怕who?搞錢搞事業,暴力禦夫術,手撕狐貍精,她手拿把掐。 花鬱塵苦不堪言:爺爺,你這是要親手斷了花家的香火啊? 老爺子:誰說的?花家的香火在孫媳婦肚子裏。
98.9萬字8 4787 -
完結154 章

超甜軍婚:不嫁霸總,嫁軍爺!
【現代軍婚+年齡差+暗戀成真+豪門小可憐記者VS特種最強軍官】因為一場旅游,荀桉眠意外亂入戰場。遇險絕望時,傅時樾從天而降。 再次遇見,她是身陷詐騙窩的臥底記者。為了不嫁紈绔霸總,荀桉眠閃婚了最強軍爺! 本以為結婚是他逼不得已的妥協,卻不想婚后的荀桉眠不僅被傅時樾寵成公主,更找回親人,走上人生巔峰。 有一天,荀桉眠忽然發現,曾經高冷禁欲的軍官,早在不知不覺間變得粘人,總愛抱著她親親。 遇到荀桉眠之前,傅時樾心無旁騖。 遇到荀桉眠之后,他說他的心不大,只有她和國家。 家國他要守護!她,亦然!
27.1萬字8 17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