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門嬌嬌一睜眼,偏執王爺來搶親》 第641章 云祁的手藝也不怎樣
“好啊!”
謝昭昭也心愉悅。
他們這夫妻倆,其實真正能膩在一起的時間并沒有那麼多,大部分時間各自忙碌,或者謝昭昭會關注娘家。
所以難得空閑能膩在一起的時候,謝昭昭都很是珍惜。
扶著云祁的手到鏡臺前坐下。
香桂趕讓人給云祁搬了個圓凳來。
云祁坐在謝昭昭邊,手指一勾,將那發帶解開,手指梳著的長發,“你想挽什麼髻?”
“我隨意……”謝昭昭先這般說了一聲,后又說:“不過我覺得,在家里的話垂掛髻舒服一點吧。”
其實是垂掛髻更簡單一點。
至謝昭昭這樣認為。
云祁點點頭:“那就給你挽垂掛髻……你來教我。”
他看向香桂。
“是。”香桂屈行禮后,站在謝昭昭的后,拿了木梳來幫謝昭昭整理頭發。
云祁也站起了,朝手。
香桂把梳子給云祁。
云祁說:“你站在旁邊,告訴我怎麼弄就可以,我自己來。”
香桂又應了一聲是,規規矩矩站在一側。
云祁把謝昭昭那頭墨染一樣的秀發仔細地梳理的一遍,梳理的很順之后,香桂便告訴云祁怎麼挽。
謝昭昭在鏡子里看著自己的青繞在云祁的指尖。
其實謝昭昭想錯了。
Advertisement
垂掛髻是看似簡單卻需要一些手法的,云祁顯然沒手法,還有些笨拙。
弄了好一會兒,沒弄好,還把謝昭昭拉疼了好幾次。
一開始還面帶笑意的云祁,逐漸就變得張起來,還時不時飛快地抬眸看鏡子里的謝昭昭一眼,很是小心翼翼。
當對上謝昭昭帶著揶揄笑意的眼睛時,云祁略略尷尬,輕咳一聲,而后卻浮起幾許窘迫的紅。
香桂想笑不敢笑,只能耐心地指點。
李嬤嬤進來了一趟,瞧見云祁和謝昭昭二人正閨房趣,也掩笑了一下沒出聲。
把下人使喚退下之后,自己倒是沒退走,站在月亮門邊瞧著。
云祁著實是有一點手忙腳。
住了這一縷,那一縷掉下去了,好不容易都夾在指之中,卻沒法用珠花固定,面難,劍眉擰。
謝昭昭終于忍不住“噗嗤”輕笑一聲,“還是讓香桂來吧。”
“我覺得我可以。”云祁地說著,又試了一下,謝昭昭那幾縷頭發非常不給面子地掉了下去,云祁本來要別住發梢的珠花也扎了謝昭昭頭皮一下。
云祁面大變,連忙將手指落在謝昭昭頭頂,輕輕了:“弄疼你了嗎?”
“倒是不疼。”謝昭昭抓住他的手牽在自己手中:“不過你要是繼續折騰下去,下一次可能會弄疼的。”
認真建議:“還是讓香桂來吧。”
“……”
云祁默默片刻,飛快點了點頭,又坐回了謝昭昭邊去。
香桂重新走到謝昭昭后站定,手指翻飛之間很快就挽好了一個漂亮的垂掛髻。
云祁盯著想瞧一瞧,奈何沒怎麼看清楚一切就結束了。
這讓云祁不瞇起了眼睛。
“你去忙吧。”謝昭昭讓香桂退下。
云祁皺眉瞧著香桂——的手,覺得有點不可思議,他的視線一路跟隨。
香桂走到月亮門口的時候,云祁的視線也追過去,就瞧見了一直朝里看的李嬤嬤。
李嬤嬤連忙朝云祁笑。
云祁卻笑不出來。
李嬤嬤自小服侍他,分自然不同,云祁和視線一對,就流出幾分窘迫來。
大致上……自己方才手忙腳的樣子應該丟人。
“老奴也退下了!”
李嬤嬤懂事地屈了屈膝,和香桂一起退出去。
“好啦,還看!”
謝昭昭雙手捧住云祁的臉,將他轉過來面對著自己,“人都走了,你盯著瞧什麼呢?喜歡上香桂那雙手了嗎?”
“是嫉妒。”
云祁一板一眼地更正,“我第一次覺得,自己如此無能,這雙手白長了。”
謝昭昭笑得歡快:“你明白就好……你再怎麼能干,也有你干不了的事哦?你的‘手藝’這回不是不怎麼樣,是很差!是沒有!”
那“手藝”二字,謝昭昭咬的略重。
云祁如何聽不出來話中有話,臉微微一黑,“你等著,這手藝我一定會有,還會很好。”
“行吧,我等著。”
謝昭昭抓住云祁的手搖了搖:“阿祁,我們今日做什麼?”
義診那邊有醫士,還有紅袖和玄靖盯著,本也不是要謝昭昭每日到場。
先前只是云祁不在府上,謝昭昭無事可做,再加上修建白云觀的事一直吊著,所以謝昭昭便每日都去,都大半個月了呢。
今日云祁難得在家,謝昭昭自然也讓自己放松一二,想一起做點什麼。
云祁想了想說:“你現在肚子大了,練劍騎馬定然都不行……我不然陪你回謝家一趟吧,你看看岳母,和你姐姐還有嫂嫂們說說話。”
謝昭昭眼睛一亮:“也行!”
謝昭昭又說:“明日你還休沐對不對?咱們去東宮看太子……就不知道太子殿下明日得不得空。”
“今天便送消息過去,明日父子便會得空了。”
云祁了謝昭昭額角,“這就走吧。”
他一路牽著謝昭昭從寒月軒出來,到門前馬車便,抱著妻子送到車上。
回去的路上,謝昭昭的腦袋歪在云祁肩頭,說起謝家,說起謝長珩還沒治好的,謝嘉嘉的月牙,陳書蘭那一對雙胞胎,還有元宵和謝佳怡。
云祁著的手靜靜聽著,目卻是落在了謝昭昭的肚子上。
再過兩三個月他們也該有孩子了呢。
他甚至連孩子的名字都空想了好多,有男有,到時候生男生都有的用。
希這一切早點塵埃落定,到時候他能安心地陪在謝昭昭邊,陪在生產。
馬車在這時候停下來。
云祁帶著謝昭昭下了車。
謝昭昭疑地看著不遠的馬車:“這是陸先生的車嗎?”
“是的。”門前守衛上前回話:“陸先生剛進去,說是來給四公子看的。”
“原來如此!”
謝昭昭笑道:“陸先生一向說話算數,答應了的事就這般上心。”
“嗯。”
云祁點了點頭,牽牢了謝昭昭的手,眼神溫,心中卻過一抹微妙思緒。
猜你喜歡
-
完結1250 章

法醫王妃:我給王爺養包子
坊間傳聞,攝政王他殺人不眨眼,吃人不吐骨頭,所到之處,寸草不生。 蘇七不過是從亂葬崗“詐屍”後,誤惹了他,從此他兒子天天喊著她做孃親。 她憑藉一把柳葉刀,查案驗屍,混得風聲水起,惹來爛桃花不斷。 他打翻醋罈子,當街把她堵住,霸道開口:“不準對彆的男人笑,兒子也不行!”
216.9萬字8.18 52483 -
完結2007 章

神醫狂妃:娘親你馬甲又掉了!
大齊國的人都以為瑾王妃只是個寡婦,瑾王府也任人可欺。可有一天,他們發現——神醫門的門主喊她老祖宗。天下第一的醫館是她開的。遍布全世界的酒樓也是她的。讓各國皇帝都畏懼的勢力是她的外祖家。就連傳說中身亡的夜瑾居然都回來了,更是將她疼之入骨,寵入…
181.2萬字8 94733 -
完結7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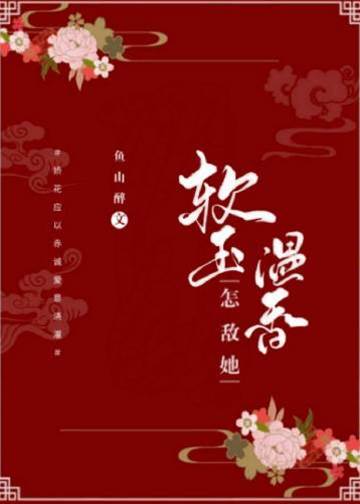
怎敵她軟玉溫香
提起喬沅,上京諸人無不羨慕她的好命。出生鐘鳴鼎食之家,才貌都是拔尖兒,嫁的男人是大霽最有權勢的侯爺,眼見一輩子都要在錦繡窩里打滾。喬沅也是這麼認為的,直到她做了個夢。夢里她被下降頭似的愛上了一個野男人,拋夫棄子,為他洗手作羹湯,結果還被拋棄…
21.9萬字8 11801 -
連載2178 章

替姐出嫁後,錦鯉農女逆襲了
荒年,任家一車糧食就將宋九換走,成了任家傻兒子的媳婦,都說傻子兇狠殘暴還咬人,咬一口就得病幾日,世人卻不知,傻夫有三好:相貌好、身材好、體力更好。 錦鯉體質的宋九,嫁到任家就成了團寵,好事一樁連一樁,任家生活也越過越好。 隻是她這個傻夫身份卻變得不簡單,親生父母來相認,爹不疼娘不愛?沒關係,宋九護短疼丈夫。鬥極品虐渣渣,帶著傻夫發家致富,誰也別想欺負他。 宋九:“榮長隻有我能欺負。” 任榮長:“隻有媳婦能欺負我,其他人都不準欺負我媳婦。”
404.1萬字8.33 47784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