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孕後渣老闆每天都想拿掉我的崽》 第95章 誰先動心
�
ル年會過後沒兩天,公司就放了長假。
比起法定假期,多給了三天的休息時間。
大年初十才需要到崗。
江稚簡單收拾了行李,提前買好了回南城的機票。
春節假期,機票比平時要難買一些,價格也有所浮。
臨近出發,江稚去了趟醫院,每個周末都會病房看看母親,握著的手和說說話,哪怕依然是什麽反應都沒有。
有時候江稚著呼吸機平穩的線條,也在思考自己是不是不應該這樣強行挽留住母親的命。總覺得的母親有朝一日會醒過來,可能要過去很久很久,但是能等。
要放棄,實在做不到。
總是那麽自私的抱著一線生機。
江稚去見了醫生。
醫生已經很委婉,“希是有的,但是不大。”
想要從植人狀態中清醒過來,全然是看老天爺了。
或是病人有沒有足夠的求生,可既然當初選擇決絕的從臺上跳下去,早就沒了求生意誌。
江稚承得了,的臉有點白,“沒事的,我相信我媽媽會醒過來的。”
媽媽一定舍不得丟下。
還沒有看見江北山的報應。
怎麽甘心就這麽一直沉睡下去呢?
江稚總是幻想,等母親醒來,等一切結束,要帶著媽媽回南城的小鎮上,好好生活。
醫生覺得可憐,但也沒說多餘的話。
Advertisement
未必會聽,“我們也會盡力醫治,希能看見奇跡。”
江稚見完醫生又回病房陪媽媽說了一些話,絮絮叨叨,到最後也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麽,“昨天是我和沈律言的結婚紀念日。”
“媽媽,你還記得沈律言嗎?我跟你說過的。”
“他是我的丈夫,也是喜歡的人。”
“但是我們應該過不了多久就會離婚。”
“離婚了也好,他一直都不喜歡我,我確實很難過的。”
江稚和媽媽嘮叨了這麽多的話,好像又沒有那麽難過了:“媽媽,我要去看看外公外婆,今年過年想去陪陪他們,等過完年我就回來。”
從媽媽出事,江稚就變得很不喜歡過年。
萬家燈火裏,沒有屬於的一盞。
盛世煙花,隻剩孤寂。
年年都是如此,總是孤一人。
江家不歡迎,傅家早就沒了。
舅舅還在服刑,媽媽在住院。
什麽時候能好起來呢?江稚不知道,但想總會有那一天的。
江稚從醫院離開,直接打車去了機場,路上又遇堵車,尤其是高架橋堵的水泄不通,還好離乘坐的班機,起飛時間還早。
不趕時間,通過堵車路段,路況就好多了。
江稚喜歡預留足夠的時間來辦登機手續,由於天氣不好,航班延誤了將近一個小時。
江稚耐著子在候機廳裏等待,著窗外起起落落的飛機,又升出一種無法用語言表達的孤獨。收回視線,打開手機,猶豫再三,還是選擇給沈律言發了條短信:【沈先生,我回南城了,有要事你可以打電話給我。】
發完這條,盯著對話框裏發了會兒呆。
又過去了會兒,輕輕在手機鍵盤摁下幾個字:【另外,祝您春節快樂。】
發完就退出了微信。
仿佛知道不會得到他的回應。
又或者要等待很久,才能收到他的回複。
江稚今天出門前,鬼使神差的戴上了婚戒,樸素的鉑金戒指,沒有鑽石,也沒有刻字,看起來普普通通。
不知的人看見了隻會當裝飾品。
江稚抬起手,盯著拇指上的婚戒看了好一會兒。
隻見過沈律言佩戴過一次婚戒,那是他第一次帶回沈家的老宅吃飯,先斬後奏,瞞著家裏人和領證結婚不久。
他的手指頭特別漂亮,削瘦白皙,骨節寸寸分明,又不失力道。
青筋在薄薄的皮底,管時時現。
長指白瘦,佩戴上戒指,偏有種人夫的。
不過從那天之後,江稚就沒見他戴過,戒指被他收了起來,丟在了屜的角落裏,腐朽生灰,大概這輩子都不會再拿出來。
因為沒有用了。
就像這個人一樣,對他的用很有限。
*
晚上十點,江稚上了飛機,兩個多小時的航程,睡得迷迷糊糊,後腦昏昏沉沉醒來還有點疼痛。
飛機落地時已過淩晨,機場裏還是人來人往。
大多都是著急回家過年的旅客。
江稚打開手機,微信跳出幾條未讀消息。
置頂的聯係人,回了幾個簡短的字:
【路上小心。】
【春節快樂。】
江稚的手指輕輕著屏幕,指腹依依不舍到了這幾個字。
看了眼時間,他隔了兩個小時才回。
他好像總是很忙。
江稚其實很討厭等待他回複消息的這種覺,好像這樣也是在卑微的這方。
不過本來先心的那個人,就是輸家。
江稚平時很會給他發這些,生怕走一一毫喜歡他的風聲。
江稚從機場打車回了以前住的巷子,時間很晚,毫無困意。
淩晨一點,看見沈律言更新了一條朋友圈。
一張很簡單的圖片。
他和江歲寧高中的畢業照。
當然,照片上不止他和江歲寧兩個人。
盡管是班級合照,最矚目耀眼的就是站在中間的兩個人。
年雙手兜,眉眼桀驁,麵對鏡頭的笑容卻依然燦爛,他邊的孩輕輕靠著他的肩膀,被他抓著手對鏡頭比了個剪刀手。
江稚看著這張照片,說不上什麽滋味。
沈律言幾乎沒有更新過朋友圈,更不會無聊到發從前的照片,很快得到了答案,他意簡言賅在評論區解釋:【玩遊戲輸了。】
江稚知道他們那群人關係很好。
今天晚上,應該是一起聚餐吃了飯。
江稚和沈律言也玩過遊戲,賭注往往是錢,但是從來沒有贏過他。
他也從來沒輸過。
有些敗局,是他心甘願。
江稚給他點了個讚,幾秒種後又有些後悔,默默取消了點讚。
以為沈律言不會看見,剛準備關手機睡覺,那邊就發來了消息:【到了嗎?】
江稚忍著心髒的窒悶回複他:【嗯。】
沈律言說:【早點睡。】
江稚今晚可能又要失眠,說:【你也是。】
【沈先生,晚安。】
沈律言沒有再回了。
每次對話的最後,都是以結尾。
猜你喜歡
-
連載0 章
嬌寵甜妻鬨翻天
前生,她心瞎眼盲,錯信狗男女,踏上作死征程。 沒想到老天開眼,給了她重活的機會。不好意思,本小姐智商上線了!抱緊霸道老公的大腿,揚起小臉討好的笑,“老公,有人欺負我!” 男人輕撫她絕美的小臉,迷人的雙眸泛著危險,“有事叫老公,沒事叫狗賊?” 寧萌萌頭搖的如同撥浪鼓,並且霸道的宣告,“不不不,我是狗賊!” 男人心情瞬間轉晴,“嗯,我的狗我護著,誰虐你,虐回去!” 從此,寧萌萌橫著走!想欺負她?看她怎麼施展三十六計玩轉一群渣渣!
246.6萬字8 59408 -
完結518 章

團寵女鵝是偏執大佬的白月光
錦城豪門姜家收養了一對姐妹花,妹妹姜凡月懂事大方,才貌雙全,姐姐姜折不學無術,一事無成。窮困潦倒的親生家庭找上門來,姜家迫不及待的將姜折打包送走,留下姜凡月;家產、名聲、千金大小姐的身份、未婚夫,從此以后盡數跟姜折毫無關系。.姜折踏入自己家…
95.4萬字5 132631 -
完結1752 章

腹黑萌寶,總裁爹地寵入骨
溫酒酒愛了傅司忱十年,結婚后傅司忱卻因為誤會選擇了其他女人。當他帶著帶著大肚子的林柔柔回來之后,溫酒酒失望至極,決心離婚。挺著一個大肚子,溫酒酒一尸三命。五年后,溫酒酒以大佬身份帶著兩只小萌寶回歸。瘋了五年的傅司忱將她抓回家中:“我們還沒離婚,你生也是我的人,死也是我的人!”當看到兩只翻版小萌寶時,傅司忱急了,“你們是誰?別搶我老婆!”
162.3萬字8 399631 -
完結1685 章
愛上你劫數難逃
一場代嫁,她嫁給了患有腿疾卻權勢滔天的男人。“我夜莫深不會要一個帶著野種的女人。”本以為是一場交易婚姻,誰知她竟丟了心,兜兜轉轉,她傷心離開。多年後,跟他長得一模一樣的小正太一巴掌拍在夜莫深的腦袋上。“混蛋爹地,你說誰是野種?”
303.9萬字8 22994 -
完結19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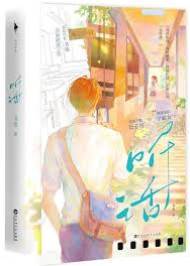
聽話
那不是程歲寧第一次見周溫宴。 她見過他意氣風發,見過他浪蕩不羈,見過他懷裏女孩換了一個又一個。 只是那次,她心動最難捱。 那天室友生日她走錯包間,偶然窺見他懶懶陷在沙發裏,百無聊賴撥弄打火機。 火苗忽明忽暗身旁女生和他說話,他勾着笑半天敷衍回個一字半句。 她回到包廂裏第一次鬼迷心竅主動給他發了信息,【今天聚會好玩嗎?】 下一秒,他回:【你不在沒意思。】 後來他們分手,多年後在風雨裏重逢,她被男友差遣輕視狼狽不堪。 他跨過一衆圍着他殷勤討好的人羣,不顧目光,拉住她的手,塞進一把傘。 冬夜昏天暗地光線裏,他垂眼看她,聲音淡淡:“撐傘,別淋雨。” 那一刻她這才知道,除了他以外都是將就。 朋友問那再後來呢?她淺笑着沒說話。 只是每年西園寺,雲蒸霞蔚煙火繚繞的銀杏樹下多了個虔誠的少女。 那天年初一,青衣僧人說有緣人贈了她一張紙條。 展開一看,字體熟悉,上面寫着‘一歲一禮,得償所願。’ 她下意識回頭,人海茫茫裏,一眼只看見他溫柔背影。
34.2萬字8.18 6032 -
完結94 章

他的鳶尾
【先婚后愛】【蓄謀已久】【暗戀】【甜文】【雙潔】裴琛是京城有名的紈绔子弟,情場浪蕩子,突然一反常態的答應貴圈子弟最不屑的聯姻。結婚后,他每天晚出早歸,活脫脫被婚姻束縛了自由。貴圈子弟嘩然,阮鳶竟然是只母老虎。原本以為只是短暫的商業聯姻,阮鳶對裴琛三不管,不管他吃,不管他睡,不管他外面鶯鶯燕燕。后來某一天,裴琛喝醉了酒,將她堵在墻角,面紅耳赤怒道:我喜歡你十六年了,你是不是眼瞎看不見?阮鳶:……你是不是認錯人了?我是阮鳶。裴琛:我眼睛沒瞎,裴太太。
31.8萬字8.18 740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