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縷衣》 第106頁
過了好一會兒,魏姩還是沒忍住,仰頭看著他問:“為什麼?”
仔細回想,他當時抱的是,并非齊云涵,所以其實,或許,他也是想救的?
可這麼高的懸崖跳下來生死不知,他為什麼這麼做?
褚曣沒有睜眼,淡淡道:“孤想跳就跳,需要理由?”
魏姩抿了抿仍盯著他。
半晌后,他道:“若真要說出個一二,孤的人在孤的地盤上被人弄死,孤豈不是很沒面子?”
魏姩眸一閃,長睫輕輕。
誰是他的人啊!
但他的這個回答是不是也說明,他跳下來的理由中,確實有。
一時不知該如何接這話,卻聽他嗓音微啞道:“孤方才做了一個夢。”
魏姩順著話問道:“殿下做了什麼夢?”
褚曣沉默了好半晌,才徐徐道:“孤夢見孤去奉京獄,有一個渾是的子求孤賜一死。”
Advertisement
褚曣依舊閉著眼,便沒看見魏姩那一瞬間的震驚錯愕。
直勾勾看著褚曣,渾的都仿若有一刻的凝滯。
“孤約知道是殺人犯,殺了一個對孤來說,很重要的人。”
魏姩的不由自主的一抖,無比慶幸這一刻褚曣是閉著眼的,否則本無法完的掩飾自己此時此刻的神。
“孤瞧了一會兒,但看不清臉。”
“孤好像連夜又查了一次那個案子,仍舊沒有找出破綻,得知判下凌遲,天明時,讓長福給送了鴆酒。”
褚曣的聲音愈發無力,魏姩沉浸在極大的震撼中,并沒有察覺。
“可惜,夢境太模糊,孤不知是誰,殺的又是誰。”
魏姩垂在膝上的那只手攥著擺,神復雜的抬頭看向儲曣。
原來,他那夜竟查過那樁案子。
哪怕是為了齊云涵,也是激的。
“魏姩。”
褚曣突然睜開眼,第一次喚了的名字。
魏姩渾一,無措的看著他。
他知道是了?!
“你是不是覺得,孤還沒死,就萬事大吉啊?”褚曣半瞇著眼,聲音里的虛弱已清晰可聞。
魏姩了,愣了好一會兒,腦子才轉過彎來。
這才后知后覺,著急忙慌道:“殿下傷了!”
褚曣覷一眼,冷哼了聲:“得虧你還能發現啊。”
魏姩臉一紅,心中愧疚愈深。
“腰間有藥,旁邊有河。”
褚曣撂下這句后,就不管不顧的昏睡了過去。
魏姩嚇的紅了眼:“殿下!殿下!”
喚了幾聲,人沒有任何反應。
魏姩強行鎮定下來,才開始四張。
果然,不遠便有河流。
抹了把淚,踉蹌著站起。
雖不會理傷口,但卻也知曉個大概,四尋一圈,沒有找到盛水的,便看到不遠有一叢竹子。
魏姩從腰間出褚曣送給的那把匕首走了過去。
果然如褚曣所說,此極其鋒利,功的做了幾個裝水的竹筒。
打完水回到樹下,魏姩從不省人事的太子上出了一瓶藥后,一時有些手足無措。
他沒說他傷在哪兒...
又是墨裳也看不大出來,破損的地方也到都是。
魏姩簡單的掙扎后,抖著手向那墨金腰封。
只能他的裳自己找了。
小半刻后,魏姩的面無比凝重。
不是為他上新添的傷口,還有那幾道印記很深的疤。
有一道就在心臟旁邊,可想而知當時是怎樣的兇險。
是四年前在戰場上留下的,還是這些年被不間斷追殺傷的。
魏姩下心中酸,將帕子打輕的給他拭傷口。
沒理過傷,做起來有些笨拙,但他上傷口太多,到后面也就愈發得心應手了。
好不容易上完藥,卻沒有能包扎的細布,魏姩躊躇片刻后,咬咬牙走到樹后解下腰帶,將自己的里取出,撕一些碎片,給他包扎。
做完這一切,魏姩的視線落在他的上,上傷那樣,上應該好不到哪里去。
魏姩忍著臊意手,到一手膩,鮮紅的跡沾滿了指頭,眼神一變,飛快掀開墨擺,雖看不見,但能看到已經了一大片,腥味也愈來愈濃。
當即意識到,這恐怕才是他傷的最重的地方!
此時也就顧不得什麼男授不清了,魏姩趕灌了水回來,干脆利落的將太子下了個干凈,喔,倒也不是很干凈,留了。
果然,他大外側有很長一條口子,幾乎染紅了整條。
魏姩白著一張臉專注的清洗完傷口,上了藥用方才剩下的里碎片替他包扎好后,就用外裳將蓋住。
被浸的濡的下是沒辦法再穿了,魏姩便將其拿到河邊洗凈,又撿了些干柴,用方才從褚曣上搜下來的火折子生了火,烤干裳。
猜你喜歡
-
完結205 章

香妻如玉
凝香從冇想過自己會嫁給一個老男人。可她偏偏嫁了。嫁就嫁了吧,又偏偏遇上個俏郎君,凝香受不住俏郎君的引誘,於是甩了家裡的老男人,跟著俏郎君跑了。不料卻被老男人給抓了個現行!“你殺了我們吧!”凝香撲倒郎君身上,勇敢的望著老男人。老男人冇殺她,給了她一張和離書。然後,然後就悲劇了....俏郎君負心薄倖,主母欺辱,姨娘使壞,兜兜轉轉的一圈,凝香才發現,還是原來那個老男人好。突然有一天,凝香睜開眼睛,竟然回到了和老男人剛成親的時候。可這一切,還能重來嗎?--情節虛構,請勿模仿
42.4萬字8 11515 -
完結591 章

帶著千億物資穿成大奸臣的炮灰前妻
穿成大反派的作死前妻,應該刻薄親生兒女,孩子養成小反派,遭到大小反派的瘋狂報復,死后尸體都被扔去喂狼。 看到這劇情走向,俞妙云撂挑子不干了,她要自己獨美,和離! 手握千億物資空間,努力發家致富,只是看著這日益見大的肚子,俞妙云懵了,什麼時候懷上的? 不僅如此,大反派體貼化身寵妻狂魔,小反派乖巧懂事上進…… 這劇情人設怎麼不一樣?
103.7萬字8 99967 -
完結19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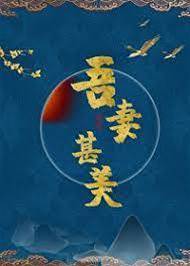
吾妻甚美
昭虞是揚州風月樓養的瘦馬,才色雙絕。 誰知賣身當天風月樓被抄了個乾淨,她無處可去,被抄家的江大人收留。 江大人一夜唐突後:我納你進門。 昭虞搖頭,納則爲妾,正頭夫人一個不高興就能把她賣了,她剛出泥沼,小命兒得握在自己手裏。 昭虞:外室行嗎? 江大人:不行,外室爲偷,我丟不起這個人,許你正室。 昭虞不信這話,況且她隨江硯白回京是有事要做,沒必要與他一輩子綁在一起。 昭虞:只做外室,不行大人就走吧,我再找下家。 江大人:…… 後來,全京城都知道江家四郎養了個外室,那外室竟還出身花樓。 衆人譁然,不信矜貴清雅的江四郎會做出這等事,定是那外室使了手段! 忍不住去找江四郎的母親——當朝長公主求證。 長公主嗤笑:兒子哄媳婦的手段罷了,他們天造地設的一對,輪得到你們在這亂吠?
28.4萬字8 2325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