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春空》 第104頁
從這里,能清楚窺到那頭舊書肆門口的狀。
祝晚玉穿過熙攘的大街,拐了這條小巷。
知道俞安行在這里。
才走上一步,腳上干凈的繡鞋立馬便染上了一層厚厚的泥漿。
耳畔聞得一陣突然闖進來的細碎腳步聲,俞安行側臉過去。
他面上神無波無瀾,眉尾揚起的弧度薄涼。
兩人視線對上,教祝晚玉的頭皮無端發麻。
停在原地,不敢再往前一步。
醞釀了許久的、有竹的話卡在了嗓子口。
祝晚玉憋了半晌,才用哆嗦的音調斷斷續續說了出來。
俞安行向來沒什麼耐。
早在祝晚玉開口說出第一個字時,大手便徑直握上的脖頸。
祝晚玉能清楚到間的氣息一寸一寸被出,面漲紅一片,眼球幾凸起。
俞安行向祝晚玉的眼眸中了無緒。
如同在看著一只無足輕重的螻蟻。
卻又在聽到說的某一句話時,作一頓,繼而緩緩收了手上的力道。
良久。
俞安行瞇起眸子,散漫一笑。
Advertisement
他問祝晚玉。
“你什麼名字?”
青梨走進書肆,抬眼環顧了一下四周。
發現鋪子里的東西已幾搬空,只余幾座零星擺放著幾本書冊的書架立在一旁,顧客寥寥,繞了幾圈也見不到多個人。
聽小魚道明來意,在柜臺前候著的小二往二樓的方向比了比手:“我家掌柜的眼下就在樓上,姑娘請跟小的過來。”
一路將青梨和小魚引至了二樓去見掌柜的。
小心關上門,小二又遵著掌柜的吩咐,下樓泡茶去了。
待到新茶烹好,再回到樓上時,余瞥見二樓過道上不知何時多出了一位年輕郎君。
郎君斜斜倚在廊邊,容貌清雋矜貴。
上一襲純白的狐大氅,過分純潔的,點亮了這一方灰暗簡陋的舊書肆。
許是新進來的客人?
小二被郎君上的風采迷了眼,忍不住多看了幾眼。
直至被茶壺燙到了手,才回過神來,小心翼翼地端著熱茶,躬進屋里去招待掌柜今日的貴客了。
青梨和掌柜的談得很順利,當即便將定金給付了。
仔細算算,將之前的舊鋪子理好,最遲到來年,新鋪子也就能開張了。
新鋪子的事計劃了許久,眼下終于也算是有了著落。
又再細細將其中的事項一一商討敲定好,掌柜將手上的算盤放好,起將青梨送至門外。
小魚上前攙過青梨走出房間,低聲道。
“姑娘……我們好像離開得有點太久了,若是世子爺和元護衛買好了糕點,回來時沒看到我們該怎麼辦?”
青梨聞言,探頭看了一眼天,估著已近午時,確實是耽擱得有點久了。
“沒事,我們現在照著原路走回去,到時便說迷了路,一不小心就走遠了。”
反正,無論說什麼,俞安行總是會相信的。
帷帽遮擋住視線,青梨并未瞧見后墻角那抹悉的頎長形,只往前走著。
風將漫不經心的嗓音送至耳中。
聽不出半點對他的在意。
俞安行維持著靠在墻邊的姿勢。
一不,像是玉雕琢而的一尊塑像。
從窗邊進來的日落在他冷峭的肩上。
墻上落下他一個人的影子。
孤零零的,疏離又清冷。
半邊面龐被昏暗籠罩。
教人窺不清楚他面上的神。
在天機閣時,殺完了人,他也常常這樣。
抬頭看著頭頂天窗滲進來的微薄線。
什麼都不想。
他知曉青梨對著他時的一切,不過都是虛假意。
一聲又一聲乖巧依賴的兄長,全都藏著的手段與算計。
但還是第一次聽到親口說了出來。
莫名其妙的,心上被陌生的愫裹挾住了,一點一點往下墜。
俞安行想,他可能有一點難。
手上著贈的薔薇花。
上面的每一道紋路他都記得清清楚楚。
從前他只當這式樣的絡子只他一人才有,便刻意忽略了隨意敷衍的手法。
眼下仔仔細細地瞧了,才發覺這絡子不個樣子,是出來的線頭就有四五。
中間的花蕊是一個半圓的形狀。
有那麼一點像彎對他笑的模樣。
俞安行也跟著彎起了角。
眼底和的眼波恍若春初剛破冰的湖水,漣漪清淺。
他側眸,目盯著青梨款款的背影。
沒關系的。
他會讓心甘愿地籠。
手上的力度輕。
薔薇花重新回到了男人腰間。
要下臺階了,青梨低頭仔細看著腳下,莫名察覺到一道落在背后的視線。
黏膩、。
像是蜘蛛網一般將包裹其中。
心口發。
青梨轉過去。
帷帽隨風而,出一點致的下頜廓。
果然看到了后不遠正站著一個男子。
——是曾在家宴上有過一面之緣的蘇見山。
猜你喜歡
-
完結159 章

嫁給奸臣沖喜后
傅瑤要嫁的是個性情陰鷙的病秧子,喜怒無常,手上沾了不知多少人的血。賜婚旨意下來后,不少人幸災樂禍,等著看這京中頗負盛名的人間富貴花落入奸臣之手,被肆意摧折。母親長姐暗自垂淚,寬慰她暫且忍耐,等到謝遲去后,想如何便如何。傅瑤嘴角微翹,低眉順眼地應了聲,好。大婚那日,謝遲興致闌珊地掀開大紅的蓋頭,原本以為會看到張愁云慘淡的臉,結果卻對上一雙滿是笑意的杏眼。鳳冠霞帔的新嫁娘一點也不怕他,抬起柔弱無骨的手,輕輕地扯了扯他的衣袖,軟聲道:“夫君。”眾人道謝遲心狠手辣,把持朝局,有不臣之心,仿佛都忘了他曾...
46.3萬字8 58850 -
完結36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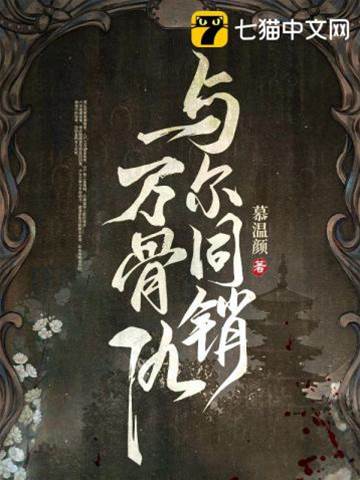
與爾同銷萬骨仇
深山荒野狐狸娶親,人屍之內竟是魚骨,女屍愛上盜墓賊,吊滿詭異人影的地宮...... 六宗詭譎命案,背後隱藏著更邪惡的陰謀。 少女天師與年輕尚書,循著陰陽異路解決命案,卻每每殊途同歸。 暗夜中的枯骨,你的悲鳴有人在聽。
32.6萬字8.18 8221 -
完結191 章

妾身嬌貴
莊綰一直以為,她會嫁給才華冠蓋京城的勤王與他琴瑟和鳴,為他生兒育女。然,一夕之間,她想嫁的這個男人害她家破人亡,救下她後,又把她送給人當妾。霍時玄,揚州首富之子,惹是生非,長歪了的紈絝,爛泥扶不上牆的阿鬥。初得美妾時,霍時玄把人往院裏一扔讓她自生自滅。後來,情根已深種,偏有人來搶,霍時玄把小美人往懷裏一摟,“送給爺的人,豈有還回去的道理!”
51.9萬字8.18 18298 -
完結347 章

囚她
施家二小姐出嫁一載,以七出之罪被夫家休妻,被婆婆請出家門。 無子;不事舅姑;口舌;妒忌。 娘家一席軟轎把她帶回。 她住回了自己曾經的閨房。 夜裏,她的噩夢又至。 那人大喇喇的端坐在她閨房裏,冷笑睨她。 好妹妹,出嫁一年,連自己娘家都忘了,真是好一個媳婦。 她跪在他身前,眼眶皆紅。 他道:“不是想要活着麼?來求我?” “你只許對我笑,對我體貼,對我賣弄,對我用十分心計,藉由我拿到好處。”
56萬字8.18 325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