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江花月》 第 101 章 第 101 章
陸煥之終于回過了神。臉一變,猛地拔出腰間佩劍,朝著李協刺了過去。
李協閃避。他立刻奪門而出,卻被李穆一腳給絆倒了。
“啪”的一聲,整個人重重摔到了門檻之上,鼻梁磕,頓時冒了出來。
伎紛紛驚。
李協朝子們示意,命人都出去。
眾知今晚是攤上事兒了。
門外突然冒出來的這兩個男子,顯然都不是一般人。尤其那個神沉的,另個人喚他“李刺史”。
難道便是那個剛回建康不久的李穆?
眾怎敢再多停留。避著地上一時還爬不起來的陸煥之,慌忙相繼出去。
綠娘最后一個,提著,從李協邊走過。
李協沉著臉,下令道:“那人方才全是污蔑。你的人點。不該說的,不要說!日后若是我聽到半個字的風聲,你這里也不用營生了。”
綠娘停步,起先不語,忽抬手,拔下簪在發間的一枝新鮮仙花,蔻丹纖指送著,慢慢地到了他襟上,盯著他,雙目宛若秋波漣滟,啟齒一笑,面綻春花,耳語般地低聲道:“郎若是信不過我,日后常來這里,自己多盯著些,豈不是更放心?”
李協一愣,反應了過來,看著扭飄然而去的背影,不有點尷尬,忙扯下前的仙,轉頭,卻見陸柬之的那個隨從還張著在看著自己,突然回過神,轉似要跳窗逃跑,低低地罵了一聲,上去一把制住,拎了出去,關上了門。
李穆蹲到陸煥之的頭旁,手探他懷里,將那冊琴譜取出,翻了一翻。
他看過神的字。
一眼便認了出來,琴譜確實是出自手。
視線落到尾頁一角所留的那日期,他渾的,仿佛一下凝固住了。
Advertisement
他盯著那道墨跡,看了片刻,視線慢慢轉向還倒在地上的陸煥之,指著被撕去扉頁后留下的那道紙張殘頁:“這一頁呢?”
他的聲音聽起來依然平靜,眸底,卻已是開始暗波逐涌。
陸煥之睜開眼睛,
“姓李的,你想知道?我偏不告訴你!”
“你別以為那日在街上幫你說話,就是心里真的有你!你算個什麼東西?一個寒門出的武人,連替提鞋都不配!你名為丈夫,想必平日在面前,也是如犬般搖尾乞憐,唯恐看不上你,是不是?”
“我和從小就認識。打小心地就最是了,見不得人在面前扮憐,連看到個乞丐也要給碗飯吃。似你這般向搖尾,莫說你是個大活人,你便是條狗,也會對你好的!不過是見你當街被我辱,可憐你,才開口替你解的圍!”
“可惜啊,不止我一人,滿大街的人都聽到了,看似在替你說話,心里想的卻還是我大兄!當著滿街之人,褒揚我大兄人品!”
“是,我陸煥之是無品無德,豬狗不如,我被罵,我心甘愿。可是你呢,你當初用計將從我大兄邊奪走,名義上是丈夫,人都嫁你了,這麼久了,卻還是對我大兄念念不忘。”
“李穆,你可真是可憐哪!”
他的不住地一張一合。從鼻孔里冒出來,一道道地蔓延開來,漸漸布滿了兩側的面頰,又流進了他的里,他也不去拭,模樣瞧著有點滲人。
“我再問你一遍,扉頁在哪里?”
李穆恍若未聞,面無表,又問了一遍。
“你既然人跟著我了,想必方才早也到了,聽到了我的話。這可是阿彌去年三月送我大兄的琴譜,曲名就鸞鳴。”
他神經質般地呵呵笑了起來。
“不妨告訴你吧,扉頁就是被我撕下的。至于上頭,都和我大兄說了什麼,我偏不告訴你!”
李穆五指驀然收,骨節發出一道清脆的格格之聲。蚓般的縱橫青筋,瞬間暴布手背。
他張手,一把便抓住陸煥之的襟,竟將他整個人從地上提了起來,擲了出去。
陸煥之人雖瘦,但也是個年男子,整個人卻似一只面袋般飛了出去,“砰”的一聲,重重地撞到對面的墻上,又彈落在下頭的那張琴案之上,在琴弦斷裂發出的一道雜無章的嗡嗡聲中,人帶著整張琴案,翻滾在地。
他撞到了墻的那整面肋骨,已是齊齊斷裂。痛苦地攏著雙臂,整個人的蜷了一團,在墻角掙扎著。
“……阿彌和我大兄投意合,你卻奪人所,你憑了什麼?原本如今,已是我阿嫂了……”
他猶在,聲音斷斷續續。
“和我大兄,才是天生的一對,當年曲水流觴,簫琴相合,誰不知道……你以為就只給我大兄譜過如今這麼一支琴曲?從前就和我大兄用琴譜往來,互訴心意。的人是我大兄……不過是可憐你……”
李穆大步而來。
一只劍柄,猛地擊在了他的腦袋上。
伴著一道慘之聲。
人那堅的頭骨,在這劍柄之下,猶如一只脆弱的蛋殼,瞬間應力而裂。
從陸煥之的頭上汩汩而下,宛若溪流,瞬間染滿了他的整張臉。
他的人蜷一團,四肢搐著,仿佛下一刻就要死過去了,卻還在微微地張翕著。
“你等著……等我大兄這回攻下了東都……阿彌還不知會如何高興……”
氣若游般的最后一道聲音,也戛然而止了。
李穆掐住了他的脖頸,一手將他整個人高高舉起,懸空地釘在了后的那堵墻上。
在他這只曾染過無數人的鐵鉗般的指掌之下,陸煥之的脖頸,脆弱得猶如一秋天行將腐爛的蘆葦,一折便斷。
一團一團地從陸煥之的鼻孔和角里涌出。但那張分明布滿了痛楚的臉上,卻仿佛還殘留著方才糅雜著恨意和猶如報復得逞似的近乎暢快的詭異表。
他被掐住,無法呼吸,翻著白眼,無力地在空中蹬著兩。
李穆看著在自己五指之下,徒然扭著,沒有半點反抗之力的陸煥之,視線最后定在他那張扭曲得幾乎已經認不出原本面目的臉上,看了片刻,凝聚于他眼底的仿似下一刻便要發而出的暴風驟雨、海嘯山洪,慢慢地消失了。
取而代之,在他的眸底,忽地掠過一縷蕭瑟。
緩緩地,他手背之上那原本縱橫暴布著的一片青筋,亦是平復了下去。
他突然松開了自己鉗住陸煥之嚨的那只手,轉而去,再沒有看他一眼。
陸煥之從墻上掉落在地,仿佛被去了脊梁,趴在那里,一不。
李協方才吩咐好了綠娘,命手下將樓里的人全部驅走,閉了大門,自己便守在這門外。
雖隔著門,他也能想象里頭正在發生著什麼。
起先還能聽到陸煥之傳出的話語之聲和慘之聲。漸漸地,里頭安靜了下來,也聽不到他發出的任何靜了,不起了擔心。m.166xs.cc
萬一李穆一時緒失控,若真將他給弄死了,畢竟此是建康,又是個大活人,且還是陸家的,恐怕會有一場司。正要推門進去阻止,卻見門自己先開了,李穆出現在了面前。
他的臉看起來并不怎麼好,但還算是平靜。
李協又瞥了眼地上的陸煥之,見他滿頭污,面目可怖,一不,匆忙走了過去,手探了探鼻息,發覺還活著,只是昏死了過去,松了口氣,笑著走了回來,低聲道:“李將軍放心去吧,我會替你再盯著這小崽子的。干出這樣的事,他自己必也不敢在陸跟前全部認下。陸家若是找你的事,方才我也吩咐好了那子,就說是他來此鬧事在先,險些出人命,刺史恰好路過,路見不平,出手教訓了一下而已。”
李穆道:“多謝兄弟。回頭我做東,請眾位兄弟吃酒。”
李協唉了一聲,急忙擺手:“李將軍怎說這話?當初若不是李將軍,莫說有我和那幫子兄弟今日,指不定連命都已經沒了。我等兄弟,對李將軍敬佩得是五投地。不過是舉手之勞罷了。往后但凡還有用的著我兄弟的地方,只管開口,便是掉腦袋的事,你瞧我會不會皺一下眉!”
李穆又叮囑,他看著些這里,莫惹來陸煥之日后報復。
李協眼前便浮現過方才那子朝自己襟簪花的一幕,咳嗽了聲,點頭:“不消你說,我亦知道。”
李穆微微一笑,向他作了個揖,旋即邁步而去,從后門而出,影消失在了夜里。
……
為了方便與父母相,回來后,兩人一直還住在高家。
李穆回到高府,已是戌時中。不等他下馬,早有門口的下人出來迎接,爭相向他問好,替他牽馬廄。
李穆,遇到了阿。問了聲,知高嶠今日回來得早些,伴著長公主,此刻兩人已經回屋了。
“夫人也在房里了。李郎君晚飯可吃過了?夫人本想等你一道吃的,沒等到你回,自己便先吃了,吩咐給你留飯。”阿又說道。
李穆說在外頭已是吃了,不必費心,如常那樣,臉上帶著笑容,繼續朝里而去。
越近那個院落,腳步便越來越慢。
院門是開著的。
他知是為自己而留的。
院中線昏暗,屋子的窗里,映著一片明亮的燈火。
廊下等候著的幾個仆婦侍正在低聲地嘮著閑話,忽然聽到后腳步發出的靜,轉頭見是他回了,忙來迎,道夫人正在屋中沐浴。
李穆穿過蕉影婆娑的院落,步上檐階,來到出亮的門前,定了定神,輕輕推門而。
外屋空無一人。一道垂下的帳簾,將外分隔了開來。
水聲中,李穆聽到了低低地哼著小調的愉快嗓音,清囀,百千。
溫水洗脂,滴妍姿俏。
閉著眼眸,他都能想象,此刻里頭是何等一番人的景象。
他只要手,開面前這道輕如云的帳簾,走到的面前,便能開口問了。
那只手,卻猶如灌滿了鉛,重得無法舉起。
懷中那本薄薄的,不過十來頁的冊子,仿佛一團火,被他揣了膛,在漸漸地升溫。
灼燙之,從某個平日藏起來的不為人知,或許連他自己亦是未能察覺的角落,不停地蔓延,刺灼著他的四肢百骸,遍布全,直到每一寸的。
他到心浮氣躁,再也無法維持住方才在下人面前的從容了,臉漸漸變得僵。
那日他接出宮,路上遇到了陸煥之的挑釁,為自己解圍,陸煥之憤而離開之時,將滿腔怒氣都撒在了下的坐騎之上。
那一幕,李穆心生警惕。
陸煥之不過是個無能之人,上輩子如此,這輩子亦是如此。
但再無能的人,手中一旦舉刀,亦能殺人。
他的,便曾被陸煥之用劍刺穿過。
出于直覺,亦是為了對的保護,哪怕只是多心。在送回來后,他便去尋了李協,這個當日曾被興平帝派來助他去打郡的下屬,如今掌著都衛,耳目遍布四城,他派人留意陸煥之的異常舉。
果然被他猜中了。
如此之快,陸煥之便就開始了他的報復。
但李穆無論如何也猜不到的是,他的報復,竟是如此一種手段。
李穆到了一后怕。
并不是為自己可能面臨的聲名損,而是為。
倘若不是李協第一時間通知了自己,他及時趕到,截了下來。倘若琴譜真的就此傳了開來,伴著高氏千里相思寄郎的傳言,他無法想象,將要面對怎樣的一番景。
幸而,一切都未發生。
原本他該為之到慶幸。
猜你喜歡
-
完結644 章

獸黑狂妃:皇叔纏上癮
“本王救了你,你以身相許如何?”初見,權傾朝野的冰山皇叔嗓音低沉,充滿魅惑。 夜摘星,二十一世紀古靈世家傳人,她是枯骨生肉的最強神醫,亦是令人聞風喪膽的全能傭兵女王。素手攬月摘星辰,殺遍世間作惡人。 一朝穿越,竟成了將軍府人人可欺的草包四小姐,從小靈根被挖,一臉胎記丑得深入人心。 沒關系,她妙手去胎記續靈根,打臉渣男白蓮花,煉丹馭獸,陣法煉器,符箓傀儡,無所不能,驚艷天下。 他是權勢滔天的異姓王,身份成謎,強大逆天,生人勿近,唯獨對她,寵之入骨,愛之如命。
116.9萬字7.5 400695 -
完結169 章

暴君的寵后[重生]
傳言北戰王性情暴戾,喜怒無常,死在他手裡的人不知凡幾。前世安長卿聽信傳言,對他又畏又懼,從不敢直視一眼。 直到死後他才知道,那個暴戾的男人將滿腔溫柔都給了他。 重生到新婚之夜,安長卿看著眉眼間都寫著凶狠的男人,主動吻上他的唇。 男人眉目陰沉,審視的捏著他的下巴,“你不怕我?” 安長卿攀著男人的脖頸笑的又軟又甜,“我不怕你,我只怕疼。” 而面前的男人,從來不捨得讓他疼。 —————— 最近鄴京最熱鬧的事,莫過於北戰王拒絕了太后的指婚,自己挑了丞相府一個不受寵的庶子當王妃。 眾人都說那庶子生的好看,可惜命不好被北戰王看上了,怕是活不過新婚之夜。 所有人都等著看北戰王府的笑話。 可是等啊等啊……一直等到北戰王登基稱帝,等到庶子封了男後獨占帝王恩寵,等到他們只能五體投地高呼“帝后千秋”,也沒能等到想看的笑話。
50.7萬字8 38486 -
完結25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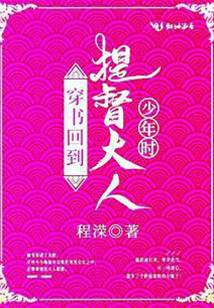
穿書回到提督大人少年時
她書穿成了女配,可憐兮兮地混在公堂的男男女女中,正等著知縣大人配婚。 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使長吏配之。 按照劇情她注定是炮灰,超短命的那種。 她不認命,急切的視線在人堆裡可勁兒地扒拉,終於挖掘出他。 夭壽呦,感情這小哥哥,竟是男二! 連女主都無法覬覦的狠人! 這位爺有秀才功名在身,卻被至親算計,入宮成為殘缺不完整的太監。 他生生地熬過種種苦難,任御馬監掌印太監,最後成了人人敬畏的提督大人。 他曾顛沛流離,人人嫌惡,也曾位高權重,人人討好。 成為看盡人生百態,孑然一生的權宦。 但這都不是重點,重點是他壽終正寢! 只要她抱緊他的大腿兒,定能擺脫螞蝗般的至親,待日後做了大宦官之妻,更是吃香的喝辣的,還不用費勁巴拉的相夫教子。 小日子簡直不要太美好,撿大漏啊! 他一朝重生,再回少年時,尚未入宮,更未淨身。 眼下,他還是小三元的窮秀才,父暴斃而亡,母攜家資再嫁。 他浴血歸來,渾身戾氣,可一時善心,就多了個嬌嬌軟軟的小娘子! 說啥他這輩子也不淨身了,好好地考科舉,走舉業,給她掙個誥命夫人做,再生幾個小崽子玩玩兒……
44.7萬字8 23041 -
完結794 章
盛寵天下:不良醫妃要休夫
大婚之日,軟弱的草包嫡女雲安安被庶妹陷害與他人有染,渣男將軍更是將她打到死,並且休書一封將其掃地出門。 鳳眸重視人間之時,二十一世紀賞金獵人雲安安重生,洗盡鉛華綻,瀲灩天下。 “小哥哥,結婚麼,我請。” 雲安安攔路劫婚,搖身一變從將軍下堂妻成為北辰國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攝政王寵妃。 世人都說攝政王的寵妃是個不知檢點的草包廢物,可一手銀針起死人肉白骨,經商道成為天下首富,拳打皇室太子腳踏武林至尊又是誰? “王爺...... 王妃說她想要當皇帝。 “ 北辰逸眼神微抬,看著龍椅上的帝王說道”你退位,從今日起,本王的夫人為天。 ”
155.3萬字8 14973 -
完結135 章

偏執帝王掌心囚:千金為奴恕不從
【隱忍堅毅侯府假千金*狠厲偏執竹馬渣帝】身為濮陽侯府嫡女,宋玖兒享盡榮光,可一朝身世揭露,她竟是冒牌貨!真千金入府,爹娘棄她、世家恥笑,而深愛的未婚夫蕭煜珩,卻疏離避著自己。哀莫心死,宋玖兒嫁與清貧書生,可未曾料到,雨催風急的夜,房門被踹開。新帝蕭煜珩目光沉沉,陰鷙抬起她的下頜:“朕允你嫁人了嗎?”她被虜入宮中做賤婢,受盡磨難假死出宮卻發現有喜。幾年後,聽聞帝立一空塚為後。小女兒杏眸懵懂,“娘親,皇上真是深情。”宋玖兒微微展眉,“與你我無關。”蕭煜珩曆盡萬難尋得那一大一小的身影,赫然紅了眸:“你是我的妻!”
21.3萬字8.18 781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