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妃撩人:王爺請接招》 第四百零五章:別入戲太深
晏以淵拿著一塊過水的金手帕,低頭為霍兮容拭腳底染上的灰塵,上說起來十分嫌棄,但作上卻不見任何芥。
“你剛剛腳站在地上,腳底上沾的灰也不說,轉頭就鉆進了被窩里,真虧你也不嫌臟。”晏以淵上還吐槽著,只是手下的作卻異樣的溫。
霍兮容有些不習慣的想要收回自己的腳,只是晏以淵卻不愿放開。
一個子,別的男人為自己腳,這未免也太顯親近了......
難得霍兮容收起了自己的利爪,臉上有些尷尬,那塊黃布似乎是晏以淵用的東西吧,看上面的繡工十分,為自己腳也太奢華了。
而且霍兮容不認為,自己過腳的手帕晏以淵會宮娥們清洗清洗,繼續手、臉用。
“就算臣妾腳底上有灰,都過這麼久了,那些浮塵也早就在被褥上蹭干凈。皇上這個時候才來獻殷勤,您老人家不覺得晚了嗎?”不管心里尷不尷尬,至霍兮容這張是絕不饒人。
Advertisement
晏以淵人的手段高明啊,這要是換其他子還不被晏以淵迷得神魂顛倒。
霍兮容心中暗嘆,還好自己清楚,晏以淵對自己的好只是因為看中了自己的命格而已,否則就憑晏以淵的人功力,還真的會誤會這個男人是不是也喜歡上自己了呢。
“朕比你大不了幾歲,妃一口一個老人家的著,你覺得合適嗎?”晏以淵把干凈的兩只腳全部放回被褥里,同時還很心的為霍兮容掖了掖被角。
“皇上,過過戲癮也就算了,你可別戲太深,演戲演得久了,就分不清什麼是戲里,什麼是戲外了。”霍兮容瞇著眼睛,意有所指的提點了一句。
不可否認,如今晏以淵的舉已經霍兮容有些心了,這男人到底哪一面是真的,哪一面是假的,有些看不。
“戲深淺不重要,只要唱戲的人能一直陪在朕旁,就算把這一出戲唱演一輩子那又如何。”晏以淵重新從袖中掏出一塊干凈的帕巾,慢條斯理的拭著自己的手指。
“哦?皇上認為這出戲能唱到一輩子之久?”霍兮容嗤笑一聲,在笑晏以淵的癡心妄想。
就算沒有璟王的搗,與晏以淵此生注定無緣無份,甚至可以說若不是因為璟王,與皇上本連面都不會見。
一輩子?
呵,霍兮容都不知道,晏以淵是哪里來的勇氣能說出這句話來。
“妃之所以認為自己不可能永遠在宮中陪著朕,那是因為你心里還記得自己是璟王妃。若是朕當著全天下百姓的面,做實了你皇后的位置,你會如何?”晏以淵盯著霍兮容的雙眸,淡笑著問道。
晏以淵可永遠記著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道理。
“皇上這如意算盤打的,臣妾倒是看不懂了,似乎公開臣妾的容貌對皇上而言并無什麼益才對。”霍兮容最厭惡的就是晏以淵這副凡事都運籌帷幄的模樣,這事是個賭局,輸贏全看天意。
霍兮容不知道,這個男人憑什麼認為自己一定會贏。
人心是最難掌控的東西,也許今日還對你恩戴德,搞不好明天轉就會把你給出賣了。
晏以淵憑什麼認為,憑他一己之力就能把千萬百姓的忠心玩弄于掌之上?
晏以淵起,整理著自己的衫,沒有毫避諱的對霍兮容說:“妃的容貌怎麼了?澤,目勾人,小臉潔無瑕,雖說依妃的容貌當不起第一人的贊譽,可朕能看上眼的子,容貌又能差到哪里去?”
“還真是謝皇上如此瞧得起臣妾。”霍兮容冷笑一聲,聽晏以淵的話音,這人似乎是打算拿之前臉上的假疤做文章。
“不,只能說妃實在太勾人,就連朕也自愿為妃的護花之人。”晏以淵謙虛的笑了笑,如今只要等霍兮容把子養好,好戲才能真正開場。
所有的配角都已準備好,這個戲臺其一是為了引出一直觀戲的老虎,其次是為了抹殺掉璟王妃這個人。
從此之后,世間再無霍兮容,霍家唯一活下來的只有霍自若!
“皇上,你覺得兮容有沒有魄力,敢來一個弄假真?”霍兮容笑的面若桃花,只是眼中的狠絕人不敢小小覷。
霍兮容唯恐晏以淵聽不懂自己暗示一般,還特別‘好心’的用芊指特意點了點自己的臉頰。
猜你喜歡
-
完結159 章

嫁給奸臣沖喜后
傅瑤要嫁的是個性情陰鷙的病秧子,喜怒無常,手上沾了不知多少人的血。賜婚旨意下來后,不少人幸災樂禍,等著看這京中頗負盛名的人間富貴花落入奸臣之手,被肆意摧折。母親長姐暗自垂淚,寬慰她暫且忍耐,等到謝遲去后,想如何便如何。傅瑤嘴角微翹,低眉順眼地應了聲,好。大婚那日,謝遲興致闌珊地掀開大紅的蓋頭,原本以為會看到張愁云慘淡的臉,結果卻對上一雙滿是笑意的杏眼。鳳冠霞帔的新嫁娘一點也不怕他,抬起柔弱無骨的手,輕輕地扯了扯他的衣袖,軟聲道:“夫君。”眾人道謝遲心狠手辣,把持朝局,有不臣之心,仿佛都忘了他曾...
46.3萬字8 58850 -
完結36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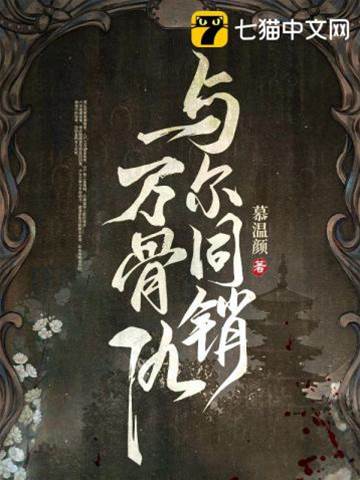
與爾同銷萬骨仇
深山荒野狐狸娶親,人屍之內竟是魚骨,女屍愛上盜墓賊,吊滿詭異人影的地宮...... 六宗詭譎命案,背後隱藏著更邪惡的陰謀。 少女天師與年輕尚書,循著陰陽異路解決命案,卻每每殊途同歸。 暗夜中的枯骨,你的悲鳴有人在聽。
32.6萬字8.18 8221 -
完結191 章

妾身嬌貴
莊綰一直以為,她會嫁給才華冠蓋京城的勤王與他琴瑟和鳴,為他生兒育女。然,一夕之間,她想嫁的這個男人害她家破人亡,救下她後,又把她送給人當妾。霍時玄,揚州首富之子,惹是生非,長歪了的紈絝,爛泥扶不上牆的阿鬥。初得美妾時,霍時玄把人往院裏一扔讓她自生自滅。後來,情根已深種,偏有人來搶,霍時玄把小美人往懷裏一摟,“送給爺的人,豈有還回去的道理!”
51.9萬字8.18 18298 -
完結347 章

囚她
施家二小姐出嫁一載,以七出之罪被夫家休妻,被婆婆請出家門。 無子;不事舅姑;口舌;妒忌。 娘家一席軟轎把她帶回。 她住回了自己曾經的閨房。 夜裏,她的噩夢又至。 那人大喇喇的端坐在她閨房裏,冷笑睨她。 好妹妹,出嫁一年,連自己娘家都忘了,真是好一個媳婦。 她跪在他身前,眼眶皆紅。 他道:“不是想要活着麼?來求我?” “你只許對我笑,對我體貼,對我賣弄,對我用十分心計,藉由我拿到好處。”
56萬字8.18 325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