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醫香之嫡女不下嫁》 第六章 栽贓陷害
厚重的大門再次被推開,四兒媳四兒媳雅芙從里面慌慌張張地跑了出來。
“清遙啊,你是清遙吧?”四兒媳雅芙靠近到范清遙的邊,低聲音問著。
范清遙點了點頭。
四兒媳雅芙的眼淚猛地就流了下來,“這孩子可是凍壞了?我是你四舅娘,你,你和你娘怎麼落得這般地步了?”
四兒媳雅芙的心疼是真的,愧疚也是真的,這可憐的孩子究竟是遭了什麼罪,才落得這般狼狽?
“我這里有些銀子,你先帶著你娘去旁邊的酒家吃些東西,暖和暖和子,等晚上們都睡下了,我再帶著你跟你娘回府。”四兒媳雅芙從袖子里掏出了一些碎銀子塞給了范清遙,卻不敢看范清遙的眼睛。
范清遙小小地手攥著銀子,看著四兒媳雅芙鄭重其事地道,“謝謝四舅娘。”
這一聲四舅娘,的四兒媳雅芙渾一,眼中的愧疚更濃。
“你這傻孩子,跟四舅娘客氣什麼?趕去吧,去吧……”四兒媳雅芙又從懷里掏出了一袋碎銀子,悄悄塞進了范清遙的袖子里,這才憐地抬起手,了范清遙那早已被雪覆了白的發頂。
Advertisement
范清遙點了點頭,拿著銀子推著吱嘎作響的板車走了。
那小小的影漸漸消失在街道的巷子里,四兒媳雅芙的臉上卻生出了濃濃的愧疚之。
與此同時,后的大門被徹底推開,已梳洗打扮過的其他幾個兒媳相續邁出了門檻。
大兒媳大兒媳凌娓冷冷地啐了一口,“不但連自己的男人都看不住,就連生出來的孩子都是個傻的,三言兩語就被騙得團團轉。”
其他幾個媳婦兒均是沉默著不說話,剛剛在門口們看得清楚,那娘倆狼狽那般模樣,們是看著都覺心酸。
大兒媳大兒媳凌娓見沒人搭理自己,面上笑著又道,“這得說四弟妹演得好,眼淚說流就流,別說是那個小野種信以為真,就是我看了都險些沒的掉淚。”
四兒媳雅芙垂著眼,梗咽的聲音似譏諷又似討好,“哪里,這還不都是大嫂子的主意好。”
大兒媳大兒媳凌娓得意地挑了挑眉,“先別忙著好,好戲還在后面。”
花府的門口,大兒媳笑得一臉得意,其他的幾個兒媳無不是口如同堵了一塊巨石般得沉。
不多時,掛著花府牌子的馬車停在了門口。
面各異的幾個兒媳瞬間乖順地站一排,恭恭敬敬地彎膝行禮。
花耀庭當先走下馬車,年近六旬,卻異常朗,經過戰場洗禮的氣息莊重而冷峻,沉著而斂,是站在那里便不怒自威。
在花耀庭的親子攙扶下,陶玉賢也下了馬車,滿頭白發卻容煥發,面目慈又眼含凌厲。
“你們倒是勤快,連我和老爺提前回府都知道。”
面對陶玉賢的質疑,幾個兒媳婦垂低著頭不知該如何回答。
大兒媳大兒媳凌娓趕彎了下膝蓋,“回老夫人的話,剛剛我外出看見了一奇景,怕是看錯了,便是想讓其他弟妹們也過來看看,沒想回來的路上便是剛好遇見了老爺和老夫人。”
陶玉賢疑,“什麼奇景?”
大兒媳大兒媳凌娓故作善解人意的道,“我見長小姐和清遙小姐正在隔壁的吃呢。”
頃刻之間,花耀庭和陶玉賢的臉都是一沉。
花月憐當初因為丞相之子與花家翻臉,不曾想最后的一往深卻抵不過一個花樓的子,這些年,整個西涼都拿著此事當茶余飯后的消遣。
花家兩位當家也并非鐵石心腸,只是花月憐一直不肯低頭認錯,這事兒便就這麼僵著。
眼下,花月憐竟帶著范清遙跑到花府的附近大吃二喝,這不是明擺著在跟花府示威?
“既有本事,就永遠別進我花府的大門!”花耀庭怒斥一聲,扶著臉同樣不好看的陶玉賢大步上了臺階。
除了自導自演的大兒媳凌娓之外,其他的幾個媳婦兒無不是如鯁在。
現在們終于明白大兒媳凌娓說的好戲是什麼了。
被這麼一鬧,們那可憐的弟妹就別指再帶著清遙小姐踏花家的門檻!
忽一陣的寒風夾雜著雪花,從街道的一頭吹了過來。
春月被什麼東西糊在了臉上,正琢磨著哪里來的雪花竟有掌大,拿下一看險些沒嚇得暈過去。
這哪里是雪花?
這本是死人用的紙錢啊!
“吱嘎吱嘎……”
板車木碾過積雪的聲音由遠及近,站在花府門前的眾人循聲回頭,無不是被驚得狠狠一愣。
漫天紙錢紛飛之中,范清遙竟是推著那破舊的板車又回來了!
猜你喜歡
-
完結315 章
冷帝在上,傲嬌皇後求休戰
一朝穿越,冷羽翎隨還冇搞清楚狀況,就被成親了! 他是萬人之上的皇帝,高冷孤傲,“我們隻是假成親。” 成親後,冷羽翎感覺自己被深深的欺騙了! 為什麼這個皇帝不僅要進她的香閨,還要上她的床 這也就算了,誰能告訴她,為什麼他還要夜夜讓自己給他生娃呢!
53.9萬字8.8 66122 -
完結260 章

流放路上炮灰寡婦喜當娘
許柔兒萬萬沒想到,自己竟然穿成炮灰寡婦,開局差點死在流放路上!不僅如此,還拖著個柔弱到不能自理的嬌婆婆,和兩個刺頭崽崽。饑寒交迫,天災人禍,不是在送死就是在送死的路上。但許柔兒表示不慌。她手握空間富養全家,別人有的我們也有,別人沒有的我們更要有!“那為什麼我們沒有爹。”“爹?”許柔兒看著半路搶來的帥氣漢子,見色起意,一把薅來。“他就是你們的爹了!”帥男疑惑:“這可不興喜當爹。”“我都喜當娘了,你怕什麼喜當爹!”
47.3萬字8 29692 -
完結377 章

女主,你狐貍尾巴露了
養狐貍之前,裴鳴風每日擔憂皇兄何時害我,皇兄何處害我,皇兄如何害我?養了狐貍之后,裴鳴風每日心煩狐貍是不是被人欺負了,狐貍是不是受傷了,狐貍是不是要離開自己了。冀國中人人知宮中有個“狐貍精”,皇上甚為寵之,去哪帶哪從不離手。后來新帝登基,狐貍精失蹤了,新帝裴鳴風帶了個蕙質蘭心的皇后娘娘回來。
66.9萬字8 11395 -
完結11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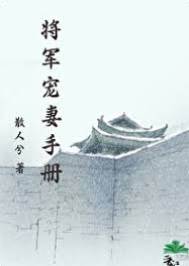
將軍寵妻手冊
雲府長女玉貌清姿,嬌美動人,春宴上一曲陽春白雪豔驚四座,名動京城。及笄之年,上門求娶的踏破了門檻。 可惜雲父眼高,通通婉拒。 衆人皆好奇究竟誰才能娶到這個玉人。 後來陽州大勝,洛家軍凱旋迴京那日,一道賜婚聖旨敲開雲府大門。 貌美如花的嬌娘子竟是要配傳聞中無心無情、滿手血污的冷面戰神。 全京譁然。 “洛少將軍雖戰無不勝,可不解風情,還常年征戰不歸家,嫁過去定是要守活寡。” “聽聞少將軍生得虎背熊腰異常兇狠,啼哭小兒見了都當場變乖,雲姑娘這般柔弱只怕是……嘖嘖。” “呵,再美有何用,嫁得不還是不如我們好。” “蹉跎一年,這京城第一美人的位子怕是就要換人了。” 雲父也拍腿懊悔不已。 若知如此,他就不該捨不得,早早應了章國公家的提親,哪至於讓愛女淪落至此。 盛和七年,京城裏有人失意,有人唏噓,還有人幸災樂禍等着看好戲。 直至翌年花燈節。 衆人再見那位小娘子,卻不是預料中的清瘦哀苦模樣。雖已爲人婦,卻半分美貌不減,妙姿豐腴,眉目如畫,像謫仙般美得脫俗,細看還多了些韻味。 再瞧那守在她身旁寸步不離的俊美年輕公子。 雖眉眼含霜,冷面不近人情,可處處將人護得仔細。怕她摔着,怕她碰着,又怕她無聊乏悶,惹得周旁陣陣豔羨。 衆人正問那公子是何人,只聽得美婦人低眉垂眼嬌嬌喊了聲:“夫君。”
17萬字8.33 5690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