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心》 第 21 節 夢里不見秋
娘帶著丫鬟急急迎出來,將狐裘裹在我上,滿目心疼地握住我冰涼的手。
又忍不住轉頭斥責:「到底是什麼要的話,非要站在院子里說?明知小笛子弱,就不能先進屋?」
崔寧枝張了張,還沒來得及出聲,崔寧遠已經將護在后,低頭認錯:
「是我的錯,沒考慮到姑娘的病。」
娘不滿地敲打他:「你與小笛已有婚約,說話何須這麼客氣?」
「親事未,禮不可廢。」他答得恭順。
事實上,在旁人面前,崔寧遠言行謹慎、時時守禮,幾乎挑不出什麼錯來。
只有和我單獨相時,他才會褪去眼睛里的偽裝,出毫不掩飾的冰冷疏離。
我也不知道怎麼想的,在侍衛來回稟,說崔寧遠又一次去醫館找唐時,坐著馬車跟了上去。
大雪連日,京中不人染了傷寒,唐醫館外排起長隊,等著問診拿藥。
我攏著斗篷走過去,正好瞧見崔寧遠一邊替抓藥,一邊側頭說著話:
「既然不能學堂讀書,我便隔一日來一趟,把先生講的講給你聽。」
聽他這麼說,唐笑得眼睛都彎起來,連連點頭,手下的作卻沒有毫延緩。
我沒有,只是沉默地著這一幕。
他收起了在我面前的疏離與厭煩,面對唐時,仿佛細致微,又萬千。
「既然如此……為何提到取消婚約,又不肯同意?」我下意識喃喃出聲,原也沒想過問誰。
然而耳畔忽然響起一道清越的嗓音,像是在回答我。
「那當然是為了利用你繼續在京城學堂讀書,最好再給他馬上要出閣的妹妹多撈點嫁妝。等明年科考一舉上位,親自告到皇上面前,再強行解除婚約也不遲嘛。」
Advertisement
猛然回頭,我在漫天大雪中,對上一雙亮若星辰的眼睛。
又是賀聞秋。
這人簡直神出鬼沒的。
腦中閃過這個念頭,不等我開口,距離我只有一步之遙的賀聞秋忽然邁步過來,微一側,恰好擋在我和藥鋪之間。
「低頭。」他低聲說,「別讓你那倒霉催的未婚夫看到你和我在一塊兒。」
5
這話說
得實在引人遐思,我有心想糾正,然而看到他一臉正氣,仿佛全然未察覺這話里的曖昧是多麼有失分寸。
我嘆了口氣,轉就走。
賀聞秋卻又追了上來。
「姜笛!」他這樣連名帶姓地我,「你生氣了?還是在傷心啊?」
我停住腳步,在愈發稠的漫天風雪里回頭,輕聲說:「我也不知道。」
應該是要難過的,心里好像被撒進去一把碎冰。
可尖銳的痛只是一閃而逝,很快就融化掉了。
我發現我的心,比想象中平靜許多。
只是愣神間,賀聞秋已經翻上馬,扯著韁繩來到我面前。
他微微彎,沖我出手:「上來,帶你騎馬散心,要不要?」
后綺月已經追上來,又急又氣地瞪他:
「登徒子!我家姑娘與你素不相識,怎麼可能隨隨便便與你同騎?」
賀聞秋不理會,只是專注地看著我,甚至把那只手又往前遞了遞。
他一貫懶散的眼神難得如此認真,我沉默了一下,還是把手過去。
他抓住我,用恰到好的力度往上拽。
我借著這力道轉過,沒怎麼費力,就落在了他前的馬背上。
綺月急得團團轉:「這麼大的風雪,姑娘子不好,怎麼得住!」
「無事。」我安,「你先帶人回府,留兩個人在此盯著便好。」
「那姑娘——」
賀聞秋截住的話:
「放心,我騎了得,怎麼把你家姑娘帶走的,定然會怎麼完好無損地送回府中。」
「好輕。」
賀聞秋的聲音很小,然而我與他之間,不過隔著一層兔滾邊斗篷,自然聽得清清楚楚,于是回頭了他一眼。
他卻一扯韁繩,一邊縱馬一邊開始念叨:
「你肯定沒好好吃飯。喝藥有什麼用啊,多吃兩口補充蛋白質,不比喝那些苦兮兮的中藥好多了。還有你早上喝那些清湯寡水的小米粥,就不能換牛和煎蛋……」
下駿馬疾馳,寒風卷著雪花撲面而來,正要咳嗽,一件斗篷已經落在了我前。
賀聞秋的聲音響起,卻不甚清晰:「抓好了,用來擋風。」
眼前景漸漸從高矮錯落的房屋變作城門,賀聞秋不曾停留,拋了塊牌子給守門的衛軍,接著便很順暢地出了京城。
目一片被茫茫白雪覆蓋的原野,接著賀聞秋勒了馬,微微側過臉,看著我。
「有沒有覺得心好點?」他說,「你看天大地大,何必在一棵樹上……」
可能是覺得不吉利,他把最后兩個字吞了回去。
我沉默片刻,把他扔給我的斗篷又往上拽了拽,才平靜道:「我沒有覺得心不好。」
「但你未婚夫……」
「他很快就不是了。」
我長長地吐出一口氣,像是終于說服自己放下了某種執念,
「回家后我理好一切,便會和他解除婚約。」
自小有頑疾,我很清楚,我大概率是活不過二十歲的。
爹娘待我如珠似寶,叔伯兄弟又對姜家家業虎視眈眈,因此我務必要想辦法,至為姜家留下一個繼承人。
挑中崔寧遠算是無奈之舉。
這三年來我對他和崔寧枝沒有半分薄待,縱然他的厭惡疏離從不加掩飾,我也不曾計較。
可他竟然要徹底毀掉姜家。
若那個夢就是未來會發生的事,那便是我引狼室,一手造的禍端。
聽我這麼說,賀聞秋眼睛亮了亮,卻又強裝鎮定道:
「其實你那天在學堂的提議,我回去后考慮了一下,覺得很是不錯。」
「既然你與他的婚約解除了,選我也不是不可以。」
我沉默片刻:「你……不行。」
賀聞秋不敢置信:「為什麼?!難道我還比不過那個恩將仇報,一心想吃絕戶的凰男?」
他看起來很生氣,仿佛我不給個說得過去的理由,就會當場把我從馬背扔下去。
「因為你是賀家唯一的嫡子。」
我淡淡地說,
「你有你必須擔負的責任,我自然也有我的。那一日在學堂說過的話,是我失禮,若你心有芥,改日我會帶著厚禮親自上門賠罪。」
「姜笛!」
「你若心懷不滿,可以現在放下我,我自己回去便是。」
話雖這麼說,賀聞秋卻完全沒有丟下我的意思,握著韁繩的那只手反而更用力了:
「哼,我說過要把你完好無損地送回去,當然不會食言。」
「那便多謝賀公子了。」
他一邊策馬,一邊又冷哼一聲:「錯過我這麼一個乖巧懂事的帥哥,你未來一定會后悔的!」
「……」
這話我實在接不上,只好閉口不
言。
6
直到把我送回姜家府邸,賀聞秋都沒有再說過一句話。
重新見到綺月后,他將我放下馬,一手撈回借我擋風的那件斗篷,扯著韁繩就要離開,卻又止住。
他坐在馬背上,居高臨下地著我。
這作本該是很有氣勢的,然而他說出的話卻截然相反:
「若我不再是賀家唯一的嫡子,能不能贅你姜家?」
「……」
邊扶著我的綺月一個踉蹌,再看去,風雪中的賀聞秋已經漸漸遠了。
我默然著他的背影,直到綺月小心翼翼地開口:
「姑娘,雪又大了,外頭冷,還是快些回去吧。」
堂屋擱著兩個炭籠,拉扯出一片暖烘烘的熱氣。
我環視一圈,不見崔寧遠和崔寧枝的影。
「崔姑娘午膳后就出去了,說是要尋什麼人。崔公子仍在西三坊,幫著寫方子抓藥。」
我點頭表示知道了,猶豫片刻后,還是去見了爹娘,將退婚的事說了出來。
娘確認了我并不是賭氣或者玩笑,竟然松了口氣:
「你總算想清楚,收了心。那崔寧遠狼子野心,實非良人。」
我目掃過和我爹的神,猛然意識到什麼:「爹和娘一直不喜歡他嗎?」
爹嘆了口氣:
「此人心思頗深,又善鉆營,借你之勢了京城學堂后,便搭上了七皇子那邊。若日后他真的與你親,想必我姜家也會被強行綁上儲君之爭的大船。」
我怔在原地。
所以,崔寧遠是因為在爭儲中為七皇子立下大功,未來才得以平步青云嗎?
離開書房后,我攏斗篷往回走,綺月輕聲問著我晚膳想吃什麼。
我張了張口,正要說話,腦中卻不知怎麼的,回想起出京路上賀聞秋的絮絮叨叨。
「……姑娘?」
綺月又了一聲,我回過神:「晚膳……來一盅燉羊吧。」
直到天黑,崔寧遠才帶著崔寧枝回府。
兩個人邊都帶著笑,似乎心不錯。
我坐在堂屋靜靜等著,崔寧遠見了我,笑容一收,正要走,我住他:「退婚吧。」
他猛地回頭,不敢置信地看著我:「你說什麼?」
「我要與你退婚。」我一字一句地說,「崔寧遠,從今夜起,你我婚約解除。你可去尋你的心上人,我也會另覓良婿。」
他死死盯著我,大概是意識到我并不是要與他相商,而是在通知他。
「姜笛!」
不等他開口,一旁的崔寧枝已經開口怒斥:
「你算什麼東西,怎麼敢對我哥哥召之即來揮之即去?你知不知道,就算七皇……」
話沒說完,崔寧遠忽然冷了臉呵斥:「寧枝!」
崔寧枝像是意識到自己失言,慌忙閉了。
我嗤笑一聲:「你在塾待了三年,竟一點長進都沒有。」
往常我若這麼說崔寧枝,崔寧遠一定會立刻跳出來護著。
但此刻他竟然只是目不轉睛地看著我:
「這麼說,你心里已有了新的人選。姜笛,在你心里我到底算什麼?一個贅姜家的備選,此刻有了更好的,便棄之不用了?」
我喝了口杯子里的熱牛,淡淡道:
「怎麼只許你與那位醫唐姑娘你儂我儂,就不許我早日另做打算嗎?」
「唐?我與只是朋友而已。君子之,向來坦。」
崔寧遠飛快地解釋了一句。
我盯著他坦的神,一時無言。
這是我第一次發現,崔寧遠這人……相當無恥。
「究竟是朋友還是存了旁的心思,你自己心知肚明。」
我不想再和他爭辯,放下杯子站起來,
「退婚庚帖我明天拿給你,你和崔寧枝三日后搬出去。至于京城學堂那邊,我抱恙,不會再去,你若還想繼續,自便就是。」
姜家只有我一個獨,因此我爹一直將我當作繼承人培養。
及笄前我已對經史策論薄有研究,之所以還日日去學堂,不過是為了陪著崔寧遠而已。
事實上,他也從沒領過我的。
得了我的命令,侍衛們作很快,三日一到便客氣冷漠地將崔寧遠兄妹請了出去。
他們離開那日難得天晴,我穿著襖站在門口,面淡淡地看著。
崔寧遠出了門,卻忽然停住腳步,轉頭向我看來。
「姜笛。」
他極連名帶姓地喊我,嗓音又冷又銳,像柄開刃的利劍,
「今日之恥,連同三年來的屈辱,來日我會一樣一樣地還給你。」
我張了張,還沒來得及開口,后面忽然傳來一道悉的聲音,聽起來喜氣洋洋:
「喲,頭一回見到這麼無恥的,
帶著妹妹在別人家蹭吃蹭喝蹭學堂三年,不當牛做馬報恩就算了,反而視為恥辱——」
目流轉,我看到馬上一獵獵紅的賀聞秋,正神態從容地停在門前。
崔寧遠的神,一下子變得很難看。
猜你喜歡
-
完結718 章

嬌妃火辣辣
某夜,某人爬牆被逮個正著。 「王妃欲往何處去?」 「那個……南楚世子東陵太子和西炎王又不老實了,我削他們去」 「那個不急,下來,本王急了……」
136.3萬字8 27080 -
完結156 章

穿成侯門寡婦後,誤惹奸臣逃不掉
【雙c 傳統古言】沈窈穿越了,穿成了丈夫剛去世的侯門新鮮小寡婦。丈夫是侯府二郎,身體不好,卻又花心好女色,家裏養著妾侍通房,外麵養著外室花娘。縱欲過度,死在了女人身上……了解了前因後果的沈窈,隻想著等孝期過了後,她求得一紙放妻書,離開侯府。男人都死了,她可不會愚蠢的帶著豐厚的嫁妝,替別人養娃。 ***謝臨淵剛回侯府,便瞧見那身穿孝服擋不住渾身俏麗的小娘子,麵上不熟。但他知道,那是他二弟剛娶過門的妻子。“弟妹,節哀……。”瞧見謝臨淵來,沈窈拿著帕子哭的越發傷心。午夜時分,倩影恍惚,讓人差點失了分寸。 ***一年後,沈窈想著終於可以解放了,她正要去找大伯哥替弟給她放妻書。沒想到的是,她那常年臥病在床的大嫂又去世了。沈窈帶著二房的人去吊唁,看著那身穿孝服的大伯哥。“大伯哥,節哀……。”謝臨淵抬眸看向沈窈,啞聲說道:“放你離開之事,往後延延……。”“不著急。”沈窈沒想到,她一句不著急, 非但沒走成,還被安排管起侯府內務來。後來更是直接將自己也管到了謝老大的房內。大伯哥跟弟妹,這關係不太正經。她想跑。謝臨淵看著沈窈,嗓音沙啞:這輩子別想逃,你肚子裏出的孩子,隻能是我的。
31.5萬字8.18 9189 -
完結12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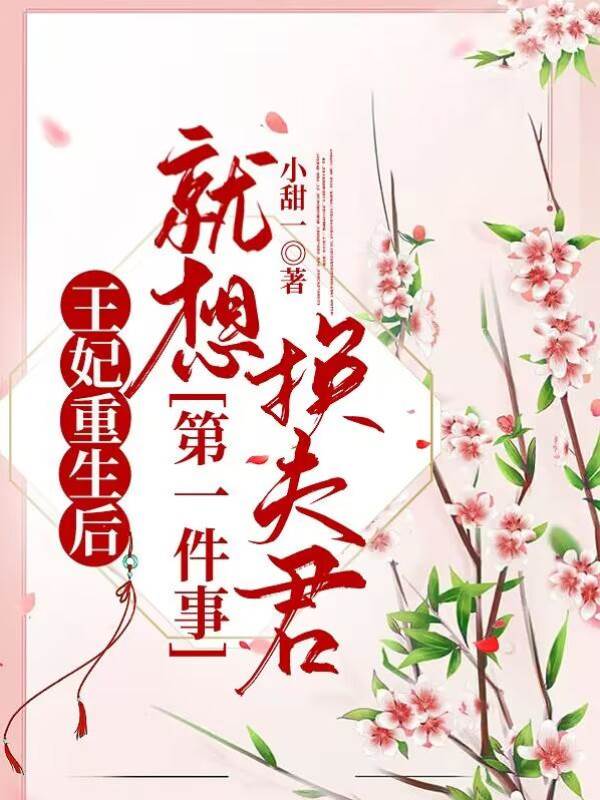
王妃重生後,第一件事就想換夫君
上輩子盛年死於肺癆的昭王妃蘇妧重生了。回想自己前一世,溫婉賢惠,端方持家,一心想把那個冰塊一樣的夫君的心捂熱,結果可想而知;非但沒把冰塊捂化了,反而累的自己年紀輕輕一身毛病,最後還英年早逝;重生一世,蘇妧仔細謹慎的考慮了很久,覺得前世的自己有點矯情,明明有錢有權有娃,還要什麼男人?她剛動了那麼一丟丟想換人的心思,沒成想前世的那個冤家居然也重生了!PS:①日常種田文,②寫男女主,也有男女主的兄弟姐妹③微宅鬥,不虐,就是讓兩個前世沒長嘴的家夥這輩子好好談戀愛好好在一起!(雷者慎入)④雙方都沒有原則性問題!
34.3萬字8 20883 -
完結279 章

嫁給兄長的竹馬
寧姒10歲時遇見了16歲的姜煜,少年眉目如畫,溫柔清雅,生有一雙愛笑桃花眼,和她逗比親哥形成了慘烈的對比。 那少年郎待她溫柔親暱,閒來逗耍,一口一個“妹妹”。 寧姒既享受又酸澀,同時小心藏好不合時宜的心思。 待她出落成少女之姿,打算永遠敬他如兄長,姜煜卻勾起脣角笑得風流,“姒兒妹妹,怎麼不叫阿煜哥哥了?” 【小劇場】 寧姒十歲時—— 寧澈對姜煜說,“別教她喝酒,喝醉了你照顧,別賴我。”嫌棄得恨不得寧姒是姜煜的妹妹。 姜煜微醺,“我照顧。” 寧姒十六歲—— 寧澈親眼看到寧姒勾着姜煜的脖子,兩人姿態親密。 姜煜低頭在寧姒臉頰上親了一口,然後對寧澈笑,“阿澈,要揍便揍,別打臉。”
42.9萬字8.18 11084 -
完結309 章

釣餌
周宴京電話打來時,陳桑剛把他白月光的弟弟釣到手。周宴京:“陳桑,離了我,你對別的男人有感覺?”弟弟雙手掐著陳桑的腰,視線往下滑:“好像……感覺還不少。”……“在我貧瘠的土地上,你是最後的玫瑰。”【飲食男女 男二上位 人間清醒釣係美人VS偏執腹黑瘋批大佬】
53.4萬字8.18 6024 -
完結123 章

傻妃配殘王
最近京城可出了個人人皆知的大笑話,將軍府中的傻公子被太子殿下退貨轉手給了殘王,傻子配殘王,天生一對。 世人卻不知這被人人嘲笑的某人和某王正各自私地下打著小算盤呢。 “報,王爺,外面有人欺負王妃殿下。” 某人聞言,眉頭一挑:“將本王四十米的刀拿來,分分鐘砍死他,活得不耐煩了!!” “報,王爺………………,”某士兵支支吾吾的看著心情不錯的某人。 “怎麼了,誰又欺負王妃殿下了?” “王爺,這次并不是,王妃殿下他去了春香閣……………………” 砰的一聲,某人身下的輪椅碎成了幾塊:“給本王帶兵將春香閣拆了!” 歡脫1V1有副cp
15.5萬字8 5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