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甜妻吻安:總裁老公超棒的》 第1242章 動如參與商(4)
這場架最後還是沒有打起來,因為來這裏是執行任務,不是旅遊的。
這次任務相對來說比較簡單,原本計劃的三天時間本就沒有用上,一天四人就解決了任務目標,這小地方雖然偏遠,但是風景秀麗,祝非白突發奇想,想要去山上營。
傅沉寒一向是無所謂的,去也行不去也行,魏恪很縱容祝非白,自然也就同意了,只有騰蛇表示了拒絕,但是因為沒有一票否決權,最後還是背上了登山包。
那天晚上星漢燦爛,正好是七夕節,祝非白在看見銀河的時候才反應過來,愣了愣,隨即笑道:「咱們這個時間選的倒是不錯。」
騰蛇冷嘲熱諷:「七夕節是之間的節日,我們一群單狗,過什麼七夕節?」
「誰說我是單狗了?」祝非白拉開了一罐啤酒,躺在草地上笑著說:「我有朋友的。」
Advertisement
幾人都是一愣,魏恪笑問:「我怎麼不知道你什麼時候了朋友?」
祝非白唔了一聲,道:「我已經不是小孩子了,總不能事事都要像小時候那樣跟你報備吧?」
魏恪頓了一會兒,才說:「是我認識的人嗎?」
祝非白道:「不是。」
連騰蛇都忍不住八卦:「是你先追求的人家吧?」
祝非白笑:「還沒追到手呢。」
騰蛇就翻了個白眼:「那你還好意思說人家是你的朋友?!」
「早晚都是唄。」祝非白笑嘻嘻的道:「說說又不犯法。」
魏恪笑著搖搖頭,喝了口啤酒。
這啤酒買的時候是冰凍的,現在已經恢復常溫了,只是拿在手裏,蹭了一手的水,他垂眸用紙巾慢慢的將手上的水去,祝非白轉眸問他:「誒,你有喜歡的人嗎?」
「沒有。」魏恪說:「一天天的這麼忙,哪有時間談?」
祝非白道:「時間就像是海綿里的水,一總是會有的。」
騰蛇嗤笑:「人家出時間是為了學習,你出時間是為了談?」
祝非白難得沒有跟騰蛇爭辯什麼,他只是喝了一口啤酒,看著天上的星星,說:「談也是人生里很重要的事啊。」
他忽然看向傅沉寒:「Azalea,你呢?你喜歡哪種類型的孩子?」
傅沉寒垂眸著自己的匕首,似乎對頭頂的滿天星辰毫無興趣,聽見祝非白的問話,道:「省心聽話的。」
頓了頓,又補充:「當然,沒有最好。」
祝非白:「……」
祝非白大笑:「那你這是要注孤生啊。」
「別胡說。」魏恪道:「像我們外甥這樣的,將來肯定會有很多孩子飛蛾撲火的。」
騰蛇道:「你也說了是飛蛾撲火。」
聲音忽而有些悲傷:「飛蛾用盡了自己全部的熱,明知道是死路一條,仍舊義無反顧,但是火,永遠都不會知道它的深。」
一陣沉默。
魏恪了的頭髮,說:「我記得你大學學的是理科?怎麼這麼多愁善?」
騰蛇抿了抿,看著篝火里魏恪和的側,到底是什麼都沒說。
。
猜你喜歡
-
完結43 章

春色難馴
江城時家弄丟的小女兒終于回來了。 整個時家,她要星星還強塞月亮。 —————— 二中開學,時年攬著好不容易找回來的妹妹招搖過市。 眾人看著那個被時年夾在咯吱窩里,眉眼如春的小姑娘,紛紛誤會,“小嫂子絕了,絕了啊。” “想什麼呢?!”時年忿忿,“這是我妹!” 時·暴躁大佬·年,轉頭笑成智障,“歲歲,叫哥。” 此時,一位時年的死對頭,江·清貧(?)學神·頂級神顏·骨頭拳頭一起硬·馴,恰巧路過—— 椿歲哥字喊了一半,就對著江馴甜甜一聲,“哥哥!” 江馴看著這對兄妹,鳳眼微掀,漠然一瞥,走了。 時·萬年老二·考試總被壓一頭·年:“???”啊啊啊啊你他媽什麼態度?!所以為什麼你連哥都比我多一個字?! —————— 時年曾經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江馴踩在腳下,讓那個硬骨頭心甘情愿叫他一聲“哥”。 直到看見死對頭把他親妹子摁在墻角邊(沒親,絕對沒親)。 時年真的怒了,“你他媽壓.我就算了,還想壓.我妹??!!” 江馴護著身前的椿歲,偏頭懶聲,“哥。” 椿歲:“…………” 時年:“???”啊啊啊啊別他媽叫我哥我沒你這種妹夫!! —————— 小劇場: 椿歲:“為什麼裝不認識?” 江馴:“怕你喜歡我啊。” 椿歲嘁笑,“那為什麼又不裝了啊?” 春夜的風,吹來輕碎花香。 江馴仰頭,看著枝椏上晃腿輕笑的少女,低聲笑喃:“因為……我喜歡你啊。” #你是春色無邊,是難馴的執念# 冷漠美強慘X白甜小太陽 一句話簡介:我成了真千金你就不認識我了? 1V1,HE,雙初戀。不太正經的治愈小甜文。
16.3萬字8.18 6106 -
完結1181 章
余生悲歡皆為你
婚前,她當他是盲人;婚后,方知他是“狼人”。 * “你娶我吧,婚后我會對你忠誠,你要保我不死。”走投無路,喬玖笙找上了傳聞中患有眼疾、不近美|色的方俞生。 他空洞雙眸毫無波瀾,卻道:“好。” 一夜之間,喬玖笙榮升方家大少奶奶,風光無限。 * 婚前他對她說:“不要因為我是盲人看不見,你就敢明目張膽的偷看我。” 婚禮當晚,他對她說:“你大可不必穿得像只熊,我這人不近美|色。” 婚后半年,只因她多看了一眼某男性,此后,她電腦手機床頭柜辦公桌錢包夾里,全都是方先生的自拍照。 且看男主如何在打臉大道上,越奔越遠。
216.9萬字8 12334 -
完結6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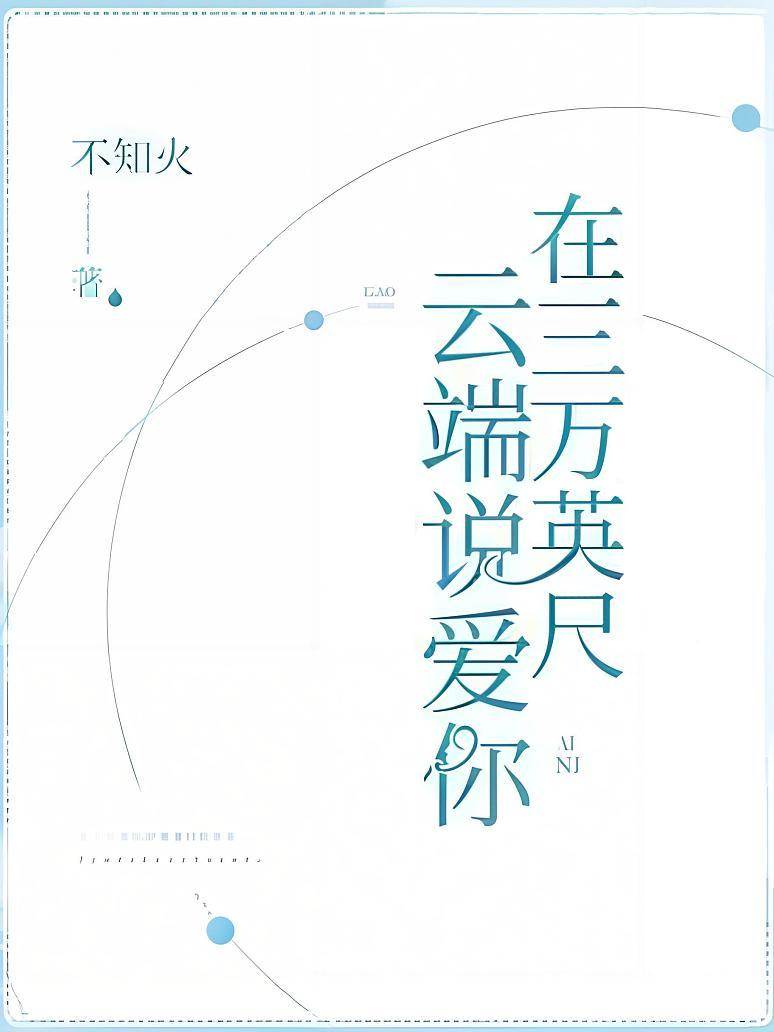
在三萬英尺云端說愛你
高考過后,楊斯堯表白周月年,兩人在一起,但后來因為性格不合,和楊母從中阻撓,周月年和楊斯堯憤而分手。分手之后,兩人還惦記著對方,幾番尋覓,終于重新在一起。周月年飛機故障,卻因為楊斯堯研制的新型起落架得以保全生命,兩人一同站在表彰臺上,共同迎接新的生活,新的考驗。
18.2萬字8 37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