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謀卿心》 第209章 因果循環,報應不爽
“謝謝你跟我說了這些。”李珺喬眼瞼低垂,似帶著十分的疲倦,“這些賞銀是你應得的。”
說罷,從袖中取出一張銀票,雙手奉上。
劉蓮娘并把銀錢拿到手上,展開看了一眼,復又塞回李珺喬的手中。
“我來尋你,并非為了這些銀錢。”
一邊用那塊布面簾重新遮擋面容,一邊對李珺喬說,“我不過是見有人與我一樣,想要尋到那婦人,想著會不會是同病之人,以圖互相報團取暖罷了。”
“既然姑娘并非同路之人,彼此就當萍水相逢,就此別過。”
說完這話,便從凳子上站起來,正轉離去。
看著劉蓮娘單薄的背影,李珺喬有些不忍,思慮再三以后,還是決定把黃盼憐已死之事告知。
“你要尋的那個婦人已經死了。”李珺喬特意把話放緩了來說。
此時李珺喬明顯到劉蓮娘腳下一滯,放置在兩側的手下意識握了拳頭。
此時猛然轉過了子,眼神寫滿了震驚和不愿相信。
也就是數秒之間,剛才還冷靜自持的子,突然變得有些歇斯底里,不由分說便扯住了李珺喬的袖。
力度之大,就連李珺喬也被扯得子一歪,差點就往的方向倒去。
李珺喬聽著話語中帶著萬分不甘,連聲音都在抖,“死了?怎麼能死了?我因為那婦人了這麼多苦,怎麼能如此輕松就死了?”
李珺喬明白此刻的心,淡淡地說了句,“也不算死得輕松。一個月前在江南一客棧投宿,結果那客棧失火,被困其中,被煙火所傷,尸尚在縣衙,無人認領。”
劉蓮娘聞言連連往后跌退幾步,冷笑一聲,“把人送火坑之人,最后也喪命于火海,妙啊,妙啊。”
Advertisement
“我從不信天理循環,因果報應,但如果這就是上蒼報應在黃盼憐上的因果,我得雙手合十,對祂道一聲謝。”
正當李珺喬以為這件事能告一段落時,聽到了劉蓮娘問了句,“那婦人的尸首無人認領?那所謂的‘閨’又在何?是不是也一同死在那場事故之中了?”
李珺喬聽出了劉蓮娘的意思,昧著良心地回了句,“這個我也不知道。”
雖說李珺喬竭力讓自己面不改,但畢竟劉蓮娘在風月場所混跡過數月,也見過各式各樣的人,還是輕而易舉地察覺到神不對勁。
直直地向李珺喬,冷不防問了句,“既然你一開始就知道黃盼憐已經死了,那你為何還要到此去尋?我看你真正所圖,并不在此吧。”
李珺喬本就心中有鬼,此番被劉蓮娘這麼一問,更覺心慌不已。
李珺喬擔心要是跟劉蓮娘坦誠,家中姑姑正是當日給送水的子,只怕以這般堅韌的子,恐會去尋李歸晴的麻煩。
先不說當日姑姑是否被黃盼憐所脅迫,做出這種為虎作倀之事來。如今李歸晴已如五歲孩一般,對過往之事早就沒了記憶,即使劉蓮娘執意要尋仇,也是于事無補。
眼見如今錯誤已,誠然李珺喬憐惜劉蓮娘的遭遇,但要讓大義滅親,把姑姑的去向告知,這事做不到。
但劉蓮娘如此聰慧,明顯已經起了疑心,要是李珺喬沒能想到合適的說辭把糊弄過去,只怕后患無窮。
頃刻之間,的大腦快速運轉,終于給想到了一個辦法。
打定主意以后,馬上抬眸對劉蓮娘說,“我的確志不在黃盼憐,我真正要尋的人,是畫像上的另一個男子。”
“這男子盜取了我一樣十分重要的件,然后逃逸到范疆。我也曾報,但府卻以客棧失火一事,尚未聯系到部分遇難之人的親人,所以無暇顧及我。”
“幸好衙之有我相之人,告訴我只要尋到黃盼憐的親人,把尸首認領回去,便能幫我尋獲已失之。”
“我雖知道衙不一定靠得住,還是做好了兩手準備,把黃盼憐的畫像取了去,跟盜取我件的男子的畫像放在一起,懸賞尋人。”
李珺喬見劉蓮娘半信半疑的樣子,馬上趁熱打鐵地說,“你也看到這次懸賞,的確擺的是兩個人的畫像。”
“正正因為這件事屬于府機,我不愿連累了我那在衙相之人,一開始才沒有告知姑娘。還希姑娘能夠理解。”
李珺喬這話說得在在理,而且事實的確是茶攤外面懸掛的是兩人的畫像,即使是劉蓮娘也一時找不到反駁的理由。
但心中既存了疑心,便不可能如此輕易就被李珺喬打發掉。
既然已經知道李珺喬會在此懸賞,也不急著要走,大可以在茶攤附近悄悄守著,以便觀察李珺喬的真實意圖。
于是,劉蓮娘假意表示相信了李珺喬的話,只說既然那黃盼憐已經死了,留在范疆也無用,還不如從此浪跡天涯,逍遙自在。
故作灑地朝李珺喬拜了拜,“今日得見姑娘,雖然憶及不堪往事,但也算有所收獲,并非白走這一趟。”
“只希姑娘能早日尋獲已失之,心結解除。”
說罷,轉而去,徒留李珺喬一人在原地,著毫不留的背影出神。
李珺喬的聰慧向來不在劉蓮娘之下,所以雖然劉蓮娘上說了放下,但卻不敢掉以輕心。
而去按照劉蓮娘的說法,黃盼憐尚有一遠房表親住在宋梓溪下游,何不干脆拿著這畫像去尋他一番,也好了卻一樁事。
走出簾外,只見茶攤的凳椅上坐著好些附近勞作的農戶,而茶攤夫婦則在殷勤地斟茶遞水,忙前忙后。
聽到那些農戶都在對張在茶攤圍墻的懸賞議論紛紛,話語中不乏對那五十兩銀子的。
“五十兩銀子呢!到底是那一戶人家,出得了那麼高的賞銀?”一個材甚為胖的中年男子對著畫像評頭點足。
“那還用說,肯定不是像你我這樣的農戶,我看著這尋親之人非富則貴,說不定這五十兩銀子在他們看來也不過一頓飯的銀錢。”坐在中年男子旁邊的一個黑瘦男子接了話。
“可惜我從未見過這兩人,要是我見過了,說不定因此一夜發了財,定家中那婆娘不再看輕我!”另一個眉心有一顆黑痣的男子話中似有怨氣。
就在眾人議論紛紛的時候,其中一個眼尖的男子發現站在簾子旁邊的李珺喬。
他見李珺喬臉生,又生得貌,便用調侃的語氣跟茶攤夫婦說,“徐大哥,你什麼時候得了這麼一個閨?長得還俏的。”
因著這個男子的話,其他人的目紛紛投落到李珺喬上來。
這赤的目,讓李珺喬渾不舒服,正想說話之際,茶攤大哥馬上用眼神向示意,讓不要做聲。
他笑容滿臉地對那個開口的男子說,“看你這話說的,你什麼時候見過我有閨了?這是我遠方表親的兒,按輩分還得喊我一聲表舅舅呢。”
那男子一聽更好奇了,“那不知道你這表侄許親了沒?”
其他人馬上明白過來那男子的意思,紛紛起哄。
茶攤大哥馬上說,“不好,下不了地干活的,家都被的病拖著,就別連累別人了,你要是想說親,還是去尋東門的黃家吧。”
在場的人此時才察覺李珺喬雖然俏麗,但一副弱柳扶風的樣子,臉上更是稍稍蒼白,跟平日所見的農家姑娘想必,果真帶了幾分病態。
農戶之家的子是必然要勞家務活兒的,誰也不愿意娶一個病秧子在家中,所以眾人著李珺喬,只覺得有些可惜了。
就連剛剛開口說話的男子,也低著頭,只顧著大口喝茶,全然不提說親之事了。
茶攤大哥這才對呆在原地一臉懵然的李珺喬說,“還傻傻站在這里做什麼?!”
李珺喬這才回過神來,迅速退回簾子里去了。
聽著外面那些男子肆意大聲調笑,話語俗,不堪耳,心中只覺得莫名煩躁。
不多久,茶攤嫂子便進來了,徑直走到李珺喬邊,低聲音地對說,“姑娘,你莫要生氣,我家那口子這是為了保護你。”
“剛才開口的那個男子是村長的獨子,從小被村長寵著,便變得霸王一般。要是他看上了你,即使沒能把你要到手,也會折騰一番。”
“但因為村長只有他一個兒子,所以要求娶的姑娘一定要康健、看起來好生養的,這才能讓他家子嗣延綿,枝繁葉茂。”
“所以我家那口子才不得不借口說姑娘有病,好斷了他的心。希姑娘千萬不要怪他,他也是好心。”
李珺喬見茶攤嫂子一臉擔憂的樣子,連忙安說,“我還在尋思怎麼大哥會說出這番話來,沒想到當中竟有這樣的講究。”
“我這番過來尋親,自然不想惹上什麼麻煩,大哥嫂子能這般為我考慮,我恩戴德還來不及,又怎會怪你們呢。”
“說到底都是我給大哥和嫂子帶來麻煩了,要是我在這里會影響到你們的營生,要不我還是離去吧。”
茶攤嫂子馬上拉著李珺喬的手,勸說道,“你一個姑娘家,只一人來這里,遇著我們夫婦也算是彼此的緣分,我們怎忍心讓你孤離去?”
“你就放心在這里住下,只是不要再出茶攤了。雖說懸賞沒什麼大錯,但五十兩不是小數目,要是讓有心之人知道你懷巨財,只怕會惹來禍端。”
“所以我和我家那口子商量過了,要是有人來尋,說有畫像那兩人的消息,你只說你是尋親那戶人家的丫頭,老爺夫人不好出面,派了你這個丫頭來探路,問話可以問,但要回了老爺夫人,才能拿到賞銀。”
“如此一來,方能保障姑娘的安危。你懂我的意思了嗎?”
李珺喬沒想到五十兩賞銀居然還牽扯到如此大的問題,頓時到自己考慮不周,竟沒有眼前這個一麻布的農家婦人思慮得周詳。
看來掌家時候學到的為人世之道,也不過是學了個皮,真正的本領,還得在宅門之外才能學到。
李珺喬對茶攤嫂子的建議表示了認同,還歉疚地說了句,“原是我考慮不周,竟沒想到還有這一層關系了。”
茶攤嫂子卻安說,“你年紀輕輕的,已經比其他姑娘考慮得多了,只是嫂子比你年長幾歲,才得了些經驗罷了。”
“你也別怕,我家口子頗認得些人,說不定很快就能打探到你親人的消息了,你且安心住下吧。”
李珺喬激地點了點頭,“恭敬不如從命,那就麻煩嫂子了。”
茶攤嫂子擺了擺手,“也多虧你這懸賞,今天茶攤的生意比平日要好上不呢,很多都是聽聞了有這麼一回事,特意借著吃茶的理由過來看賞的。”
把李珺喬拉到一旁的桌子,讓坐下來等待,“你大哥在外面怕是忙瘋了,我也得出去幫忙了。姑娘要是覺得了,灶頭還熱著小米粥,你可以自個兒盛些出來吃。”
“今日的茶水買得快,大概會比平日早收攤,到時候嫂子再帶你回家里去,給你做好吃的。”
看著茶攤嫂子轉離開的影,李珺喬不由得想起昨夜那兩碟炒糊了的菜,開始想念起今夕的手藝來。
雖對吃食不甚講究,但這些年也不知不覺被今夕調教得對飯菜也有要求起來,想著要是再沒打探到拓跋繁的消息,只怕回到江南之時,便要瘦上一圈了。
但念到今天一早便已把家書寫好,給了茶攤大哥幫忙寄出,想必過不了幾天,今夕便能收到了吧。
猜你喜歡
-
完結85 章

暴君的囚籠
鎮國公家的幼女江知宜自幼體弱,一朝病重,眼看就要香消玉殞。有云遊的和尚登門拜訪,斷言其命格虛弱,若能嫁得像上將軍那樣殺氣重、陽氣足的夫婿,或許還能保住性命。鎮國公為救愛女、四處奔波,終於與將軍府交換喜帖,好事將成。然而變故突生。當夜,算命的和尚被拔舌懸於樑上,上將軍突然被派往塞外,而氣咽聲絲的江知宜,則由一頂轎攆抬進了皇宮。她被困於榻上一角,陰鷙狠絕的帝王俯身而下,伸手握住她的後頸,逼她伏在自己肩頭,貼耳相問,“試問這天下,還有比朕殺氣重、陽氣足的人?”#他有一座雕樑畫棟的宮殿,裡面住著位玉軟花柔的美人,他打算將殿門永遠緊鎖,直到她心甘情願為他彎頸# 【高亮】 1.架空、雙潔、HE 2.皇帝強取豪奪,愛是真的,狗也是真的,瘋批一個,介意慎入! 3.非純甜文,大致過程是虐女主(身)→帶玻璃渣的糖→虐男主(身+心)→真正的甜
27.4萬字8 29018 -
完結13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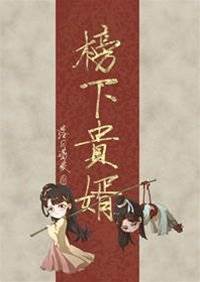
榜下貴婿
預收坑《五師妹》,簡介在本文文案下面。本文文案:江寧府簡家世代經營金飾,是小有名氣的老字號金鋪。簡老爺金銀不愁,欲以商賈之身擠入名流,于是生出替獨女簡明舒招個貴婿的心思來。簡老爺廣撒網,挑中幾位寒門士子悉心栽培、贈金送銀,只待中榜捉婿。陸徜…
46.9萬字8 7765 -
完結899 章
權寵天下:紈絝惡妃要虐渣
她不學無術,輕佻無狀,他背負國讎家恨,滿身血腥的國師,所有人都說他暴戾無情,身患斷袖,為擺脫進宮成為玩物的命運,她跳上他的馬車,從此以後人生簡直是開了掛,虐渣父,打白蓮,帝王寶庫也敢翻一翻,越發囂張跋扈,惹了禍,她只管窩在他懷裏,「要抱抱」 只是抱著抱著,怎麼就有了崽子?「國師大人,你不是斷袖嗎......」 他眉頭皺的能夾死蒼蠅,等崽子落了地,他一定要讓她知道,他到底是不是斷袖!
76.9萬字8 2029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