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后歸來之鳳還朝》 第129章 舊事重提
燕歡想了好一會兒,也沒記起這麼一號人。
楚霽心思深沉,手底下的布置太多,對誰都不會全信。
即使是,也不知道所有的藏在暗的后手。
只是這鶯兒出現的時機太巧,燕歡又素來謹慎,略一思索,還是放不下。
得多加留意著。
一曲落下。
鶯兒面含春,端起酒杯,輕移蓮步,緩緩走到了楚玉前,聲道:
“公子宇軒昂,一見就知不似凡人,奴家有幸被邀而來,想要敬公子一杯,還請公子莫要嫌棄奴家這酒,不夠溫。”
微垂著頭,只用余瞥著他,好似的不行,一雙眼眸當中,卻盡是毫不遮掩的仰慕。
若是旁人給瞧了一眼,怕不是連骨頭,都要徹底下去。
可楚玉只是輕笑一聲,起道:
“叨擾姑娘,已是冒犯,哪來嫌的道理。”
鶯兒眼睛一亮,素手一,酒灑出幾滴,滾至手背,又沿著的一路下,沒在了雪白的袖口。
低呼一聲,咬了下,懊惱道:
“呀,鶯兒這高興又張的,都給公子面前失態了。”
男人心,是極為懂得。
這像是天生的妖,一舉一,都帶了些渾然天的態。
就是姿容比不得燕喚喜,可給年齡累加的風萬種上,鶯兒遠勝了不止一籌。
連楚玉都給那副小人的態,看的晃了晃神。
但他很快反應過來,遞出手帕,道:
“無事,鶯兒姑娘莫要張。”
“謝過公子了。”
鶯兒接了帕子,卻攥在掌心,舍不得去用。一口氣喝干了殘酒,對楚玉粲然一笑,轉又端著杯走向了另一位公子。
只留下一陣香風。
給楚玉邊徘徊輾轉,久久不散。
Advertisement
他仿是一愣,而后笑著搖了搖頭,眼眸微闔,瞧不清眼底的緒。
這讓其他的觀察的人,不免有些失。
鶯兒才貌雙絕,又是個清倌,就是深陷紅塵,地位太低,收不到府里,可即使做一日夫妻,也是哉。
不人,都認為楚玉會對興趣。
送上門的紅知己,誰不想順水推舟?
可楚玉只是淡淡。
如此,是有人失有人喜。
鶯兒敬出幾杯酒,余掃著楚玉,看他依舊端坐主位,眼里不免有些愴然。
楚濂倒是瞧喜歡,眼里的欣賞毫不遮掩,視線給上來回掃,語氣也帶著幾分親熱,笑道:
“鶯兒姑娘琴藝湛,師承何?”
“小時候家境尚可,跟著一位老先生學了幾日。”鶯兒低眉斂目,態度恭順,聲繼續道:“后來會看譜子,就自己個練了。”
“家境尚可?”楚濂若有所思,“那是因為家道中落,在淪落風塵的了?說書先生里,可是不你這樣的事兒。”
鶯兒指尖一頓,笑道:“公子喜歡聽說書?”
聲音輕緩,尾音卻微微上挑,鉤子一樣,帶著心尖都向上一提。
楚濂瞧著,眼底一片滾燙,也沒注意到刻意調轉了話題。
燕歡給一旁,聽得一清二楚。
一直留出三分神,放到鶯兒的上。
也是注意到了些有趣的東西。
雖是沒法知曉是誰的人,但卻看得出來,對楚玉,的確有刻意的討好和接近。
鶯兒遮掩的功夫已經學的不錯。
但兩者一比較,也不知道是不是故意做出來給楚玉看,對楚濂的熱絡,明顯差上不止一籌。
燕歡低頭抿了口茶。
也有去注意楚霽,不過他演技高超,未曾出毫馬腳,
也是,若非如此,也不會騙到碎骨,才算清醒了。
楚濂和鶯兒聊得興起,大手一揮,道:
“不喝了。來來來,借酒論賦,今個可是詩會。”
“對啊,酒酣耳熱,正是詩興大發的好時候!”
“那就要獻丑了。”
有楚濂挑頭,其他人自然不會拒絕。
燕喚喜最為高興。
鶯兒一到,方才給眾人環繞中央,簇擁夸贊不絕于耳的場面,頓時散了一片空。
琴藝這方面,鶯兒確實湛,燕喚喜心中雖憋悶,但也是清楚,這一點,確實是比不得。
可一青樓子,忙著涂脂抹,給男人面前賣弄風,詩作賦這方面,又哪能通曉?
怎麼比得讀書認字,四書五經?
燕喚喜志得意滿。
主道:
“若是諸位公子不介意,就由喚喜先來如何?”
楚濂這才又給注意力重新轉回的上,笑道:“喚喜愿意,自然最好不過,就是不知道,想以什麼為題?”
燕喚喜并未作聲,掩面一笑。
此次出行,既是楚玉牽頭,就沒有旁人定題的道理。
也是知曉,眸瞥向了楚玉。
楚玉略一沉,道:“今日好時好景,又有三位如此出眾的姑娘愿意來此一聚,就以賞字為題吧。”
燕喚喜笑著點了點頭。
自然不會現作。
既要出頭,就得盡善盡。
干脆選了一首之前給全昔韞批注過的。
的嗓音尚且,婉轉間,還帶著一抹飛揚的靈。
襯著的尚未徹底張開,卻已有絕之姿的眉眼,足讓人,移不開視線。
他們屏息凝神。
不忍這一幕游走。
可尾音徐徐落下,燕喚喜面頰泛紅,眼中滿是得,故作謙虛道:
“喚喜愚笨,這短時間之,只能作到如此程度,還請各位公子,莫要見怪。”
“哪里的話。”楚濂這回倒是反應的快,第一個搖頭,贊嘆道:“之前見天畫像,遠不及喚喜三分貌,便只覺喚喜以人勝仙,竟是忽略了這般才華,怕是連大把書生都比不過,簡直是罪過罪過。”
他這時,倒是利索的很。
只給燕喚喜哄的面帶春意,瞧著他的眼神,都和了不。
鶯兒安靜的坐在楚濂側,等著眾人番夸贊燕喚喜的勁頭過頭,才出聲道:
“姑娘真是好才華,又這般絕,是鶯兒見過最好看的姑娘了。只可惜鶯兒讀的書,不懂這些詩詞上的事兒,但聽了姑娘的詩,眼前倒是一片景。若是諸位不介意,鶯兒可以試著畫下來,以此,一表敬意。”
態度放的極低。
話里話外,給燕喚喜高高捧起。
哄的心覺不妙,卻說不出任何反駁的話。
楚濂自然也不會拒絕,拍手道:“這自然是好!快去準備!”
“那鶯兒,就獻丑了。”
筆墨宣紙很快擺好。
鶯兒執起筆,落下時,竟不帶毫猶豫。
行云流水間,牡丹緩緩綻放。
用的時間很短。
宣紙上的圖畫卻不見任何敷衍的痕跡。
不過一刻多鐘的時間。
鶯兒長出口氣,放了筆,眸一掃,對著楚玉笑道:
“獻丑了。”
眾人連忙上前。
圍在案前,一窺畫卷真容。
墨跡還未干。
卻如卷上的牡丹水未卸。
更添幾分靈。
明是死。
但給鶯兒手里,竟好似雨后清早,牡丹迎晨,重新活過來了一般。
這般畫技,就是和鶯兒最為出眾的琴技一筆,都不逞多讓,若是花時間細致些,怕是都不輸給皇宮的畫師。
在場的都是達顯貴家的爺公子,自然沒幾眼,便瞧得出其中妙。
都不免有些驚訝。
燕喚喜的詩雖然好,可不過是于閨閣小姐而言,加上年紀尚小,多缺了幾分懷大氣。
此來以看。
倒是這詩配不上畫了。
聽著他們對鶯兒的贊賞,燕喚喜的臉是越來越沉。
不管是容貌還是才華,都素來都是眷中最出眾的那個,哪里得了這種事事給比下去的覺。
氣梗在心口,悶的臉發白。
一連兩次。
燕景安也察覺到了不對,他瞥了燕喚喜一眼,看面不對,想了想,開口道:
“鶯兒姑娘果然不同凡響,不過著說起作畫,好像我一妹妹,也很是擅長。”
楚濂揚起眉,“喚喜也會作畫?”
“不是喚喜。”燕景安輕笑一聲,眼神卻是冷了下來,“諸位是不是忘了,今個來的,可不只喚喜這一個妹妹。”
眾人一愣,目流轉,最后落在了燕歡的上。
一直未做聲響。
獨自一人坐在角落品茶賞景。
忽然給這麼多人的視線落到上,也不慌,緩緩放下茶杯,輕聲道:
“哥哥謬贊了,歡不過門,還是常給夫子責備,哪會作畫。”
“歡真是謙虛。”燕景安不依不饒,存心讓給這些人面前落掉臉面,迫道:“之前瑯玡別宛誕辰,你獻上去的,不就是一副扇面畫嗎?我記得,那位貴人可是喜歡的不行,今個諸位公子都在,相信他們也是好奇的。不如,就麻煩你,來繪上一副,讓我們都開開眼界。”
他步步。
又故意提起了六公主誕辰。
讓眾人想起來,燕歡奪得魁首,又哄的六公主對百般寵,甚至上門維護之事。
一個剛回相府沒幾日的私生,竟然能拿出讓公主歡喜的禮,本就離奇。
此時給燕景安一說,對那副畫,他們自然想要一窺。
楚濂更是冷哼一聲,道:“怎麼?難道你的一幅畫,有那般神,只有我妹妹看得,我們卻看不得嗎?”
猜你喜歡
-
完結55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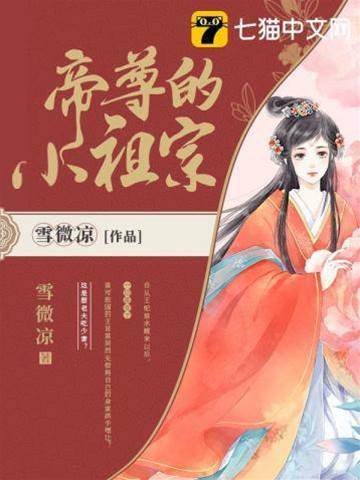
帝尊的小祖宗
自從王妃落水醒來以后,一切都變了。富可敵國的王首富居然無償將自己的身家拱手相讓?這是想老夫吃少妻?姿色傾城,以高嶺之花聞名的鳳傾城居然也化作小奶狗,一臉的討好?這是被王妃給打動了?無情無欲,鐵面冷血的天下第一劍客,竟也有臉紅的時候?這是鐵樹…
99.6萬字8 11327 -
完結506 章

媚婚之嫡女本色
陌桑穿越了,穿越到曆史上沒有記載的時空,職場上向來混得風生水起的白領精英,在這裏卻遇上讓她恨得咬牙切齒的克星,高冷男神——宮憫。 他嫌她為人太過陰詭狠毒。 她嫌他為人太過高冷孤傲。 本想無事可做時,虐虐渣女渣男,逗逗小鮮肉。 豈知一道聖旨,把兩個相互看不順眼的人捆綁在一起,組成嫌棄夫婦。 自此兩人過上相互猜測,彼此防備,暗裏算計,夜夜心驚肉跳的生活。 豈知世事難料,兩個相互嫌棄的人看著看著就順眼。 她說“你是護國賢臣,我是將門忠良,為何跟你在一起,總有種狼狽為奸的覺悟。” 他說“近墨者黑。” 陌桑點點頭,確實是如此。 隻是,到底是誰染黑誰啊? 再後來…… 她說“宮憫,你是不會笑,還是從來不笑?” 他看了她十息,展顏一笑“陌桑,若知道有一天我愛你勝過愛自己,一開始就不會浪費時間防備你、猜疑你,而是把所有的時間用來狠狠愛你,因為一輩子太短,我怕不夠愛你。” 陌桑咽著口水道“夫君,以後千萬別隨便笑,你一笑,人就變得好風騷……” 宮憫麵上黑,下一秒就露出一個魅惑眾生的笑容“娘子放心,為夫隻對你一人笑,隻對你一人風騷。” 某女瞬間流鼻血…… 【這就是一個白領精英穿越到異世古國,遇上高冷男神,被帝王捆綁在一起,相殺互撕,最後相親相愛、強強聯手、狼狽為奸的權謀愛情故事。】
187.7萬字8.18 335163 -
完結639 章

萬毒狂妃懷個寶寶來虐渣
她,本是藥王谷翹楚,卻因圣女大選而落入圈套,被族人害死。 一朝身死,靈魂易主。 楚斐然自萬毒坑中醒來,一雙狠辣的隼目,如同厲鬼蒞臨。 從此,撕白蓮,懲惡女,不是在虐渣,就是在虐渣的路上。 她醫毒雙修,活死人,肉白骨,一手精湛的醫術名動。 此生最大的志向就是搞到賢王手上的二十萬兵馬,為她浴血奮戰,血洗藥王谷! 不料某天,他將她抵在角落,“女人,你懷了本王的孩子,還想跑路?”
110.9萬字8 1245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