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郡主有喜,風光再嫁》 第132章 應對之策
豫和園被封,看們都被驅逐出來,姑娘們,唱們,還有跑兒的小廝們都被關在里頭出不來。
姑娘們著急,看們更著急。
本就是為了最后的結果才看著玩兒的。
如今還沒出來結果,選秀卻看不下去了?那之前的錢不都打了水漂了?
已經約約有“煙雨樓騙錢”的流言散播出來。
蕭玉琢回到煙雨樓中,人拿出最致的燙金請柬,樓里的姑娘拿去熏香。
“娘子是要請誰擺平這件事啊?”竹香問道。
“蘭雪,你去,把今日帶人封了豫和園的捕頭請來。”蕭玉琢吩咐道。
劉蘭雪立即答應。
“別自己去,樓下有人,你帶幾個去,免得他看不上你一個小姑娘,再你吃了虧。”蕭玉琢吩咐道。
劉蘭雪笑嘻嘻的點頭,“便是婢子一個人去,也吃不了虧!”
但知道娘子是關心,還是帶著人去了。
那捕頭也沒客氣,人來請,他便帶著人大大咧咧的來了煙雨樓。
景延年不放心蕭玉琢,悄悄的也跟來了。
他沒上去,就坐在馬車上等著。
他耳力敏銳,萬一煙雨樓里起手來,他也能第一時間沖進去。
可他細細聽著。
卻不聞樓里有什麼靜。
那捕頭分明是氣勢洶洶的來的,還帶了好些人,明擺著是來尋釁挑事兒的。
怎麼這麼久了還沒打起來?
景延年皺眉,忽而想到這是院……
蕭玉琢該不會是樓里的姑娘用人計了吧?
聽說那捕頭面丑,兇神惡煞的……
再者樓里的姑娘哪有他的玉玉好看?
萬一那捕頭看上了玉玉……他的玉玉會不會為了跟他置氣,什麼都不顧惜了?
景延年越想越糟,所謂關心則,越是關心在意的人,越忍不住往壞想。
Advertisement
他繃不住,縱下了馬車。
馬車近旁的侍從都被他嚇了一跳。
景延年正要往煙雨樓里進,可轉念一想,如果不是自己想的那樣,他就這麼著沖進去了,玉玉還不得再跟他生氣?
若是知道他這般誤會,只怕這輩子都不能原諒他了吧?
景延年長吐了一口氣,沖侍從打了幾個手勢,侍從掩護他,他直接從后院墻頭了煙雨樓。
雖然后院有煙雨樓的打手護衛。
可他的手還不至于被幾個院的打手發現。
他在羽林軍里作備的時候,學的就是偵查。
他很快便偵查到了那捕頭和蕭玉琢所在的房間。
他從房頂悄悄的墜到那屋子窗外,側耳聽著里頭靜。
“王捕頭可能還不知道,二十晉十的選秀,有五位新評委。”蕭玉琢的聲音帶著淡淡笑意。
王捕頭面相兇狠,聞言不屑的哼了一聲,“管你什麼評委,與我有何關系?”
蕭玉琢笑了笑。
“我不妨也提醒你一句,如果真是請了什麼了不得的人,你最好趕著派人通知你的評委,這活已經查封,免得到時候,人來了,你卻沒有活拿出手,得罪人,可怪不得王某。”王捕頭冷笑道。
蕭玉琢輕嘆一聲,“唉,王捕頭提醒的是,可如今,我的請柬已經發出去,這五位評委也都答應了要來,如今再說活被查封……那我豈不是已經將人得罪了?”
王捕頭得意一笑,一臉的事不關己。
“若是這五位評委問起來,我免不了的也要將活被查封的原因據實相告。”蕭玉琢緩緩說道。
“喲呵?”王捕頭聞言忽的從座椅上站起來,“怎麼著?小娘子你威脅我呀?”
窗戶外頭的景延年凝眉,聽著屋里頭的氣氛不對,他隨時都要手。
蕭玉琢卻仍舊笑起來,“豈敢豈敢,只是這五位評委,我一個婦道人家,著實得罪不起,不若王捕頭您給出出主意,他們倘若問起來,我也好有個代?”
王捕頭不屑的冷哼一聲,“你都請了誰人做評委?”
蕭玉琢淺笑嫣然,“關中的關三爺,宛城的秦刺史,趙通判,軍中的周將軍,還有就是越王殿下了。”
王捕頭聞言一怔。
見面前娘子笑的淡然,他忽而一,噗通一聲,又跌坐回椅子上。
他艱難的咽了口唾沫,“你……休要胡言,此五位,豈、豈能被你請來……做這勞什子的評委?”
“噓——”蕭玉琢抬手放在邊,“我也提醒您一句,這話在外頭說,可要留神,這五位評委聽到了,估著要不太開心呢!”
王捕頭眼角搐,“休要誆我!”
蕭玉琢微微一笑,“怎麼是誆您呢?我這煙雨秀宛城的活,一沒有涉賭,二為宛城創收,三大大提升了宛城在我大夏的氣質形象。王捕頭可能還沒聽說,如今連長安城的貴胄都在議論,憾這活為何沒有辦在長安城呢!”
蕭玉琢笑容明艷,恍惚人睜不開眼。
那王捕頭額上已是一層細的汗。
“是不是我這屋子里的火攏得太大了?王捕頭別介意,婦人家怕冷。”蕭玉琢笑嘻嘻說道。
那王捕頭臉難看,揚手手下扶自己起來。
“我這兒有些上好的茶葉點心,王捕頭帶回去嘗嘗。”蕭玉琢揮手看向竹香。
竹香連忙端著兩只匣子上前。
匣子里有淡淡甜膩的香味兒。
王捕頭手接過,“乃是有人舉報你煙雨樓的活涉賭,我大夏有規矩,非朝廷批準的賭坊,其他人不準開設賭局!娘子既如此說,本捕回去會詳查此事的!”
他話說的敞亮,聲音卻有些氣弱。
蕭玉琢起福禮,“多謝王捕頭,定是旁人見我煙雨樓紅火,而心生嫉妒,故意攀誣。王捕頭明察秋毫,定不會我煙雨樓蒙冤的!”
王捕頭拱拱手,帶著一干手下,灰溜溜的離開煙雨樓。
他本是徒步而來,回去的時候卻有些腳,手下見他這般樣子回衙門也不像話。
只好人抬了轎子,扶他上去。
轎子上,那王捕頭打開兩只匣子,一只匣子里是致漂亮的點心。
另一只匣子里,除了茶葉意外,還有薄薄的一張票券。
正是聚財寶柜坊的存儲票券。
他可聽人說了,如今聚財寶柜坊的票券,和現錢一個樣兒,在大酒樓大銀樓里都能花用的!
王捕頭反復挲著那張票券,又小心翼翼的將票券塞懷中。
瞧著數額不小,這小娘子還算懂事兒!能請來那五位作評委,看來這煙雨樓,也是得罪不起的!
王捕頭默默的在心里有了決斷。
打發了王捕頭,蕭玉琢心甚好。
樓里的姑娘恰好也把燙金的請柬熏好了宜人的清香,送到面前來。
景延年勾了勾角,離開窗口,又從正門進來。
“你何時請了五位新評委,我怎麼不知道?”他瞇眼問道。
蕭玉琢微微一怔,抬起頭來,“你竟聽?”
景延年輕哼一聲,“古人云,隔墻有耳,不得不防。你沒防備,怎麼怪我?”
蕭玉琢輕哼一聲,“小人。”
景延年皺眉上前,“你別岔開話題,什麼時候請了五位新評委?”
蕭玉琢沒有理會他。
他低頭卻正瞧見,正提筆在請柬上書寫。
看了片刻,他忽的笑出聲來,“原來你真是詐那捕頭,你慣會撒謊麼?我也信了你!”
蕭玉琢不屑,“古人云,兵不厭詐,不得不防。你沒防備,怎麼怪我?”
景延年被一噎,抿住。
見手握狼毫,一筆一劃的寫著請柬,他皺眉道:“你騙了那捕頭,如今又送請柬去,可曾想過,若請不來這五位,該如何收場?”
“景副幫主不用擔心。”蕭玉琢漫不經心的看了他一眼,“我定能請來的。”
“呵,好生自信。”景延年說著,又往邊走了幾步,想要看看那請柬上,是不是藏了什麼端倪。
蕭玉琢也不遮掩,任憑他打量。
景延年細看,不由皺眉。
只是普普通通的請柬呀,不過是華麗些,又熏了香,顯得更為鄭重,一手小楷極為漂亮。
別的,就沒有什麼不同了呀?
“就靠著這一張薄薄的請柬,你以為,就能請來這五位評委?”景延年哼笑。
蕭玉琢擱下筆,抬頭看著景延年,姣的臉上含著淡淡笑意,“不如這樣,景副幫主就坐在這兒,咱們都等著,若是回話的人來說,我要請的人,同意出席評委,那就算景副幫主你輸!”
景延年瞇眼,饒有興味的看著。
“若是有一位不來,就算我輸,怎樣?”蕭玉琢挑著眉梢。
一臉生的笑意,像是冬日里最為難得的暖,忽而就照在了他的心頭上。
他著他的臉頰,著明的笑容,一時間心頭像是被人拿著一把小錘子,當當當的敲著,要把他的整個心都敲開了。
“輸了怎樣?贏了又怎樣?”景延年沉聲問道。
蕭玉琢垂眸想了想,“若是你贏了,我就把煙雨樓還,從此不再手煙雨樓的事兒。”
景延年微微一愣。
這些時間整日相,在煙雨樓上花費了多功夫,他是親眼所見的。
很用心的想做好煙雨樓。
而且就像當初在關三爺面前承諾的那樣,煙雨樓到了的手里,和當初的院已經完全不一樣了。
不但為關三爺整到了比原來多得多的錢財,而且煙雨樓的們也過上了比原來更好的生活。
甚至為們贏來了人們的褒獎尊重,為們贏得了曾經難以想見的社會地位。
好些紅倌兒因為舉辦的活,都不在以賣弄為生……
現在竟愿意提出放手煙雨樓?
景延年謹慎的看著,“倘若你贏了,你想要什麼?”
蕭玉琢收斂笑意,面嚴肅,“我要你承認,人不是男人的附屬,我即便嫁你為妻,也不必依附你,事事聽從你,委曲求全。”
景延年聞言一怔,這條件倒是他不曾想到。
“我原以為,你會借機我把重午還給你。”
蕭玉琢笑了笑,“我是重午的母親,即便你讓我們母子分離,也改變不了這樣的事實。這件事,我本不用提條件,也不必跟你商議。”
景延年沉著臉,抿沒做聲。
“怎樣?這條件你敢不敢應?”蕭玉琢笑問道。
景延年輕哼一聲,“應就應,這我有何不敢?”
蕭玉琢點頭而笑,“好,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你可別出爾反爾啊?”
景延年表不屑,“斷然丟不起這個臉面。”
“別到時候你承認,你卻口是心非,心里不愿才好。”蕭玉琢說完,了竹香上前。
竹香連忙附耳過來。
蕭玉琢將五份請柬在手中,又在耳邊細細叮囑一番。
竹香眼中一亮,連連點頭,當即帶著請柬告退出去。
“你又代了什麼?”景延年好奇問道。
蕭玉琢輕哼一聲,“等著結果就是。”
接下來的時,蕭玉琢安靜的翻看著賬冊。
自從看們給佳麗打賞投票以來,活的收就翻倍的往上漲。
隨著佳麗們的人氣越來越高,看們出手也越來越闊綽了。
蕭玉琢算得認真。
景延年安靜的坐在一旁,看著的側臉,也看的認真。
像個謎團一樣,讓人越想深究,就越是看不清。
可越是看不清,就好似越人著迷。
他不喜歡失控的覺,他想把看的徹徹的。
壺里的水,滴答滴答的往下。
時間靜靜的在兩人之間流淌。
竹香照著蕭玉琢的吩咐,將請柬分派給五個人,并這五個人同時出發,前往五位要請的評委家中。
并且每個前去送請柬的人暗示,其他四位已經答應出任評委了。
猜你喜歡
-
完結4255 章
神醫鳳後
她,21世紀王牌特工,被家族遺棄的天才少女;他,傲嬌腹黑帝國太子,一怒天下變的至高王者;她扮豬吃虎坑他、虐他、刺激他、每次撩完就跑。是個男人就忍不了!他隻能獵捕她,寵溺她,誘惑她為他傾心,誰知先動心的人卻變成了他。——君臨天下的少年,鳳舞江山的少女,一場棋逢對手,勢均力敵的愛情追逐遊戲。
377.2萬字7.67 327610 -
完結20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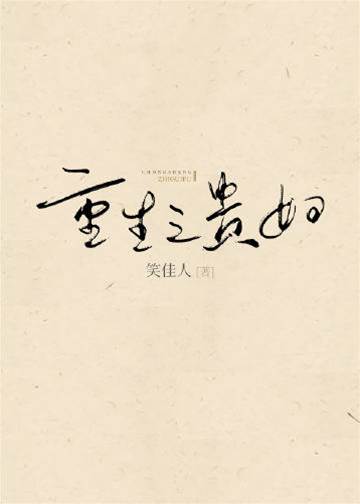
重生之貴婦
人人都夸殷蕙是貴婦命,殷蕙也的確嫁進燕王府,成了一位皇孫媳。只是她的夫君早出晚歸,很少會與她說句貼心話。殷蕙使出渾身解數想焐熱他的心,最后他帶回一個寡婦表妹,想照顧人家。殷蕙:沒門!夫君:先睡吧,明早再說。…
66.6萬字8.71 195765 -
完結74 章

屠戶家的美嬌娘
年方二八的小娘子賀婉瑜長的膚白貌美,一雙瀲灩的杏眼更是勾的人心神蕩漾。 媒婆來說媒:城東有個後生今年二十,家裡有餘錢。 賀婉瑜羞答答:做啥的? 媒婆:殺豬匠。 賀婉瑜瞪大眼,腦補了一張肥頭大耳,身寬體胖,手握大刀砍豬的渾人形象,然後翻個白眼暈倒了。 城東殺豬匠許秋白聽說自己嚇暈了美嬌娘,默默的收好刀帶上聘禮親自上門了..... 小劇場: 媒婆:喜歡殺豬的哪兒? 賀婉瑜羞答答:我就喜歡殺豬的,身體好,勇敢有力氣,再也不怕別人欺負我。最重要的就是長的好。 被誇勇敢力氣大的許秋白默默的看了眼自己的胳膊點點頭:是的,他力氣大,也很勇敢,但他其實想說的是他會疼娘子愛娘子,不讓娘子受一丁點委屈。然後又摸摸自己的臉心道:多虧他這張臉還能看啊。
24.2萬字8 15945 -
完結289 章

美人酥軟
大將軍只喜歡他的劍,不喜歡女人。 老夫人擔心兒子身有隱疾,自作主張,給兒子房裏塞了一個人。 將軍征戰歸來,就多了一個小通房,豐肌豔骨、媚眼桃腮,一看就不是正經姑娘。 —— 小宮女阿檀生性膽小害羞,只因容貌妖嬈,被當作玩物賜給了將軍。 將軍其人,冷面冷心、鐵血鐵腕,世人畏其如修羅。 阿檀嚇得要命,戰戰兢兢地討好將軍:“奴婢伺候您更衣,奴婢很能幹的。” 一不小心,把將軍的腰帶扯了下來。 這婢子一來就解他的戰袍,果然不正經。 將軍沉下了臉。 —— 日子久了,將軍想,小通房雖然不正經,但是對他百般愛慕,他很受用。 他時常欺負她,看她紅着臉、淚汪汪的模樣,偶爾還會覺得,這個女人或許和他的劍差不多重要。 直到有一天,皇帝要給將軍賜婚,將軍前腳拒了婚,後腳回到將軍府…… 他的阿檀呢? 她跑了,不要他了! 將軍赤紅着眼,折斷了他的劍。 —— 武安侯傅家被抱錯的嫡女回來了。 衆人嘆息,可憐美人絕色,卻在外流落多年,還生了孩子,此生討不得好姻緣了。 誰知道,在那日賞花宴上,京城最出色的兩個兒郎,大將軍和崔少卿拔劍相向,爭着給傅娘子的孩子當爹。 *帶球跑的火葬場,十分正經的笨蛋美人和假裝正經的傲嬌將軍*
45.8萬字8.25 3755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