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公深不可測》 第52章 寒酸得可笑的履歷
孟若男眼準毒辣,手下培養出的藝人,現在都是能獨當一面的風云人。然而要求極其嚴苛,公事公辦到了不講面的地步。
不管你咖位如何,后臺多,孟士都不放在眼里,甚至連幾大電影節滿貫影后,出豪門,嫁世家的黎詠詩也被罵哭過。
孟若男已經淡出圈外足足兩年,因為上一位苦心捧紅的藝人和丈夫暗通款曲。這些年收雖然厚,卻全部投給前夫的公司,然而那對男早就合謀轉移了財產。
遭遇雙重背叛,又損失全部積蓄,心俱碎,退圈調整心。然而據知人說,原本只是冷如鐵,現在這塊鐵已經被生活捶打了一柄鋒利的刀,讓人更加不敢靠近。
白微微不知道凌君昊是怎麼說服再次出山的,不過這種曾經拍戲不勤,如今又靠著金主空降的人,是孟士深惡痛絕的類型。
Advertisement
雖然隔著一扇門,依然覺得脖子涼颼颼的,仿佛孟士這柄鋼刀已經在刮的嚨。
深深吸了口氣,抬手輕輕敲門,兩秒后,里面傳來微微沙啞的聲:“請進。”
白微微推門進去,先鞠了個躬:“若男姐你好,我是白微微,今后請你多關照。”
孟若男抬起眼皮,目從的頭頂開始,一寸一寸的慢慢往下打量。
黑緞子一般的長發束簡單的馬尾,順的垂在腦后,每一縷劉海都被梳上去,出潔飽滿的額頭,臉上不施脂,周除了一對小小的鉆石耳釘之外,沒有任何首飾,衫也是最簡單的無袖及膝。
打扮得格外素凈,卻讓人移不開視線,仿佛有淡淡的芒從深散發出來。
凌君昊沒有夸大其詞,這個孩,注定為人群中的焦點。
只是那寒酸得可笑的履歷……孟若男譏諷的揚了揚角,直截了當的說:“白小姐自條件確實出類拔萃,肯砸資源的話,靠炒作值就能躋一線小花。不過我絕對不帶華而不實的藝人,白小姐若是只想快速走紅,像現在那些流量明星一樣吸金賺快錢,那就只能請你另尋高明,畢竟有君在,大把的經紀人搶著想帶你。我們道不同不相為謀,就不要互相浪費時間了。”
白微微把的鄙夷收進眼底,前世經歷過無數冷眼和嘲諷,孟士這點不滿就像雨一樣,甚至無法激起的緒波。沉聲答道:“我想當個好演員,然后才是風的明星。”
孟若男嗤了一聲,抖了抖手上的履歷表:“白小姐的演藝經歷實在蒼白,并不像有志于此的人。”
印滿黑字的白紙被一團,丟進了垃圾桶里:“我不想聽你解釋。既然我答應了君,機會我會給你,但只有一次。后天你就正式進組,那點戲份,拍完全程也花不了多時間,足夠我看清楚你究竟是被埋沒的璞玉,還是扶不上墻的爛泥。這是我的聯系方式,劇組見。”
一張名片留在了桌上,孟若男徑直起,頭也不回的離去。
猜你喜歡
-
完結890 章

蛇仙相公慢慢來
一場重病,讓我懷胎十月,孩子他爹是條蛇:東北出馬仙,一個女弟馬的真實故事……
202.3萬字7.67 80747 -
完結834 章

寵婚蜜愛:傅先生他又想娶我了!
結婚兩年,兩人卻一直形同陌路。他說:「一年後,你如果沒能懷孕,也不能讓我心甘情願的和你生孩子,那好聚好散。」她心灰意冷,一紙離婚協議欲將結束時,他卻霸佔著她不肯放手了!!
77.3萬字8 94329 -
完結267 章

被渣後小叔叔寵我入骨
那一夜,淩三爺失身給神秘的女人,她隻留下兩塊五和一根蔫黃瓜,從此杳無音訊……被養母安排跟普信男相親的栗小寒,被一個又野又颯的帥哥英雄救美,最妙的是,他還是前男友的小叔叔。想到渣男賤女發現自己成了他們小嬸嬸時的表情,她興高采烈的進了民政局。結果領證之後,男人現出霸道本性,夜夜煎炒烹炸,讓她腰酸腿軟,直呼吃不消!
73.5萬字8 32067 -
完結183 章

成蝶
分手多年後,路汐沒想到還能遇見容伽禮,直到因爲一次電影邀約,她意外回到了當年的島嶼,竟與他重逢。 男人一身西裝冷到極致,依舊高高在上,如神明淡睨凡塵,觸及到她的眼神,陌生至極。 路汐抿了抿脣,垂眼與他擦肩而過。 下一秒,容伽禮突然當衆喊她名字:“路汐” 全場愣住了。 有好事者問:“兩位認識” 路汐正想說不認識,卻聽容伽禮漫不經心回:“拋棄我的前女友。” - 所有人都以爲容伽禮這樣站在權貴圈頂端的大佬,對舊日情人定然不會再回頭看一眼。 路汐也這麼以爲,將心思藏得嚴嚴實實,不敢肖想他分毫。 直到圈內人無意中爆出,從不對外開放的私人珠寶展,今年佔據最中央的是一頂精緻又瑰麗的蝴蝶星雲皇冠。 據傳出自商界大佬容伽禮之手,於他意義非凡。 好友調侃地問:“這麼珍貴的東西,有主人了嗎?” 容伽禮不置可否。 殊不知。 在路汐拿到影后獎盃當晚,滿廳賓客都在爲她慶祝時,她卻被抓住,抵在無人知曉的黑暗角落處。 路汐無處可躲,終於忍不住問:“容伽禮,你究竟想幹什麼?” 容伽禮似笑非笑,語調暗含警告:“你以爲……回來了還能輕易躲得掉?” 路汐錯愕間,下一秒,男人卻將親手設計的皇冠從容的戴在路汐發間,在她耳畔呢喃:“你是唯一的主人。” ——在廣袤的宇宙空間,蝴蝶星雲終將走到生命盡頭,而我給你的一切,比宇宙璀璨,亙古不散。
27.2萬字8.18 5293 -
完結20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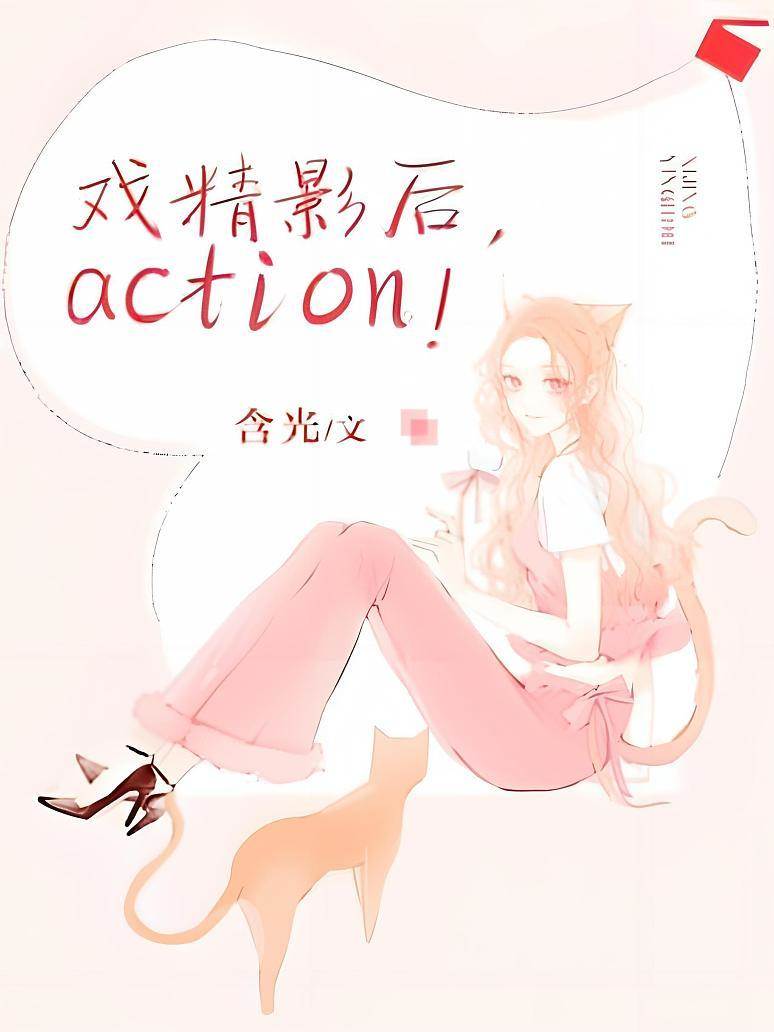
戲精影后,action!
影后楚瑤瑤被人害死一命嗚呼,醒來后已經是20年后,她成了臭名昭著的十八線女明星。 渣男渣女要封殺她?小助理要踩她上位?家里重男輕女要吸干她?網友組團來黑她? 最可怕的是身材走樣,面目全非! 影后手握星際紅包群,這些全都不是問題。星際娛樂圈大佬們天天發紅包,作為影后迷弟迷妹只求影后指導演技。 第一步減肥變美。 第二步演戲走紅。 第三步虐渣打臉。 第四步談個戀愛也不錯……隔壁的影帝,考不考慮談個戀愛?
40.3萬字8 19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