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驚悚世界當商人》 第20章白須道士
夢?
我從床上坐起,上還套著服。
我用力捶了捶腦袋,終於回想起來了,我昨天從商業街回來後,是合睡下的。
再看看牆上的掛表,已經是下午一點了,我睡了一天一夜。
一天沒吃東西,我肚子咕咕的個不停,我在廚房裏找到一盒泡麵,水是前天燒開的,溫熱,我懶得重新燒,直接倒進麵盒裏。
泡麵的功夫,我把自己的服收拾了一下,我才來了幾天,沒添置幾件行頭,簡簡單單打個包就行。
我想找個紙筆,留幾句話給表哥,雖然他壞心眼害了我,但好聚好散,總不能一走了之。
我的房間裏有筆沒紙,我推開表哥臥室的門,看看能不能找個本子撕一張。
這是我第一次來表哥臥室,屋子簡單的,一張床,兩個床頭櫃,外加一個櫥就沒別的了。
表哥實在邋遢,走之前被子沒疊,扭在一起全是褶子。
Advertisement
找了一圈,他屋裏也沒紙,我剛準備離開,忽然聞到一花香。
玫瑰花的味道。
一個大男人的臥室,沒有子發酵的味道就不錯了,怎麽會有玫瑰的香味?
聞著這玫瑰香,我有一種悉的覺。
我怔住了,難道不是夢?
就在這時,我忽然聽到客廳的門,傳來開鎖的靜。
這個房子,隻有我和表哥有鑰匙。
我走到客廳,剛好看到門被推開,出表哥的臉。
兩日不見,表哥滄桑了許多,他的下爬滿了胡茬,發紫,挑起不死皮。
表哥也看到了我,他有些意外,還有些不高興。
“小懸,都這個點了,你還沒去茶樓?”
他這語氣,像極了老板訓斥懶不幹活的員工。
見他這個模樣,我也惱了,正是因為他讓我做的那些事,害得我前天夜裏差點沒了命。
我把桌子上打好的包扛在肩上,泡好的麵也不吃了,推開表哥往外走。
“我不幹了!”
誰知我一頭撞上了一個人,像是撞上一堵牆,不自覺的後退了兩步。
我這才發現,表哥後,還有一個人。
這人個頭和我差不多高,有些消瘦,也不知道怎麽把我給撞回來的。
他穿著一白練功服,黑布鞋,和清晨公園打太極的老爺爺們,一個裝束。
這是個道士,我能認出來,倒不是因為他手裏攥著拂塵,或著有仙風道骨的氣質。
而是他的頭上用布條綁了發髻,還著一支黑的木簪。
我爹娘都信神仙,他們帶我去過道觀,道觀裏的道士,頭上紮著混元髻,和這人一模一樣。
眼前的道士六十多歲,臉上有不皺紋,惹人注目的是他明明有一頭青,胡須卻是白的。
表哥手抓住我的肩膀:“小懸,你為什麽不幹了,是不是那三個混混欺負你了?”
看著表哥一臉憤怒的模樣,我更生氣了,還裝。
我剛想開口罵他,白須道士忽然手拽住我上後領,往下一扯,把我肩膀了出來。
他手指過牙印子,疼的我呲牙咧。
白須道士臉凝重:“鬼印子。”
猜你喜歡
-
完結4300 章

茅山鬼王
最火爆手有羅盤判陰陽,一把法劍定乾坤。 葛羽,三歲修道,少年大成,會抓鬼、會治病、會看相、會算命,會占卜,最重要的還是會摸骨…… 身負洪荒,天賦異稟,玄學五術,樣樣精通。 二十出山,斬妖邪,滅尸煞,斗惡鬼,殺魔頭!
780.8萬字8 239742 -
連載888 章
我家老婆有點兇
人人都知凌呈羡对任苒有着病态的占有欲,他荒唐到能在婚礼上故意缺席,让她受尽耻笑,却也能深情到拒绝一切诱惑,非她不可。“任苒,往我心上一刀一刀割的滋味怎么样?”“很痛快,但远远不够。”她现在终于可以将那句话原封不动的还给他,“我不像她,也不是她……”
150.3萬字8 5437 -
連載83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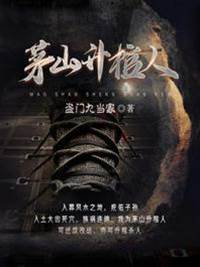
茅山升棺人
我從一出生,就被人暗中陷害,讓我母親提前分娩,更改了我的生辰八字,八字刑克父母命,父母在我出生的同一天,雙雙過世,但暗中之人還想要將我趕盡殺絕,無路可逃的我,最終成為一名茅山升棺人!升棺,乃為遷墳,人之死后,應葬于風水之地,庇佑子孫,但也有其先人葬于兇惡之地,給子孫后代帶來了無盡的災禍,從而有人升棺人這個職業。
153萬字8 952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