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念桃花》 二百七十八、夏至(三十八)
晚云趕將外面的裳褪去,出里頭致的式宮裝,而后摘下頭上的黑紗方帽,出個式發髻。
從袋里掏出玉簪簪上,上方才在院子里隨手折下的花,一打扮儼然換了個模樣。
初時,聽裴安詳細吩咐如何行事,曾困地問:“殿下手下想必人才濟濟,為何要我去做此事?”
裴安徐徐道:“我你去自然有我的道理。此人非你莫屬。”
原來是這個意思。晚云搖搖頭,不過就是要在男間切換。如此說來,裴安手下也不見得有多能干的人,連個細作也找不到。
而后,便是最重要一步。
六部是軍政重地,若非高位者,進出皆要搜。若是臉的隨便搜搜,更何況是這樣面生的子。
而這就是關鍵。六部是不得讓子進的。
除了一類人,那便是被六部長帶進來的家眷。
護門看前來,困問:“娘子是如何進來的?”
晚云并不做聲,遞上玉牌。
護門了悟道:“是四殿下府上的人。”
晚云頷首:“奴婢是隨四殿下馬車進來的,所以未與長招呼。”
“哦,怎不等殿下一道回去?”
晚云垂眸道:“殿下新得了字畫,讓奴婢送回府上讓王妃鑒賞。”
Advertisement
護門頷首笑道:“嘗聞殿下與王妃鶼鰈深,果真如此。”
他將玉牌還給晚云,正要放行,忽而看見了什麼,深深一禮,道:“恭迎四殿下!”
晚云心頭一驚,回頭看去,正見一個修長的影,飾堂皇,正往這邊走來。
一切突如其來。
晚云的腦子霎時一片空白。
四皇子裴珩是裴安一母同胞的弟弟。方才出示的玉佩,是從裴安那里得來的,想必是裴珩給裴安的信,讓以防萬一。沒想到說曹曹到。
現在溜走還來得及,要跑麼?一個念頭浮起,心里打起鼓來。
“殿下來了,莫非他還是決定親自回去送畫?”護門對晚云道。
晚云干笑兩聲,著頭皮,轉過去。
沒見過裴珩不假,但所幸的是,裴珩也不曾見過。
“拜見四殿下。”笑盈盈地向裴珩一禮。
裴珩看了看,“嗯”一聲。
晚云原想著裴珩這等大人,見到個侍婢之類的人行禮,大約多看一眼都懶得,更不會有什麼閑心去問他們在做什麼,只要說兩句好聽的話,蒙混不過不滿。
不料,那護門竟一心想要討好裴珩,上前拱手,熱心地說:“這位娘子方才還說要回去給王妃送畫,不想殿下就來了,可要去為殿下備馬?”
晚云心中暗道不好。
“畫?”裴珩不明所以,“什麼畫?”
晚云暗罵護門多管閑事,索搶先一步上前,展開手中的玉符,道:“殿下忘記了?這畫原本是二殿下的,還是殿下讓奴婢拿這玉符去二殿下那里取畫。奴婢早前問,如此貴重的畫,二殿下怎會給奴婢,殿下說二殿下一看便知。果然,二殿下看了之后,便答應了。”
頻頻提及二殿下,恨不得把我是二殿下的人幾個字寫在臉上。
如所愿,裴珩認得這玉符,目閃了閃。
他看了晚云一眼,似在打量,頃,點點頭,道:“差點忘了,你隨我出去。”
*
六部的署,一連著一,雖然吏進進出出絡繹不絕,卻頗是肅穆,讓人連走路也不敢大聲。
一直走到偏僻無人的地方,裴珩才停下步子。
他出手,面無表地看著晚云。
晚云遞上玉符。
裴珩收了,卻出另一手,示意出懷里的卷宗。
晚云有些躊躇:“這……”
“我總要知道你從六部這里走了什麼。”裴珩道,“與我看。”
什麼?晚云隨即低聲駁道:“是二殿下讓我這麼做的。”
裴珩不置可否,依舊攤著手。
什麼執拗子。晚云只得將卷宗呈上。
裴珩展開卷宗,飛速掃了一眼,又卷回去遞給,問:“你是皇城司的人?”
晚云接過卷宗,含糊其辭:“奴婢為二殿下辦事。”
裴珩看了看,沒有多問,轉離去。
晚云在他后,忙道:“殿下,那玉……”
裴珩頭也不回地地說:“二兄自會來找我要。”未幾,影已經消失在了回廊的轉角。
晚云撇撇角。裴淵這幾個兄弟,脾氣是一個比一個怪。
幸好這以后,晚云順風順水,再不曾遇到什麼阻礙。
鄭有致在六部的署外等著晚云。
看到晚云的扮相,他愣了愣,恭維道:“郎君果真妙人,辦子也毫不含糊。”
晚云干笑兩聲,道:“謬贊。”
出皇城路上,晚云和鄭有致打探起四殿下裴珩。
鄭有致笑道:“郎君不識四殿下?小人還以為皇城司的人無所不知。”
晚云道:“萬事總有例外。”
鄭有致也不含糊,道:“四殿下封號壽王,是肖貴妃之子,是二殿下的胞弟,如今執掌工部將作監。”
“將作監?”晚云問:“那不就是個造房子的地方?”
鄭有致笑道:“這話,若是將作監的人聽到,定然要暴跳,可他們確實就是干這個的。聽聞四殿下自小聰慧,很得圣上喜,人人都說四殿下前途無量。可偏偏殿下不喜舞文弄墨,也不揮刀弄槍,就愿意在工地上敲敲打打,研究廟宇樓閣。圣上起初還想讓他當工部尚書,可他又不稀罕坐值房,指明了要去將作監修房子。圣上無法,便應了。”
嘖嘖,果真執拗。晚云心道,不過這興趣倒也別致。
目前知道的幾位皇子,要麼如太子,安然穩坐權力的頂端;要麼如裴淵和裴瑾,為封疆大吏;要麼如裴安,上躥下跳地當條弄江龍;要麼就像裴律,一事無,四溜達,但甘心當個手藝人的,別說是個皇子,就是個七品小子弟,恐怕也放不下段去做。
“原來如此。”晚云頷首,“方才我遇到了四殿下,聽他說了幾句話,覺不好相與。”
鄭有致道:“確實,眾多皇子之中,有兩位是出了名的難相與,其中一位,就是四殿下。”
“哦?”晚云訝道,“另一位是誰。”
猜你喜歡
-
完結1250 章

法醫王妃:我給王爺養包子
坊間傳聞,攝政王他殺人不眨眼,吃人不吐骨頭,所到之處,寸草不生。 蘇七不過是從亂葬崗“詐屍”後,誤惹了他,從此他兒子天天喊著她做孃親。 她憑藉一把柳葉刀,查案驗屍,混得風聲水起,惹來爛桃花不斷。 他打翻醋罈子,當街把她堵住,霸道開口:“不準對彆的男人笑,兒子也不行!”
216.9萬字8.18 52483 -
完結2007 章

神醫狂妃:娘親你馬甲又掉了!
大齊國的人都以為瑾王妃只是個寡婦,瑾王府也任人可欺。可有一天,他們發現——神醫門的門主喊她老祖宗。天下第一的醫館是她開的。遍布全世界的酒樓也是她的。讓各國皇帝都畏懼的勢力是她的外祖家。就連傳說中身亡的夜瑾居然都回來了,更是將她疼之入骨,寵入…
181.2萬字8 94733 -
完結7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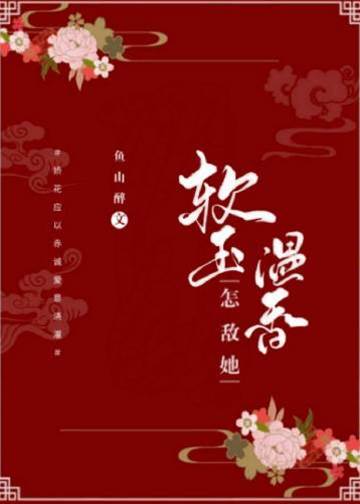
怎敵她軟玉溫香
提起喬沅,上京諸人無不羨慕她的好命。出生鐘鳴鼎食之家,才貌都是拔尖兒,嫁的男人是大霽最有權勢的侯爺,眼見一輩子都要在錦繡窩里打滾。喬沅也是這麼認為的,直到她做了個夢。夢里她被下降頭似的愛上了一個野男人,拋夫棄子,為他洗手作羹湯,結果還被拋棄…
21.9萬字8 11801 -
連載2178 章

替姐出嫁後,錦鯉農女逆襲了
荒年,任家一車糧食就將宋九換走,成了任家傻兒子的媳婦,都說傻子兇狠殘暴還咬人,咬一口就得病幾日,世人卻不知,傻夫有三好:相貌好、身材好、體力更好。 錦鯉體質的宋九,嫁到任家就成了團寵,好事一樁連一樁,任家生活也越過越好。 隻是她這個傻夫身份卻變得不簡單,親生父母來相認,爹不疼娘不愛?沒關係,宋九護短疼丈夫。鬥極品虐渣渣,帶著傻夫發家致富,誰也別想欺負他。 宋九:“榮長隻有我能欺負。” 任榮長:“隻有媳婦能欺負我,其他人都不準欺負我媳婦。”
404.1萬字8.33 47784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