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舌王爺傲嬌妃/日日思君君不見》 第6節
大殿下。
彥卿想起來,上次這姑娘就跟說什麽大殿下大皇子之類的來著。
等了半天,半夏沒再說話,彥卿忍不住問,“然後呢?”
他來了有我什麽事啊?
半夏蹙著眉抬頭看向彥卿,那表可以代表一句話。
你連這個都不知道?
好吧,就當我知道。
一個人突然跑到自己麵前傳話說,有一個什麽什麽人來了,那八是在說,有個人要見自己。
大皇子。
記得南宮信是三皇子,那大皇子就是他大哥。
彥卿一時猜不到這人找自己能有什麽事。
“我知道了,我梳洗一下就去。”彥卿做出一副漫不經心的樣子,“綺兒過來幫我更。”
“是,娘娘。”
在綺兒伺候更梳洗的時候,彥卿連哄帶嚇地問清楚了。這大皇子南宮儀是皇帝的嫡長子,自己那當相爺的爹和他走得很近,和南宮儀的關係似乎也有些微妙,就是結婚後這一個月裏,南宮儀竟來找過兩三次,每次都是在這靜安殿後的花園。
會麵時隻有這兩人,沒人知道也沒人敢過問他們說過些什麽。
既然之前已經有過兩三回這種見麵了,那就說明沒什麽好怕的。
七分疑三分好奇,彥卿就這麽去了。
到底是王府花園,湖山濃於方寸之地,亭臺樓閣相呼相應,一步一景,無可挑剔。
好在彥卿還記得自己不是來逛園子的,所以乍看到九曲橋上站著個人時沒覺得多麽意外。
看個側影就覺到這男人和他弟弟完全是兩類貨。
雖然這麽看著不會比南宮信高多,但形比南宮信健碩得多,遠遠看起來沉穩如山,還帶著清晰的皇族員上特有的那種戾氣。
這爺們兒絕對不會比他弟弟好對付。
對南宮儀做了初步判斷,彥卿才小心地走上了前去。
Advertisement
“你是想幹什麽?”
彥卿剛走近前去,還沒看清這男人的臉,就被沉沉地質問了一句。
你倆還真是一個爹生的!
“我幹什麽了?”
被彥卿這一句頂過去,南宮儀轉過了來,鎖眉頭盯著彥卿。
這男人的目深重得像刀一樣,好像南宮信缺失的目全都補到他這裏來了。
“幹什麽了?你和南宮信,昨晚是怎麽回事?”
彥卿愣了一下才反應過來,他說的大概是和南宮信同房的事。
“就是夫妻倆那回事唄。”跟你沒什麽關係吧。
南宮儀劍眉鎖得更了,“還有,你召賀仲子是怎麽回事?”
賀仲子?不認得。“不用你管。”
南宮儀微瞇著眼睛像是要把彥卿看穿一樣,“你既然什麽都有主張,都做到這一步了,那東西也找到了吧?”
東西?
不行,對這男人了解得還太,現在還不能讓他覺有什麽不對。
“還沒有。”彥卿又補了一句,“但應該就快了。”
看著南宮儀皺的眉心略鬆了些,彥卿才在心裏舒出半口氣。
看來蒙到點子上了。
“你沒忘就好。”南宮儀向前邁了一步,和彥卿之間隻剩了一拳的距離,微低下頭,低了聲音輕輕在耳邊吐出一句話,“老三那子讓你失了吧。”
說罷繞過彥卿,大笑著走了。
留下彥卿站在原地,好一陣才在剛才短暫卻分明到危險重生的鋒中回過神來,深深吐出一口氣,腦子裏就剩下一句話了。
我|你南宮家八輩祖宗!
☆、好歹是什麽
打從花園回來,彥卿就一直在想南宮儀說的那幾句話。之前以為這的舊主和南宮信之間可能是有些兒長的糾葛,但反複琢磨著南宮儀說的那些讓半懂不懂的話,好像又沒有想象的那麽簡單。
為南宮信的王妃,似乎與南宮儀有著千萬縷的關係。
南宮信新婚分居,好像不全是南宮信自己的意思。
在這王府裏,還有個找什麽東西的目的。
總結下來,那就是一句話。
跟南宮信不是一夥的,跟南宮儀才是一路人。
這的舊主到底在搞什麽幺蛾子!
一堆疑問,就隻有一點是肯定的。
比起自己老公,這的舊主更待見自己的大伯哥!
想到這個,彥卿直覺得腦仁發疼。
就沒有個化學方程式能解釋解釋這些人之間的反應原理嗎……
一天沒喝咖啡,昨晚又被南宮信那麽一折騰,現在知道一切有驚無險,腦子裏雖然還攪著一團漿糊,但往床上一躺沒多會兒就睡著了。
睡得很沉,醒來時隻記得夢裏有一片白。
那個人上的那種白。
彥卿從床上爬起來,握起拳頭砸了砸自己的腦門兒。
這是在想什麽呢……
看看屋裏昏昏暗暗的,已經是晚上了,不知道什麽時候已經有丫鬟進來把燈燭挑亮了。
一覺睡到現在,晚上隨便你怎麽折騰,我神神地奉陪到底。
吃晚飯,閑逛,沐浴,雖然知道那人橫豎是看不見的,彥卿還是好好拾掇了一下自己。
連穿沒穿服都能聽出來,誰知道他是不是還能聽出來點兒別的什麽。
正盤算著在這沒有電視沒有電腦沒有pad沒有手機還沒有學業沒有工作的鬼地方要怎麽消磨時間,想到這個,腦子裏突然冒出個疑問。\思\兔\網\文\檔\共\\與\在\線\閱\讀\
南宮信在忙什麽?
第一回見他的時候他就在說自己很忙,今天一大早出去,到現在也沒見人影。
家事國事天下事,有什麽事還非得讓他這個份尊貴羸弱的瞎子來做不可?
難不這爺們兒是在躲著?
來綺兒,不管怎麽問,這姑娘來來回回都還是那麽一句。
殿下在理公務。
“綺兒,”彥卿沉下臉來,“我不記得我以前是什麽脾氣,但我現在告訴你,我最容不得的就是別人跟我撒謊。”
綺兒一驚,“嗵”地跪了下來,“娘娘明察,奴婢不敢有半句虛言啊!”
“全國上下能用的人都死了?有什麽公務非要他一個瞎子從早忙到晚啊?是他皇帝腦子泡福爾馬林了,還是你連編個謊話都編不順溜啊?”
綺兒雖然聽不懂那個“福爾馬林”是什麽東西,但聽這一路上揚的語調也知道那不是什麽好話。
綺兒埋著頭,惶恐地回話,“娘娘,您不記得了……本朝所有皇子都要分理政務,皇上幾年前就把所有行軍打仗的事都給三殿下了啊。”
“行軍打仗?”
“是,娘娘。聽說因為近日臨邊諸國屢有犯境,殿下案頭戰報公文每日堆積如山,昨晚……昨晚怕是這大半月來殿下唯一一次徹夜安睡……”
彥卿愣了一愣,旋即笑著搖頭,“小姑娘,等我心好了一定係統地教教你該怎麽把謊扯得像真的一點兒。”
皇子分理朝政這個可以說得過去,仰仗外人不如鍛煉兒子嘛。
雖然說現在漸漸覺得南宮信不是個普通的瞎子,但要說南宮信憑這子骨去分管軍政,還能批閱戰報公文,這聽起來實在是忒扯淡了。
“娘娘,綺兒以命發誓,絕沒有欺瞞娘娘!”
彥卿牽著一抹笑,點點頭,“好啊,那就帶我去看看,咱們這王爺到底是忙了個什麽樣子。”
彥卿就這麽一說,沒想到綺兒還真就立馬站了起來,三更半夜把彥卿帶去了那繞來繞去的重華樓。
大老遠看著就燈火通明的。
皇帝腦子不會真了吧?
還是七拐八拐地上樓,彥卿毫無方向,隻是覺這回的走法和上次不大一樣。
到地方才反應過來,這來的不是臥室,是書房。
一個瞎子的書房。
裏麵有聲調嚴肅的說話聲,但聽得出來那聲音不是南宮信的。
沒人守門,從裏麵出來一個將軍模樣的人,手裏拿著幾本小冊子,在彥卿邊經過時隻匆忙向彥卿看了一眼,就行匆匆地離開了。
這人不是真的在批公文吧?!
綺兒說南宮信的書房一般仆從是不能進去的,彥卿就一個人走了進去。
偌大的一間書房,四麵牆中有兩麵都是書櫥,齊整地堆著滿滿的書。靠近一壁書櫥擺著一張碩大的檀木書案,正如綺兒說的,案麵上堆著兩三摞公文折子。
南宮信就坐在這張書案後,立侍案邊的江北正在把手中一份公文的容念給他聽。
彥卿進門的時候江北剛好念完那份戰報的最後一段,就看他把折子念完之後,攤開折子最後的空白麵放到南宮信麵前,南宮信準確無誤地在手邊筆架上拿起筆來,左手大概了一下折子頁麵的位置,之後毫不遲疑地落筆行文。
這一幕看得彥卿徹底沒脾氣了。
要說他生活自理能力強,那還是在彥卿的接範圍之的。但看到他和常人一樣,甚至比大部分常人還要幹脆利落地落筆寫字,彥卿瞬間覺得自己的世界觀都要被顛覆了。
彥卿走上前去,江北頷首向彥卿行了個禮,“娘娘。”
南宮信直到把手中這份折子寫完,放下了筆,才不冷不熱地對在他麵前站了有兩三分鍾的彥卿說,“你放心,我沒忘了夫妻的基本責任和義務。”
江北倒是夠機靈,聽到這話立馬會意地道,“殿下,卑職到外麵候著。”
彥卿已經能夠想象此時這半大小子在腦補些什麽了。
你是故意的吧……
江北出去,彥卿好歹說服自己要對眼前這個看起來疲憊得快要崩潰的男人好好說話,深呼吸了一下才張,“你這是在幹什麽?”
打心底裏還是難以相信皇帝會把軍政大事丟給這樣一個兒子。
南宮信輕蹙起眉來,“你想說什麽,直說,我很忙。”
還是那句冷冰冰的“我很忙”,但現在聽著一點兒惹人發火的覺都沒有。
事實擺在眼前,他就是很忙。
“你……”彥卿猶豫了一下,深呼吸,“你該歇會兒了。”
雖然彥卿自己都覺像是背錯臺詞了,但看著南宮信那副明顯就是在強撐的樣子,除了這句還真說不出來別的。
南宮信也聽得愣了一下,半晌,才又用慣常的語調不不慢地開口。
“裏麵就有張床,如果你著急的話。”
猜你喜歡
-
連載1884 章

帶著軍火庫到大明
秦牧穿了,帶著二戰軍火庫穿了!什麼?揚州被圍,陷落在即?老子有衝鋒槍!八旗騎兵滿萬不可敵?老子有重機槍!毅勇巴圖魯頭鐵?看我狙擊槍招待你!孔有德紅夷大炮厲害?看老子山炮野炮榴彈炮轟死你!倭寇趁火打劫?老子鐵甲艦登陸!看秦牧殺建奴,平流寇,滅貪官,掃倭寇,重整山河,再現華夏神威!畢竟老子有軍火庫金大腿,要當球長的男人!
341.1萬字8 45072 -
完結3129 章

上古強身術
一個帶著上古強身術和養生之道一系列輔助性的功法的人穿越到九州大陸,他是否能站在這世界的頂端,十二張美女圖代表這個世界的十二個最風華絕代的女子!
545.2萬字8 248855 -
完結770 章
重生都市之商海狂龍
他帶著滿腔虧欠重生。 攜步步先機,重登財富之巔! 誓要獨寵妻女,為其加冕無上榮耀。 奈何造化弄人,一腔愛恨,終是錯付。 從此后,龍如花海,總裁小姐,學霸校花,未出道明星甜心,一場場愛恨情仇。
146.9萬字8.18 39851 -
完結37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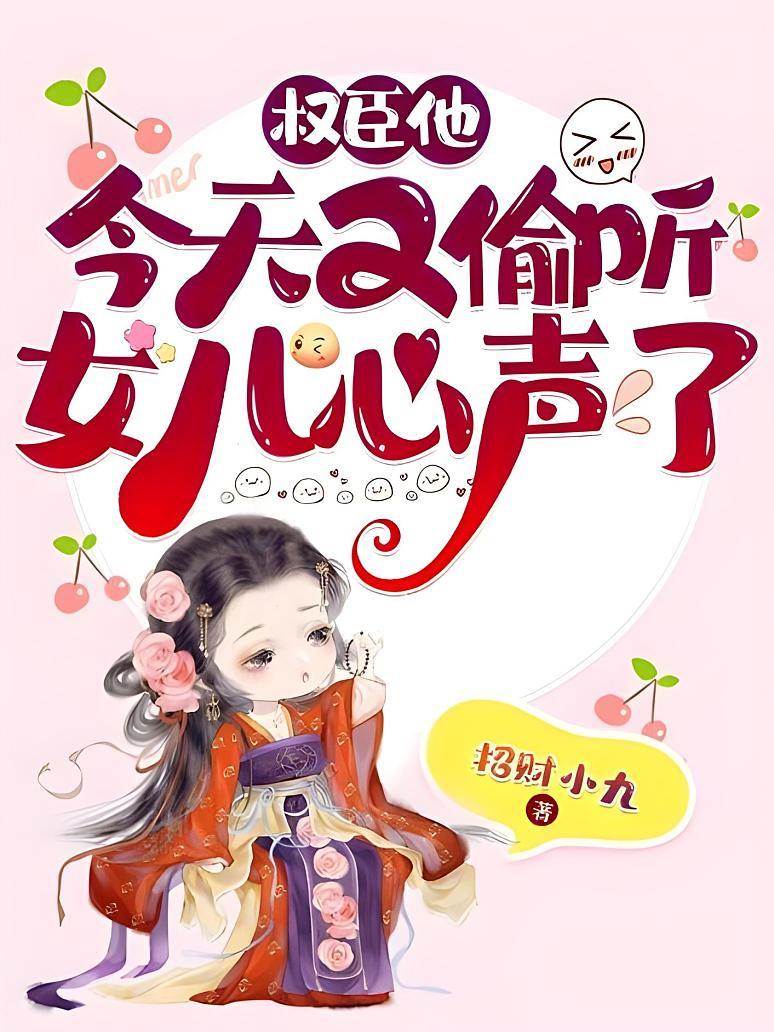
權臣他今天又偷聽女兒心聲了
樓茵茵本是一個天賦異稟的玄學大佬,誰知道倒霉催的被雷給劈了,再睜開眼,發現自己不僅穿書了,還特喵的穿成了一個剛出生的古代嬰兒! 還拿了給女主當墊腳石的炮灰劇本! 媽的!好想再死一死! 等等, 軟包子的美人娘親怎麼突然站起來了? 大奸臣爹爹你沒必要帶我去上班吧?真的沒必要! 還有我那幾位哥哥? 說好的調皮搗蛋做炮灰呢? 怎麼一個兩個的都開始發瘋圖強了? 樓茵茵心里犯嘀咕:不對勁,真的不對勁!我全家不會是重生的吧? 樓茵茵全家:重生是啥?茵茵寶貝又爆新詞兒了,快拿小本本記下來!
69.1萬字8.18 14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