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黜龍》 第9章 踉蹌行 (9)
第9章 踉蹌行 (9)
一場江湖佳話善始善終,就在幾十騎即將折上馬,準備趕一場夜路之時,李樞忽然扭頭,直接駐足於樹下,然後遠遠向東南面去。
“是靖安臺的錦巡組!”
片刻後,眼尖的徐世英也看出了端倪,然後依舊含笑。“錦出巡,其中必然有一個紅帶子巡檢坐鎮,一兩個黑帶子司檢或者副巡檢……李先生、雄大哥,咱們怎麼辦?”
“怕他作甚?!”
雄伯南負手而立,冷笑一聲。“紅帶子給我,小徐你對付黑帶子,咱們人多,淹了他們,斷不讓先生出事!”
“不必如此!”李樞瞥了一眼樹下牽著馬安坐回去的張行,運氣如常,平靜以對。“就這點人,不可能是衝著我來的,應該只是巧……做好準備,等他們來,若他們不生事咱們也不生事,可要是他們先手就不要怪我們了。”
雄、徐二人即刻點頭。
倒是張行,想起自己殺人的事,此時又聽到李樞辨析,略微猜到一二,不由微微皺眉,準備靜觀其變——真要是自己惹的事,也不讓人家白白累,但怕就怕遭殃的不是這邊,到時候又要承人家的了。
“巡檢!”
胡彥遠遠見河堤上人頭攢,有人佈陣相迎,便立即向側上司請示。“怕不是有二三十人、三四十匹馬,東境是東齊故地,歸於朝廷不過幾十年,素來人心不附,江湖豪客、地方豪強也皆素來不法,咱們人,要不要稍作避讓,小心應對?”
“迎上去看看。”
巡檢毫不猶豫就做出了決斷。“我們是靖安臺派出的錦巡組,專巡東境北六郡,如今在濟州領,有專斷之權,只有賊人避我們的道理,哪有我們避讓賊人的道理?”
Advertisement
胡彥當即不再多言,而是立即與白有思拉開馬距,後區區十來騎立即也立即默契分開,結一個倒人字形的陣型,然後馬速不減,臨到河堤百步的時候,才陡然勒馬,錦巡卒們也順勢輕馳馬匹向兩邊散開,在曠野中保持了半包圍的迫姿態。
隨即,白有思更是帶著胡彥、秦寶二人直接下馬,往堤上大樹走了過來。
“我等良民剛剛渡河,稍作歇息,準備趕路探親,不知靖安臺的大人們何故阻攔?”堤上樹下,徐世英滿臉帶笑,昂然出列,居高臨下來問。“國家權柄在大人們手裡就是這麼用的嗎?”
“是曹州徐大郎!”
秦寶一眼去,立即低頭,在白有思後低聲相告。“他家是曹州第一大地主,他父親……”
徐世英眼睛尖耳朵也尖,聽到這裡,直接再笑:“那不是登州的秦二郎嗎?上次登州武館一別不過半年,便投了靖安臺?怎麼沒給你一套錦啊?”
“秦公子是因公案暫時隨行。”已經走到堤上的白有思停下腳步,言語平靜,表不變。“至於曹州徐大郎,也是靖安臺掛著號的,他爹最喜歡裝老實,他最喜歡裝無賴,乃是曹州一等一的坐地虎……我此番奉命巡檢東境六郡,如何會不知道?”
徐世英將目落到對方臉上,然後又移到對方上的朱綬,終於微微變,但還是勉強笑對:“足下莫非就是吉安侯的那位千金?靖安臺中唯一一位朱綬巡檢?”
白有思不置可否,直接越過徐世英,負手持劍而立,的目掃過人羣,在格格不的張行上打了個圈後,最後居然落在了那位李樞李先生上。
“是思思嗎?”也就在這時,李樞忽然坦迎上上前,然後語出驚人。“我乃西京大興李樞,既是你家世,也是你父好友,猶然記得你三歲那年,你家將遷東都,在定春園中設宴,我還抱過你,等你十二歲拜三一正教從沖和道長習武時,我也恰好在場,不意今日背井離鄉,讓咱們叔侄道旁相逢……”
聽到對方名字時,其他人尚在茫然,唯獨副巡檢胡彥,原本一直在盯著雄伯南對峙,此時卻如了雷擊一般猛地轉向,而後更是全程死死盯住了李樞。
“見過世叔。”片刻後,白有思到底是平靜執劍一禮。“侄剛剛還以爲認錯了人,只是世叔不在西京安養,如何來到此?”
“來探親訪友。”李樞言語從容。
“世叔的親友也該是思思的親友,不知道是哪位?”白有思隨而上。
“思思誤會了。”李樞依舊坦然。“你也知道,我們西京李氏祖上是北荒遼地出……我此行是要往北荒訪問宗族脈,只是路途遙遠,我一個文弱書生,不堪旅途,所以先來這東境六郡找徐大郎他們這些豪傑,請他們護佑一二,然後方好出海北上,求個一路平安。”
“如此說來,倒是侄我孟浪了。”白有思若有所思,然後忽然問及了一個敏問題。“不過世叔,你此番行程,難道沒有在東都那裡被叛軍阻攔?”
“叛軍?”李樞狀若不解。
“不錯。”白有思盯著對方緩緩言道。“朝廷發二十萬銳再徵東夷,結果掌管全軍後勤的前上柱國楊慎忽然在汴梁謀逆,聯合鄭州、黎、東郡、淮、樑郡五州太守一起,前斷軍糧,後攻東都,雖然朝廷只花了二十七日便速速平定叛,可爲此事,前線幾乎全師而喪,而東都周邊三河腹地與更遠的淮上,總計十七郡俱遭兵……這麼大的事,世叔自西京過來,難道毫不知嗎?”
其餘人都還靜默無聲,正牽著馬看熱鬧的張行卻忽然表生了起來,繼而死死盯住了說話的二人。
“竟然有此事?”李樞立即就在馬上攤手,狀若慨。“我是從晉轉紅山過來的,委實不知。”
“原來如此。”白有思點點頭,圖窮匕見。“那世叔必然也不知道,楊慎起事後曾假世叔之名,對外宣揚你是他帳下謀主……並在被擒後對家父說,恨不從世叔之策,專心向東,以手中糧草和其父生前軍中威名爲籌,輕易收攏前線二十萬銳,然後據東境、中原三十郡,再取河北二十郡,彼時人心搖,則天下輕易可圖,反而被東都與陛下迷了眼。”
話到此,似乎雙方再無迴轉餘地,雄伯南與胡彥各自手按住了腰中兵,雙方隨從也各自張,倒是徐世英雖然年輕,卻依舊含笑自若,四下張,跟個長不大的孩子一樣,等他一不留神看到了冷冷看向此的張行時,還乾笑了一下。
“楊慎這個人,我只以爲他厲膽薄、好謀斷,卻不料還有這份小人心腸,臨死都要挑撥離間。”李樞當場嘆了口氣。“不過,咱們倆家世代相,令尊與我簡直是至親的兄弟一般,斷不會讓我冤屈的……不然,海捕文書都該下來了吧?”
白有思一聲不吭。
李樞捻鬚追問了一句:“賢侄可有海捕文書?”
白有思緩緩搖頭。
“既如此,我就不耽誤賢侄公幹了。”李樞見狀微微一拱手,居然直接而過,去旁邊上了一匹馬,然後打馬越過對方,孤向前。
雄、徐二人見狀,也一凜一笑,依著葫蘆畫瓢,各自上馬,昂然出,隨即,後數十騎各自就位,也緩緩隨,就從白有思、秦寶與胡彥兩側慢慢越過。
兩側十餘騎錦捕快一起向中間,胡彥更是雙目炯炯,但白有思卻一直沒有吭聲。
直到兩隊人馬錯完,這位年輕的巡檢方纔調轉馬頭,微微拱手示意:“世叔此去北荒,風波險惡,牢記家國風,一路平安。”
“賢侄也是。”李樞駐馬相顧,語調悠遠。“待見到你父,替我轉贈一言……就說天下紛紛,如我這等廢人願賭服輸,自甘遊江湖,倒也沒什麼可計較的。但像他那種才智之士,居於廟堂之中,若不能好生輔佐明君,使天下重新安定,將來怕是要被天下人瞧不起的。”
巡檢點了點頭,依然沒有什麼失措改容之態。
可就在所有人都覺得塵埃落定之時,忽然又有人開口了:
“李先生稍待!”
衆人循聲去,赫然是那個被所有人忽略掉的潰兵軍漢,此時居然牽著兩匹馬走了過來。“這兩匹馬,我恐怕不下,請先生和徐大郎拿走吧!”
雄伯南當即作,徐大郎也難得訕訕。
倒是李樞,依然面不改:“好漢是因爲軍國事怨恨起我了嗎?”
“沒有這回事。”張行直接牽馬從巡檢側走過,來到李樞跟前,言語從容。“軍國大事,風雲變幻,真要怨,可怨的人太多了,我有什麼可怨閣下的呢?再說了,萬事萬以人爲本,閣下明顯比那楊慎更懂這個道理……”
“好一個以人爲本!”聞得此言,這李樞忍不住在馬上仰天長嘆,聲震於野。“連一箇中壘軍的正卒都知道這個道理,可嘆多關隴王公貴族,志大才疏,渾然不覺!明明幾十年前還氣吞萬里如虎!”
“可要是不怨,爲何要還馬?”雄伯南聞言愈發焦躁,忍不住。
“我是活人,當然可以不怨。”張行回頭看了眼樹下,平靜對上此人。“但我那夥伴,生前就是個魯直的混蛋子,如今又死了,也不好悔改學習的,心裡怕是要怨的……我是怕他不願意坐李先生給的馬。”
李樞連連搖頭,復又點了點頭,直接打馬縱去。
雄伯南也一時氣急,卻只是甩了一馬鞭,然後匆匆尾隨而去。
還是徐大郎,忍不住低頭笑對:“你這軍漢何必不識好歹……這自是我徐家的馬,你兄弟怨李先生倒也罷了,不會怨我的吧?”
“徐大郎。”張行撒手放下繮繩,認真拱手。“謝你好意……也送你一句話,金鱗豈是池中,一遇風雲便化龍,你如此材資,爲何要因爲自己豪強之屢屢自輕自賤呢?時間長了,假的怕也真的了……便是無奈投江湖草莽,也該自一些。”
說著,直接空手轉回去了。
徐大郎怔怔看著這名萍水相逢的軍漢背影,似乎是想說些什麼,一直到對方回到樹底坐下,才幹笑了一聲,扭頭打馬引衆而去。
須臾片刻,一羣江湖豪傑便走的乾乾淨淨,只剩下一衆錦騎士和一個髒兮兮的軍漢,外加一首而已。
當然,還有半河瑟瑟,半河紅。
PS:謝書友有生皆苦的打賞,這是本書第22萌。
(本章完)
章節報錯
猜你喜歡
-
完結1513 章

煉神
只有經歷重重磨難,遍體鱗傷之后活下來的人,才可以成為強者和英雄,坐擁無數財寶,掌握億萬生死。 這個世界上,只有極少數人能夠享有最后的榮耀,而絕大多數人只能成為冰冷的墓碑。 所謂的規矩和法律,都只是用來束縛弱小者,被強者踐踏,在這個世界,不看身份,只看實力,唯獨實力,才是永恒。 第一聲春雷炸響的時候,秦逸睜開雙眼,眸中神光湛然,體內一億八千萬星辰,蠢蠢欲動……
289.7萬字8 64743 -
完結1154 章

玄幻:有求必應煉器師
蘇白穿越異界就被大佬劫持,非要讓狗屁不會的他拿出一個寶貝! 這可難壞了蘇白。 不過還好,超級係統煉器覺醒,有收益就能煉製寶物,煉寶就能變強! 多年後,看著跪在自己麵前求自己煉器的諸天神佛,蘇白輕輕揮了揮手。 “彆急彆急,本座有求必應!”
201.2萬字8 17282 -
完結15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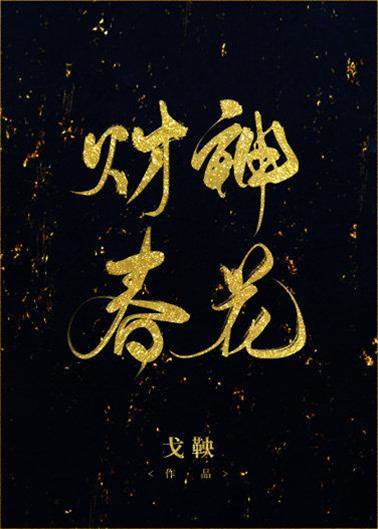
財神春花
兩個莫得感情的老神仙在人間動感情的故事~神仙日子漫漫長,不搞事情心發慌。北辰元君與財神春花在寒池畔私會偷情,被一群小仙娥逮了個正著。長生天帝下詔,將他二人雙雙貶下凡間,歷劫思過。此時正是大運皇朝天下,太平盛世已過百年,暗潮洶涌,妖孽叢生。汴陵城中長孫家得了一位女公子,出世之時口含一枝金報春,驚得產婆打翻了水盆。長孫老太爺大筆一揮,取名曰:長孫春花。長孫春花只有一生,財神春花卻有無窮無盡的歲月。
42.4萬字8 2106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