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妻歸來》 第75章 教訓她
“別以爲你塞給我,我就答應你了……”寧雪說著要取下自己手上的戒指。
“你敢摘下來!”騰項南打斷的話,厲聲喝了一聲。
雖然騰項南此時目兇步步近,但寧雪還是繼續著手上的作,騰項南一把上去抓住的手。
“明皓給你的,你就樂意戴著,我的你就這麼不稀罕!”騰項南將寧雪的手的攥在自己的大手裡,那目簡直要把寧雪活活吞掉。
寧雪第一次見他這樣的表,就是四年前,也沒有見過他這樣兇的樣子。
好像眼前的不是他每天追求的人,不是他口口聲聲說著的人,而是一個十惡不赦的壞人,更是他的仇人,他正是那個行俠仗義、又要報仇雪恨的英雄俠士。
寧雪邊後退著,邊看著廚房裡,希此時李嫂能出來救。可是,都要眼穿了,李嫂好像從後門走了一般。
當寧雪退到牆上時,見後面已無路可退,轉要跑,騰項南一隻胳膊託在牆上,隨後將上去。
因爲二人相,寧雪覺到了騰項南前心跳的靜;聽了騰項南呼著氣的聲音,甚至臉上還有他呼出來的熱氣,層層覆蓋過來,寧雪覺到的臉都被他的熱氣給烤熱了似的。
“你要幹嘛?快放開我!不然我了!”寧雪說著朝廚房看著,還是把希寄託在廚房裡的李嫂上。
騰項南沒有說話,打橫抱起寧雪就朝樓上走去。
“瘋子,快放我下來,李嫂!救我!李嫂!李嫂——”寧雪攥拳使勁兒打著騰項南的肩頭結實的,大聲對著廚房的方向著。
結果沒等到李嫂,卻聽見騰項南說:“再,把孩子們起來,我當著他們的面要你!”
Advertisement
“神經病!神經病!”寧雪的臉紅了,氣呼呼的將頭偏過一邊,“流氓!無賴!你今晚休想我!你要敢我,我死給你看!”
“好,現在就摔死你!”騰項南假裝放手。
“啊!”寧雪的子下沉,本能得趕抱騰項南的脖子。
騰項南見抱了自己,又迅速將懷裡那個的摟回來抱,很很。
回到騰項南的臥室,寧雪看去,這個房間也變了,重新裝修了一些暖調,看去比以前暖和了一些,但還是以冷爲主,這是騰項南的風格。
房間裡多了一個漂亮的歐式梳妝檯,上面擺放著一些化妝品,寧雪心裡有點暖,這個肯定是他爲準備的。這裡還和四年前一樣的是,還是那麼幹淨整潔,一塵不染。
“雪兒,別鬧了好不好,顧語薇的事,我後悔了,我一定會給補償的,你別和我較勁了行嗎?別折磨我了,求你!”
騰項南放下寧雪,寧雪剛要逃,騰項南從後面再次摟回寧雪,將頭抵在孱弱和纖細的肩上,附在寧雪的耳邊呢喃低語,乞求的味道很足。
剛剛樓下那種萬惡已經完全褪去,現在他就是一個流浪的小貓,期盼著主人的憐憫。
聲音裡也充滿悔恨、頹敗的味道,甚至還有點哽咽,是的,他說的很誠懇,聽著想讓人給他投去同票。
層層熱氣覆蓋上來,在寧雪耳邊散開,的,寧雪低頭去躲,騰項南乾脆咬上去,還用舌頭著飽圓的耳垂。
“好了!別鬧了!這場鬧劇該結束了!”寧雪用盡全力推開騰項南,剛剛他的話確實有點煽,寧雪側過,不去看他,擔心這一看去,就又會被他那副寫滿委屈的可憐的皮囊給騙了。
鬧劇?說鬧劇!原來在眼裡他們的一切都是他一場鬧劇嗎?而他所有的行爲也了鬧,不是他的真流嗎?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想要和在一起!
“你就是這樣看我們的的?你就是這樣看我對你的的?”騰項南問的很失落,好像此時正在墜谷底,地球媽媽的引力太強,他的力氣不夠抵抗只能掙扎。
剛剛上樓時那種讓人膽寒的氣魄已經完全不在騰項南的上,此時他那種如一隻傷的小貓咪般的神和態度,讓寧雪有些張。
到是希看到他如牛一般的犟,如虎一般的兇,那樣的他,覺得真實,覺得他正常,他不可怕,而這種如死灰一般的沒有氣焰,寧雪心裡卻很慌。
“說!”騰項南突然衝著寧雪喊了一聲。
突如其來的西斯底裡般的一聲把寧雪嚇了一跳,剛剛不是綿綿了嗎?怎麼突然又犯起神經來?
看見把寧雪嚇了一跳,騰項南有點恨自己剛剛失控,主要是因爲寧雪的話太讓人生氣,他全心全意的,卻說是一場鬧劇,騰項南目憐惜,出手去,剛張開要道歉,只聽得寧雪衝著他大聲嚷道:
“說什麼?神經病!難道你不是在鬧嗎?你看看你一路走來,都做了些什麼?你有做過一件正常人做的事嗎?三歲小孩子都沒有你那麼稚!你給我的那些我就都不說你了,可是你對顧語薇做的,你說說你,這是一個正常人能想出來的嗎?”
寧雪說道這裡,冷嗤了一聲,諷刺中又有難過,“你還要補償?你怎麼補償?你拿什麼補償?又要用錢嗎?人家不缺!不就用錢砸人,我就是給你用錢砸死了!”
話落後寧雪的臉上落下兩行眼淚,吧嗒吧嗒的落在前的服上,自從四年前用了他的錢,做了他的人,就沒有一天好過。
理解他,他的錢也不是颳風逮來的,自己付出一些也就算扯平了,可是,人家顧語薇到底哪裡惹他了,難道就因爲上他,就該被他這樣侮辱踐踏嗎?
“好好好,是我錯了,那我們等,等找到幸福了,我們再在一起行了吧?可是,這段時間你可不可以不要和那些男人們來往!”
“我的事不要你管!”
這句話寧雪和騰項南說過很多次,每一次聽到,這句話都會如一把利劍一樣刺痛騰項南。刺到他疼的上不來氣,說不出話。
寧雪瀟灑的抹了一把眼淚,“我們家欠你的,我也該還的差不多了吧?當初,也是你同意放我走的,現在,你就該灑一點兒,不要在糾纏了!世界上好孩多的去了,你何必抓著我不放。”
是要徹底和他決裂!騰項南聽得出,是不想再和他來往了。
“今晚就這樣吧,明天開始,我希你能男人一點兒,不要再來打擾我們了。今晚我和燦燦睡,你可以和住一晚,但是以後你就當我們不存在吧,如果你做不到,我還會消失的!”
寧雪說完把今天白天他給戴上的戒指,摘下來放在騰項南的手裡,快速轉擡步,一直到門口都一氣呵,步履從容且快而急,害怕他長臂一揮一句言細語,就又會淪陷。那樣的話,對不起顧語薇,而雅澤也將永遠不會再有機會和的人在一起。
騰項南一個箭步衝到門口,強拉起的右手,把那枚戒指再一次強迫的給寧雪帶上,上氣狠狠地說:“既然戴上了我的戒指,就是我的人!沒有摘下來的道理!這個必須戴上!”
騰項南說著有氣,心裡更是火冒三丈,都把自己快給火化了,想著寧雪戴著明皓的戒指就氣不打一來,戴著別人的戒指到心安理得,戴著自己的戒指這還沒有幾個小時,就摘下來!哪有這樣的自己的人!
“你就是瘋了!神經病!”寧雪趕著他的話,把騰項南再次強給戴上的戒指又摘下來,狠狠的朝著騰項南扔過去,“我不是你的人!我不屑你的戒指!”
戒指隨著寧雪的力氣掉在了地上,當騰項南低頭看的時候,戒指已經不在地上,不知道哪兒了!
騰項南心痛,只見寧雪再次轉,他失的問道:“寧雪!你真的上了別人?”
走到門口的時候,後騰項南的話很平淡,聽不出什麼味道?
寧雪也不去想他是認命了還是想著挽留,也沒有回頭,淡淡的回了一個字:“是。”
“是誰?我現在打電話讓他來接你,從此不再打擾你。”
騰項南走到門口來到邊,拿出手機來,“是權沛澤還是明皓?哦,我想你的是權沛澤,雖然你戴上了明皓的戒指,可是,你應該的是權沛澤,是權昌盛不同意是吧?沒事,我來給你擺平,我能讓他接你這個兒媳婦,我打給他。”
因爲就站在他邊,而騰項南的手機就在眼前,眼看著騰項南的手機屏幕上出現權昌盛三個字,那三個字下面還有一個號碼,而騰項南眼看要撥出去,寧雪急了,這個號碼一撥出去,媽媽就會陷困境。
而且現在大半夜的,一定會引起一場風波,寧雪奪過騰項南的手機狠狠的扔了出去,手機砸在了對面的牆壁上,只聽得“砰!”地一聲,手機支離破碎。
看著摔碎的手機,寧雪一下子怔住了,倒不是因爲摔了他的手機,而是後怕那個電話被撥出去。
“你真的瘋了!真是無聊了!”寧雪氣狠狠的瞪著騰項南,眼裡的淚花閃啊閃,咬著牙齒,再次狠狠的說:“我真看不起你,你連一條狗都不如!我是不會給你第二次傷害我的機會了!”
寧雪說完拉門就走,騰項南一把將拉回來,他怒的是每次一提到權家任何一個人,寧雪都會這樣拼命的和他對抗,看來真的是著權沛澤,而且到骨髓。
“權沛澤就好,我不如一條狗,他就是男人了?你那麼他,他給了你什麼?連一個名分都不敢給你,還要你辛苦去工作,還要你委屈去答應明皓的求婚!你就那麼甘心爲了他去忍一切?”
騰項南也是氣到了極點,口不擇言的繼續說道:“你他這麼的委屈自己,他家財萬貫,還讓你住在那個鳥窩裡,區區二十萬也就把你打發了!而我把心都掏給你,你卻無於衷……”
“啪!”
騰項南的話還沒有說完,臉上就被寧雪扇去一掌,寧雪氣他調查自己,擔心他這一調查就會查出自己和應寧的關係來,那麼這個將會被人知道,遲早一天,這個將公佈天下,那時,的媽媽該怎麼辦?
“別再管我!王八蛋!”寧雪擡就走,轉那一刻,的眼淚洶涌,這回真的生氣到了極點,這個男人,將永遠不會再投去一點心,永不他!
剛出門的寧雪就被一強大的力量給拉再次拉進屋裡。門“哐當”一聲被關上。騰項南如惡狼般兇狠的目再次瞪著,就像剛剛在樓下時那樣。
但無論怎麼樣,寧雪都不再在意他,此時對他只有恨。
寧雪掙扎著,從自己的兜裡掏出自己的手機,找出權沛澤的電話來,按了出去,待電話通了的那一刻,寧雪說:“阿澤,你睡了嗎?我在騰項南家的別墅,你來接我。”
寧雪說完不等對方說話,果斷的掛了電話,寧雪揚起頭,瞪著騰項南,“你說對了,我他!到每一管,每一條神經,滲骨髓!刻骨銘心!你!永遠都和他不能比!”
就一個電話打出去,已經就快要了騰項南的命,再加上對他的這一番話,騰項南真是痛不生,就在心抖的那一刻,十手指痠痛難忍。
都說十指連心,這心痛,手指也跟著痛,原來想抓住寧雪的手,一下子沒了力氣,跟著頭皮發麻,全無力,他好像被/1出了髓,放掉了元氣。
猜你喜歡
-
完結271 章

且以深情共余生
相似的聲音,相似的容貌,遇見了同一個他。兜兜轉轉,走走停停,時光不改蹉跎。如果上天再給她一次重新選擇的機會,她一定奮不顧身愛的更加用力!
50萬字8 9205 -
完結378 章

玄門回來的假千金又在擺攤算卦了
肖梨在玄門待了一百年,同期進來的那條看門狗小黑,都已經飛升上界,她還只能守著觀門曬太陽。老祖宗顯靈告訴她,“肖梨,你本來自異界,塵緣未了,若想飛升,还得回去原来的地方,了却凡尘杂事,方可勘破天道!” 回到现代,肖梨成了鸠占鹊巢的假千金,这一世,没有留念,两手空空跟着亲生父母离开肖家。 圈内人都在等着,肖梨在外面扛不住,回来跟肖家跪求收留。 却不想…… 肖梨被真正的豪门认回,成为白家千金,改名白梨。
64.4萬字8 60458 -
完結189 章

荒腔
沈弗崢第一次見鍾彌,在州市粵劇館,戲未開唱,臺下忙成一團,攝影師調角度,叫鍾彌往這邊看。 綠袖粉衫的背景裏,花影重重。 她就那麼眺來一眼。 旁邊有人說:“這是我們老闆的女兒,今兒拍雜誌。” 沈弗崢離開那天,州市下雨。 因爲不想被他輕易忘了,她便胡謅:“你這車牌,是我生日。” 隔茫茫雨霧,他應道:“是嗎,那鍾小姐同我有緣。” 京市再遇,她那天在門店試鞋,見他身邊有人,便放下了貴且不合腳的鞋子。 幾天後,那雙鞋被送到宿舍。 鍾彌帶着鞋去找他。 他問她那天怎麼招呼都不打。 “沈先生有佳人相伴,我怎麼好打擾。” 沈弗崢點一支菸,目光盯她,脣邊染上一點笑:“沒,佳人生氣呢。” 後來他開的車,車牌真是她生日。
28.8萬字8 1773 -
完結19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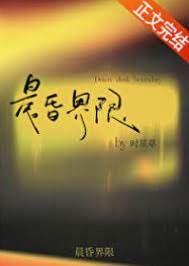
晨昏界限
林霧有些記不太清自己和陳琢是怎麼開始的,等她後知後覺意識到事情變得不對勁時,他們已經維持“週五晚上見”這種關係大半年了。 兩人從約定之日起,就劃分了一條明顯的,白天是互不相識的路人,晚間是“親密戀人”的晨昏界限。 而這條界限,在一週年紀念日時被打破。 - 人前不熟,人後很熟的故事TvT
27萬字8 564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