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謀不軌》 第869章 君澤,我來娶你了
從景秀宮出來后,顧玉沒有出宮,而是去文翰司拿了一個折子,直奔東宮而去。
不出意外地被太子拒之門外,東宮的宮人道:“太子在忙,不然顧丞相等等再來?”
顧玉自知傷了景君澤的心,合該低一次頭了,便道:“太子什麼時候忙完?”
宮人道:“丞相稍候,奴才去問一問。”
這宮人到了東宮,太子正拿著布老虎哄兩個鬧人的孩子:“丞相差奴才問您,什麼時候忙完。”
景君澤臉并不好看,只說了兩個字:“不知。”
宮人只能退下,把這兩個字轉告顧玉。
顧玉道:“那我等太子忙完再過來。”
宮人連忙攔著:“顧丞相要不再等等?說不定再等一會兒,太子就忙完了。”
宮人覺得自己暗示的已經夠到位了,太子雖然拿著架子,但定然舍不得顧丞相等太久。
顧玉指指閉的大門:“在東宮里面等嗎?”
宮人為難一笑:“恐怕得勞您在外面等等。”
這像什麼樣子?顧玉看了一眼東宮大門,有些別扭。
“我還是等太子忙完再跑一趟吧。”
說完,顧玉就轉走了。
Advertisement
宮人愁眉苦臉地向景君澤回話:“顧丞相說,等您忙完就再跑一趟。”
景君澤怒從心起,要不是怕嚇著寰晢和宸晰,都要把手中的布老虎扔了。
景君澤惡狠狠道:“讓等著吧。”
這一等就到了晚上。
宮門下鑰之前,顧玉還在文翰閣中,面前堆著一摞折子,按照顧玉從前的效率,這些早該弄完才是,但現在還有許多。
文翰學士客氣問道:“丞相不回去嗎?”
顧玉把頭從折子中抬起來,一本正經道:“無妨,我在這里守個夜。”
夜深沉,直到宮人來添茶,才發現里面空無一人,喃喃自語:“奇怪,顧丞相去哪兒了?”
與此同時,一道鬼魅的影翻墻進東宮。
雖然東宮里有守衛,但顧玉對東宮的了解比那些守衛多多了,倒是輕車路就進來了。
東宮多了兩個孩子,燈熄得早,黑一片。
顧玉打開窗戶,狗狗祟祟潛了進去。
窗戶關上后,不遠目睹一切的關言,默默走開。
屋子里十分安靜,只有一個人均勻的呼吸聲,寰晢和宸晰應該由宮人照顧著,不在這里。
顧玉悄悄走到床邊,還未掀開床簾,就把一把刀抵住嚨。
景君澤衫整齊,從床帳里走了出來。
月戶,顧玉看得出景君澤的冷臉,便舉著手,一言不發,隨著他的刀劍前進而一點點后退。
退到桌子邊上,就退無可退了。
景君澤語氣冷然問道:“你來做什麼?”
顧玉沉默了一下,頗為不自在道:“我來私會我的姘頭,你見到我姘頭了嗎?”
從前景君澤聽到姘頭二字,還能自我調侃一下,現在卻是直接炸:“沒見到!”
黑暗中,顧玉紅著耳朵道:“那你如果見到了,能不能幫我帶句話,我想他了。”
說完顧玉就在心里唾棄自己,真的不是說話的料,這七八糟的都說了些什麼。
景君澤冷冰冰道:“不能!”
顧玉看他一點兒都不為所,不心急。
忍住恥,把阿姐教的話說了出來:“那我該怎麼辦?沒有我的姘頭,長夜漫漫,孤枕難眠。”
景君澤冷哼一聲,把刀收起來:“隨你怎麼辦,你現在就走,我不想看見你。”
顧玉做了許久的心理建設,學著景君澤的樣子腆著臉來,卻沒能他,不敢慨自己真的不是說膩膩歪歪的話那塊兒料。
“那我走?”
景君澤冷酷無道:“走!”
顧玉走到窗戶邊上,回頭道:“我真走了?”
景君澤并未回答,已經走床幃,聽聲音是又躺下了。
顧玉癟癟,輕輕打開窗戶,翻了出去。
腳步聲漸行漸遠,景君澤看著頭頂的床幔,用力蹬了一下泄憤。
的心一點兒都不誠!
說走就走。
景君澤不甘心,站起來,打開窗戶,看了看外面,果真靜悄悄的。
可下一瞬,顧玉的腦袋就從拐角鉆了出來,一副“我就知道你會來看”的狡黠表。
景君澤氣急敗壞地把窗子砸上,又將顧玉拒之窗外。
他以為顧玉會過來敲窗,可是并沒有,這下外面是徹底安靜了。
乃至于景君澤翻出窗外去看,都不見了顧玉的影。
景君澤的眸愈發冰冷,他自嘲一笑,不知道自己在期待什麼。
過了好一會兒,窗戶從“吱呀”一聲,被人打開。
景君澤直躺在床上,不理會來人。
覺到腳步聲越來越近,他索閉上眼睛,眼不見心不煩。
下一瞬,就有個東西蒙在他頭上。
景君澤下意識就要用手把東西拿下,卻被顧玉自上而下桎梏住手腳。
“別!”
景君澤惡狠狠道:“顧玉,你究竟想干什麼!”
把他當什麼了?
召之即來揮之即去的狗嗎?
想親近就親近,想疏遠就疏遠,一句“終不嫁”斷了景君澤長久以來的盼,毫沒有考慮他的。
顧玉不善于表達意,也不會表達意。
在看來,親吻比話更能直接表達對景君澤的。
那些膩膩歪歪的話說著實在別扭,索便不說了。
顧玉隔著蓋頭,挲著吻上景君澤的,有控制著他的手腳,不容他拒絕。
一吻畢,不等景君澤再說出什麼賭氣的話,顧玉便意繾綣道:
“君澤,我來娶你了。”
猜你喜歡
-
完結1082 章
爆笑王妃:邪魅王爺澀澀愛
太師府剋夫三小姐,平生有三大愛好:食、色、性。 腹黑男八王爺,行走江湖有三大武器:高、富、帥。 當有一天,兩人狹路相逢,三小姐把八王爺全身摸了個遍,包括某些不該摸的地方,卻拒絕負責。
213.7萬字8.18 88415 -
完結861 章
龍鳳雙寶神醫娘親藥翻天
天才藥劑師一朝穿越成兩個孩子的娘,還是未婚先孕的那種,駱小冰無語凝噎。無油無鹽無糧可以忍,三姑六婆上門找茬可以忍,但,誰敢欺負她孩子,那就忍無可忍。看她左手醫術,右手經商,還有天老爺開大掛。什麼?無恥大伯娘想攀關系?打了再說。奶奶要贍養?行…
156.3萬字8.18 81645 -
完結1025 章

農家小福妻有法術
【無所不能滿級大佬vs寵妻無度鎮國將軍】 現代修真者楚清芷下凡經歷情劫,被迫俯身到了一個古代農家小姑娘身上。 小姑娘家八個孩子,加上她一共九個,她不得不挑大樑背負起養家重任。 施展禦獸術,收服了老虎為坐騎,黑熊為主力,狼為幫手,猴子做探路官兒,一起去打獵。 布冰凍陣法,做冰糕,賣遍大街小巷。 用藥道種草藥,問診治病,搓藥丸子,引來王公貴族紛紛爭搶,就連皇帝都要稱呼她為一句女先生。 為了成仙,她一邊養家,一邊開啟尋夫之路。 …… 全村最窮人家,自從接回了女兒,大家都以為日子會越來越艱難,沒想到一段時間後,又是建房又是買地…… 這哪是接回的女兒,這是財神爺啊! …… 連公主都拒娶的鎮國大將軍回家鄉休養了一段時間,忽然成親了,娶的是一位小小農女。 就在大家等著看笑話的時候,一個個權貴人物紛紛上門拜見。 太后拉著楚清芷的手,“清芷,我認你做妹妹怎麼樣?” 皇帝滿意地打量著楚清芷,“女先生可願意入朝為官?” 小太子拽住楚清芷的衣擺,“清芷姐姐,我想吃冰糕。”
177.3萬字8.46 176072 -
完結60 章

春閨嬌
一上一世,沈寧被死了十年的父親威逼利誘嫁給喜愛男色的東宮太子秦庭。 身為太子妃,她公正廉明,人型擋箭牌,獨守空房五年,膝下無子無女,最終熬壞了身子,被趕出東宮死在初雪。 重回始點,她褪去柔弱,步步為營,誓要為自己謀取安穩幸福,提起小包袱就往自己心心念念的秦王秦昱身邊衝去。 這一世,就算是“紅顏禍水”也無妨,一定要將他緊緊握在手裏。 二 某日。 沈將軍府,文院。 陽光明媚,鳥語花香,突傳來秦昱低沉清冷如玉般的聲音:“阿寧,你年紀小,身子弱,莫要總往我府上跑了。” 正抱著茶盞喝的開心的沈寧暴跳如雷——她跑啥了跑?倒是您一個王爺,沒事少來行嗎? 三 問:該怎麼尷尬又不失禮貌的嫁入秦·王·府? 天鴻清貴的秦昱勾了勾薄唇:王妃,床已鋪好,何時就寢? ps:男女主雙潔 ps:關於文中的錯別字,過完年我會抽時間整改一次,另外是第一次寫文,許多細節可能沒有完善好,但我日後會更加努力,謝謝觀看。 內容標簽: 情有獨鍾 宅鬥 重生 甜文 主角:沈寧
18.5萬字8 21891 -
完結1055 章

最小反派:團寵魔女三歲半
魔女變成三歲半小團子被迫找爹,可是沒想到便宜老爹一家都是寵女狂魔。從此,小團子開始放飛自我,徹底把改造系統逼成了享樂系統,鬧得整個江湖雞飛狗跳。小團子名言:哥哥在手,天下我有。什麼?有人找上門算帳?關門,放爹!
192.7萬字8 28556 -
完結43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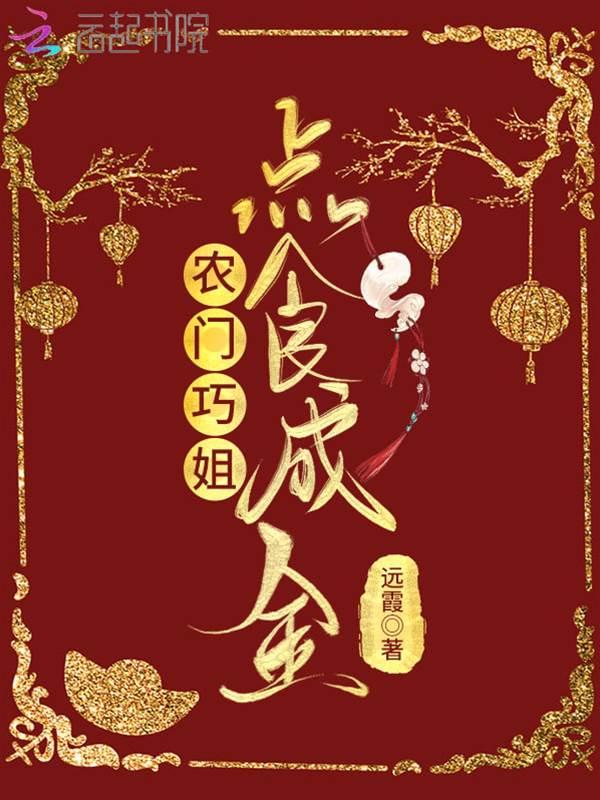
農門巧姐點食成金
高級點心師意外穿成13歲彪悍小農女-包蓉。後奶惡毒,親爺成了後爺。,爹娘軟弱可欺,弟弟幼小,包蓉擼起袖子,極品欺上門,一個字:虐!家裏窮,一個字:幹!爹娘軟弱慢慢調教,終有一天會變肉餡大包,弟弟聰明,那就好好讀書考科舉,以後給姐當靠山,至於經常帶著禮物上門的貴公子,嗯,這條粗大腿當然得抱緊了,她想要把事業做強做大,沒有靠山可不行,沒有銀子,她有做點心的手藝,無論是粗糧、雜糧、還是精糧,隻要經過她的手,那就都是寶。從此,包蓉銀子、鋪子全都有,外加一個自己送上門的親王夫君,氣得後奶一概極品直跳腳,卻拿她無可奈何。
77.6萬字8 3790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