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庶女》 3232
3232
室,一男一纏在一起,發出曖~昧又火熱的息聲。昏燭閃爍,映在牆上,照出男纏綿的影子。胥麗華躺倒在牀上,脯微。年埋在前,舐親吻。氣息不定,抱著年的頭,喃喃:
“玉臺,你小時,一直是我最喜歡的孩子。你長得漂亮,格又溫。可是我知道,你渾都是刺,你必然不是尋常人……我不讓你識字,挑斷你手筋,讓你一事無,都是爲了困住你。呆在我邊不好嗎?你看外面那些孩子,飽經風霜,多麼可憐。可你總是不聽話,就是不肯留在我邊……”
年吻著手腕,細如雨。你看他的作,如同對待人般親。但他的眼睛,落在虛空,霾可怖,滿是狠戾和殘暴。他眼神越兇狠,親吻胥麗華的作,就越溫。
胥麗華被他親得眼中滴水,子都快化了。漸漸不能滿足於他的淺嘗輒止,自己翻,把瘦弱的年在下,俯欺上他的脣瓣。卻見他眼中一抹厭惡,別頭躲過的親吻,脣落在了纖白的頸上。胥麗華一怔,一手撈起他散在牀間的烏髮親吻,另一手溫地著他脖頸上纖細的管,聲:
“我還以爲玉臺變了,原來還是和以前一樣呢。也罷,不親你的兒,親你別的地方。我也知道,你現在投懷送抱,不過是希在我手下保一命。相同的變故,我不會讓你給我出現兩次!這次,我一定要得到你,你給我使花招……哎,玉臺,如果四年前,你如現在這樣聽話,也不用吃那麼多苦頭了……”
從他的脖頸,一路向下吻去。既然不用作,年便乾脆閉眼。讓胥麗華無比沮喪的是,無論再殷切再熱地親吻,無論發出多麼曖~昧的吮吸聲,謝玉臺的,都毫無反應。他閉著眼被在牀上,睫半掩,脣瀲灩,面容如雪般惹人憐。明明細吻已經到了小腹上,他仍然沒反應——沒反應!胥麗華氣極,卻只能嘆氣:
Advertisement
“都怪我不好,小時給你灌了太多藥。只是玉臺,你總是不,是要一晚上,就這麼跟我耗下去嗎?你不怕惹火我,我再做出什麼控制不了的事嗎?你總是要我下手傷你,是何苦呢?”
謝玉臺突然睜眼,看向。雙目明亮,眨間,如銀河中鋪滿了星。他對彎眸一笑,笑得胥麗華怔住,心跳加速,面頰通紅,逆流,全彈不得……全彈不得!
“玉臺,你給我做了什麼?!”胥麗華面孔扭曲,恨不得吃了他。
“兩次,我當然不會用同樣的招數。毒藏在我舌尖,是你要我吻你的。”謝玉臺推開,嫌惡坐起。盯著吃人的眼神,慢慢從旁邊搬鏡子給看,“這一次,我毀的,是你的臉,而不是我的臉。”
只見鏡中映出的白髮子,額頭上的皺紋越來越多,眼下浮起青,面頰開始腫起……
“玉臺!”胥麗華大喝,“我的臉!給我解毒!”
“我本來要你死!不過時間來不及了……”謝玉臺從旁邊搜出男子穿上,本不理會的哭,“我要去救阿妤,沒時間耽誤在你這個老太婆上。”
同時間,門被從外推開,伏夜走進來。看了眼前景象,怔住。立馬,層層侍衛,圍住了謝玉臺。伏夜瞪著這個太大膽的年,“你做什麼你?!利州的事,是你做的?”轉頭向牀上那個越來越老的人,彙報利州發生的事。
“玉臺,給我解藥!”胥麗華被人扶著,原本漂亮的眼睛,都快到了一。這下,連角,都開始生出皺紋了。
“放我走。”謝玉臺淡聲。
“你做夢!”胥麗華大。
伏夜趕接道,“郡主,再不走,利州的事就無法挽回了。”
“……”胥麗華恨恨盯著謝玉臺,早就知道這個年壞到骨子裡,卻沒料到、沒料到——是不是還應該謝那個阿妤呢?如果沒出事,謝玉臺是打算在這裡死拖住自己,讓利州的事告到陛下那裡去。
謝玉臺看懂了他們這些人的爲難,脣扯笑,轉走出了這裡。他腳步匆匆,走過許多人面前。沒有一人,敢攔住他。他扶著手臂,踉踉蹌蹌地往外跑。自己多麼狼狽沒關係,傷多重沒關係,他要去找阿妤。
兩天時間還沒到,阿妤你不能出事!
屋,伏夜跪在胥麗華腳下,聽到他那位郡主疲憊的聲音,“還愣著做什麼?回利州。”謝玉臺,遲早讓他付出代價!
“謝玉臺?”明月下的小村落外,江思明正和衆百姓一起挖著山石,救那些在下面的人。他聽到周圍人氣,回頭看,竟看到月下的年,從臉到出的手臂,盡是傷痕累累。卻一聲不吭,跪在地上,和衆人一起挖石。
“阿妤活著吧?”謝玉臺輕聲問他,目卻不看他,“你還活著,也一定活著……”
江思明被噎著,氣道,“死了。”
“憑什麼死了,你還活著?”謝玉臺低聲自語。
江思明一張臉發黑,瞪著他跪在地上的背影,“你什麼意思你?!”
“一定活著。”有百姓跑過來哭自己喪命的孩子,見年瘦弱,一把推開他,搶過他手上的鏟子,自己挖土。謝玉臺自己傷的手臂,也沒力氣去跟人搶鏟子。沒有了鏟子,他用手開始刨。
江思明懶得理他,這個神經病!他看看天晚了,轉就打算先回去休息。卻瞇眼,看到月下不遠的道上,數百人騎馬駕車而過,掀起一大片塵土。那是……定平郡主的人吧。
離去前,他不由看了看謝玉臺:這個年,是怎麼逃出來的?
謝玉臺從來不管別人怎麼看,邊還有哪些人,他也不知道。他只是麻木地用手挖著土,挖著石頭……手上全是痕,指甲裡全是和土混的。
天黑了,天亮了,天又黑了……周圍人來來去去,他一直不。
他沒找到阿妤,還是沒有找到阿妤。那麼黑的地方,阿妤是孩子,一定害怕。他要找到……一定要找到啊。他也沒想到會發生地龍,遠比阿妤被胥麗華接過去更可怕。
後來,謝玉臺手上全是,再作不了。他才傳信,給在青城的謝家侍衛,請大家幫忙來尋人。
某侍衛猶豫,委婉勸說,“七公子,土掩的很實,下面幾乎沒空氣……還要挖嗎?”
很長一段時間,衆人就看著謝玉臺盯著塌下的山土在發呆。謝七郎和謝家其他人都不一樣,他遠沒有謝家人的詭譎多智。大家服從他,不過是因爲他謝七郎的份。挖土救人,真的很荒唐。
“當然,當然要救。”謝玉臺輕輕說道,又重複一遍,“一定要救的。”
其實他也知道,自古以來,被土埋在下面的,沒有幾人能活著出來。千百來人,估計也就那麼一個生還。可是他那麼地希,阿妤是活著的。阿妤,阿妤,他明明只想把留在邊。明臺說,有些人,遠遠的看,越想越思念,還不如留在邊好;留在邊,或許有一日,看著看著,就厭煩了,就沒那麼想了。謝玉臺自然希的是後者——可他不知道,有的人留在邊,是時間越長,越想得。
就如他現在這般,忍不住後悔:如果那時候,他放棄阿妤,讓阿妤走,就好了。他本就不是長之人,一個小姑娘,他連的聲音都會記不住。的臉,的印象,遲早有一日,也會忘的。只要他耐心的等,那思念,總會空。他真不該,想把阿妤留在邊。上天總是待他不公,他也早就習慣。可是阿妤不一樣,只是被他強行拉進來的,無罪。
“阿妤無罪,請你們仁慈,赦平安。”
地龍發生後,就一直下著雨。江思明從未放棄找阿妤,在謝玉臺忙碌的時候,他也在運用江家權勢救人。這是他妹妹,縱然平時聯繫不大。但他從來沒想過,要阿妤這樣死去。所謂,活要見人,死要見。阿妤生死,都要給他一個代。
“一定要活下去吧?”
“嗯,一定、一定、一定不能放棄。”
“爲什麼一定要活下去?”
“爲了不給別人造困擾啊。如果阿妤死在青城,還是和大哥在一起。大哥,要怎麼跟家裡人代呢?阿妤不能做別人的負擔和困。”
“還有呢?這樣的理由,並不夠讓我堅持活下去啊。呼吸困難、空氣稀薄、被……那樣的藉口,並不能說服我啊。”
“還有、還有……玉臺啊。”
“謝玉臺嗎?”
“對啊,難道不想念他嗎?不怕他難過嗎?分明相時間並不長,但已經忘不掉的謝玉臺——阿妤爲了他,也要活下去。”
“是,一定要活下去。只有活著,一切纔有希。”
黑暗世界,明突現,年的臉容已模糊,記憶卻清晰無比。有很多話,想跟他說。許多錯過的事,也都想爭取回來。江妤(並不是)(一時不查)(鬼迷心竅)(才)喜歡謝玉臺呀。
人聲離自己越來越近,阿妤想,終於得救了吧。
猜你喜歡
-
完結21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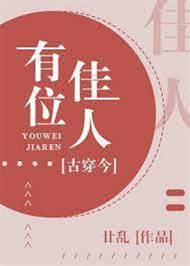
有位佳人[古穿今]
沈嶼晗是忠勇侯府嫡出的哥兒,擁有“京城第一哥兒”的美稱。 從小就按照當家主母的最高標準培養的他是京城哥兒中的最佳典範, 求娶他的男子更是每日都能從京城的東城排到西城,連老皇帝都差點將他納入后宮。 齊國內憂外患,國力逐年衰落,老皇帝一道聖旨派沈嶼晗去和親。 在和親的路上遇到了山匪,沈嶼晗不慎跌落馬車,再一睜開,他來到一個陌生的世界, 且再過幾天,他好像要跟人成親了,終究還是逃不過嫁人的命運。 - 單頎桓出生在復雜的豪門單家,兄弟姐妹眾多,他能力出眾,不到三十歲就是一家上市公司的CEO,是單家年輕一輩中的佼佼者。 因為他爸一個荒誕的夢,他們家必須選定一人娶一位不學無術,抽煙喝酒泡吧,在宴會上跟人爭風吃醋被推下泳池的敗家子,據說這人是他爸已故老友的唯一孫子。 經某神棍掐指一算後,在眾多兄弟中選定了單頎桓。 嗤。 婚後他必定冷落敗家子,不假辭色,讓對方知難而退。 - 新婚之夜,沈嶼晗緊張地站在單頎桓面前,準備替他解下西裝釦子。 十分抗拒他人親近的單頎桓想揮開他的手,但當他輕輕握住對方的手時,後者抬起頭。 沈嶼晗臉色微紅輕聲問他:“老公,要休息嗎?”這裡的人是這麼稱呼自己相公的吧? 被眼神乾淨的美人看著,單頎桓吸了口氣:“休息。”
49.8萬字8 8241 -
完結1550 章

穿成惡婆婆后,我讓全村心慌慌
二十歲的林九娘一覺醒來,成為了安樂村三十五歲的農婦五個兒女跪著求她去‘寄死窯’等死,兩兒媳婦懷著娃。母胎單身二十年的她,一夜之間躍身成為婆婆奶奶級的人物調教孩子、斗極品、虐渣已經夠困難了,可偏偏天災人禍不斷。慶幸的是,她空間有良田三千畝,還愁小日子過不好嗎?不過她都老大不小了,他們個個都盯著自己做啥?
302.2萬字8.33 176397 -
完結118 章
穿成沖喜王妃后我成了病嬌王爺心尖寵
從小寄人籬下的傻女,被害死在鄉下后依然難逃被賣的命運。 美眸初綻,傭兵女王穿越重生,夢魘散去后必將報仇雪恥。 沒錢??活死人肉白骨,值多少錢? 亂世?空間在手,天下我有! 蒙塵明珠閃耀光華之時,各路人馬紛紛上門,偽前任:你既曾入我門,就是我的人。 偽前任他叔:你敢棄我而去?! 「傻女」 冷笑:緣已盡,莫糾纏。 掃清障礙奔小康,我的地盤我做主。 某天,一個戴著銀面具?神秘人邪氣一笑:「聽說你到處跟人說,你想當寡婦?」
35.7萬字8 1262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