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娘娘她千嬌百媚》 [娘娘她千嬌百媚] - 第 111 章
番外二
顧錚詫異地看著阮綰:“你……”
四目相對。
阮綰從未見過這般深邃沉穩的眼眸, 像是能看小心藏的窘境。
杏眸微,阮綰心中越發忐忑張,腹部疼痛跟著加劇, 一陣兒冷風吹過,打了個寒, 褪去, 有些泛白的小臉一陣陣燒熱。
顧錚不會辨錯這個氣味, 靜默片刻,他不是多管閒事的人,但眼前這個稚氣的小姑娘在角落裡,像了驚一般,看上去狀態實在不好。
顧錚腳步挪, 沉聲問:“你傷了?是否需要幫忙?”
大概就是這般不湊巧,遠又傳來一陣兒雜的腳步聲。
顧錚看過去, 是阮大老爺和阮家的一眾族親們,還有方才引路的侍僕,他們是來尋他的。
阮綰自然也聽到悉的聲音, 他只是個陌生人, 被他撞到不過只是丟臉, 若是被父親和長輩們發現……
阮綰心沉了沉,忍著腹痛快速起站到亭中圓柱後,看向這個陌生人, 杏眸中不由得帶著一乞求。
鬼使神差, 顧錚了一惻之心, 看了一眼他的侍衛, 拂袖在人靠上落座。
侍衛立刻走出避風亭, 攔住阮大老爺的去路。
侍衛沒有多做解釋, 只說顧錚見此景好,想在這兒獨自一人歇會兒。
阮家恨不得把顧錚供奉在手心裡,自然他說什麼就是什麼,不敢打擾,連連點頭,說是等會兒來請他用晚宴。
阮綰盯著自己的腳尖,好像才意識到父親在心裡比這個陌生人更讓生怯。
顧錚盯著坐過的地方留下的跡,抬眸看,秀麗的面龐有些黯然,顧錚淡聲問:“你的傷勢還好嗎?”
顧錚是個的男子,聲音猶如古鐘擊鳴般溫和沈靜,分明是陌生人,阮綰狼狽之餘,眼眶也忽然有些熱。
Advertisement
阮綰回神,耳泛紅,垂眸輕聲說:“我沒有傷,只是有些不方便。”
顧錚這時才想起曾經看過的一本醫書,上頭記載著男子與子生理變化,忽然像是明白了什麼。
看蒼白,冷汗津津的面龐,默默地挪開了目,神中更是難得有些尷尬。
安靜的瞬間,阮綰知道他明白自己是什麼況了。
事已至此,阮綰也沒有什麼臉可丟的了,著冷冰冰的石柱,輕聲細語地說:“謝謝你。”
顧錚不知怎麼,竟覺得有些可憐。
“不必道謝。”
阮綰心中想過許多,冷靜下來,猜測他們是迷路才走到後院的,低聲問:“你是走錯路了嗎?”
顧錚聲音低沉:“嗯”。
阮綰微微轉子,抬手給他們指路:“你們從東邊的圓拱門出去……,左轉直走就是通往前院的路了。”
阮綰眼眸看向顧錚,目□□,似在問他記住了嗎?
顧錚緩緩點頭。
起,離開前說道:“你放心,今日之事,不會告訴旁人。”
顧錚走後不久,素月就拿著披風過來,幫繫起來:“姑娘您還好嗎?可有遇見什麼人?”
“沒有。”阮綰握握的手。
再次相遇,是在夜晚家宴,顧錚被眾人簇擁在中間,阮綰看著父親對他卑躬屈膝地討好,才知道原來他就是自己未來丈夫的兄長。
阮大老爺對阮綰招手,示意過去見禮。
阮綰頂著眾人艷羨的目,走到顧錚離顧錚一步之遙的地方站定,手裡握著父親塞給的酒杯。
整顆心臟都是提起來的,喧囂中彷彿能聽到自己的心跳聲。
“綰兒給國公爺敬酒,以後你們就是一家人了。”阮大老爺滿酒氣,面紅耳赤地催促。
被父親推到前面,阮綰有些無措和難以啟齒的難堪。
顧錚搖了手中的茶杯,笑容微淡,抬手攔住阮綰遞到他前的酒杯,聲音平和,卻不容拒絕:“小姑娘喝茶吧!”
他後的侍衛立刻給阮綰換了茶杯。
在這個場合,顧錚即便是喝茶,也無人敢說閒話。
手指拖著溫熱的杯壁,阮綰杏眸眸微。
“瞧我糊塗的,小姑娘嘛!喝茶喝茶。”阮大老爺附和地說道。
“綰兒來,快給國公爺敬茶。”
顧錚看著阮綰,就像是在看一個第一次見面的小輩一般,阮綰瞬間安定了,手臂輕抬:“見過國公爺。”
顧錚擺手,抿了一口茶,看向阮大老爺:“我們說話,讓小姑娘先退下吧。”
阮大老爺連聲道好,給阮綰使眼。
阮綰屈膝福,悄然退下。
剛離開,就有人湧上去,給顧錚見禮。
阮綰回到自己位置,才發現把茶杯帶回來了,著杯中淺淺的茶湯,阮綰遞到邊喝了一小口,口苦。
但灌腹中卻是舒的。
阮綰抿笑了笑,把杯子小心翼翼地放到桌上。
端起一旁的酒杯,喝了口酒了那苦味。
“姑娘您子不方便,不能喝酒。”素月小聲提醒。
阮綰彎著眼睛笑了笑:“知道啦!”
“咱們家的十三可出息了。”邊回來赴宴的十二姑娘湊過來說道,話中難掩酸意。
阮綰知道這個時候說什麼都是錯的,乾脆閉上,不說了。
見阮綰不應聲,來人沒趣兒,嘟噥了一聲“悶瓜”,便坐回去,和其他姐妹們說閒話。
阮綰地聽著。
“聽說這位國公爺還沒有婚呢!”
“要不你和離了,嫁過去。”
“我算個什麼,便是沒嫁人怕也只有給他做妾侍的份。”
幾人調笑在一起。
阮綰秀氣的眉頭皺了皺。
婚期定在了來年的二月末,聽說是個良辰吉日。
這就意味著阮綰最起碼十一月就要啟程去京城,才能趕上婚期。
離開住了十三年的家,即便在前十二年裡過得默默無聞,但它也給自己遮風擋雨,讓自己食無憂,阮綰心中還是不捨的。
但看著父親和夫人迫不及待送去京城的舉中,阮綰不知該哭還是該笑。
還沒等收拾好緒,便坐上去京城的馬車。
送嫁的是阮綰的兄長阮逸,阮大老爺原配所生,為著這個送嫁的人,家中吵了許久,因為這正是在顧錚面前表現的機會。
若能被顧錚瞧上,提拔到軍中做他的下屬,那才算是前程無憂了。
阮綰頭一次坐馬車出遠門,很是不習慣,剛出發就開始暈車。
這些在城中驛站落腳,顧錚的侍衛敲門送上湯藥:“這是國公爺讓屬下給您送的。”
素月接過來。
“替我謝過國公爺。”阮綰輕聲說。
侍衛拱手行禮告退。
阮綰站在房門口,看著侍衛回到迴廊盡頭的房間,慢慢地舒了一口氣,聞著淡淡地藥味,額頭彷彿都沒有那般疼了。
樓下大門忽然被人推開,阮綰下意識地過去。
一陣沉重的腳步聲響起。
隔著欄杆可以看到一群穿著褐衫,帶著圓帽,腰間別著長刀的人闖進來,退到一旁分作兩排站在堂中,接著一個著蟒袍外披輕裘,形修長消瘦的男子闊步。
男子長相極其俊,但一雙鋒銳鷙的目人不敢直視,他掃視整個驛站,與阮綰對了一眼。
阮綰汗立起,心中一嚇,往後退了退,差點兒絆到門檻。
男子的腳步微轉,往樓梯徑直走來,靜謐的大堂,只聽到他的腳步聲。
而那些褐衫男人在他踏上樓梯時,立刻關起驛站大門,握刀守在各扇窗欄前,這樣的陣仗讓人不寒而栗。
阮綰第一次到這種架勢,一旁的素月也被嚇到了,下意識地站到前面擋住阮綰的,阮綰咽了咽嚨,知道這人應該不好惹,朝他微微福,拉著素月的手,側握著門把就要把門關起來。
男子站在二樓樓梯口,了手腕,慢悠悠的把玩著手裡的扳指,目平無波瀾,冷漠地瞥過阮綰,見們作,眼裡閃過不屑。
這眼神就像是在看一個死人,阮綰關門的手瞬間僵,尖聲堵在嚨口。
這時盡頭的廂房房門從裡推開,顧錚站在門前,看著來人,淡淡地開口:“津延!”
顧錚沉靜的聲音帶著一無奈,制止他繼續嚇人。
顧錚走過來,看著阮綰,略作安:“無礙,進去吧!”
看阮綰關門進屋了,顧錚示意週津延跟他走。
週津延挑挑眉,戴好手裡的墨玉扳指,與他一同進了廂房。
顧錚親自給他倒了一杯茶:“暖暖。”
週津延閒適地靠著圈椅椅背,骨節分明漂亮的手指敲著薄薄的杯壁:“我的人已經安排妥當,剩下的你自己做好準備。”
顧錚點頭:“今晚估計要下雪,在驛站宿一夜,明早再走?”
週津延眉心:“不用。”
知道攔不住他,顧錚緩聲叮囑:“路上小心。”
週津延扯,不耐的輕嘖一聲,瞥了他一眼:“知道了。”
從袖中拿出一封信遞給他,起拂了一下披風。
他只待了片刻的功夫,他上還帶著冷氣,茶杯裡的茶還燙著。
顧錚走到窗戶口,推窗,一刺骨的寒氣撲來,低頭剛好看到週津延高坐駿馬之上的孤寂背影。
猜你喜歡
-
完結810 章
鳳謀天下:王爺為我造反了
「我雲傾挽發誓,有朝一日,定讓那些負我的,欺我的,辱我的,踐踏我的,淩虐我的人付出血的代價!」前世,她一身醫術生死人肉白骨,懸壺濟世安天下,可那些曾得她恩惠的,最後皆選擇了欺辱她,背叛她,淩虐她,殺害她!睜眼重回十七歲,前世神醫化身鐵血修羅,心狠手辣名滿天下。為報仇雪恨,她孤身潛回死亡之地,步步為謀扶植反派大boss。誰料,卻被反派強寵措手不及!雲傾挽:「我隻是隨手滅蟲殺害,王爺不必記在心上。」司徒霆:「那怎麼能行,本王乃性情中人,姑娘大恩無以為報,本王隻能以身相許!」
150.5萬字8 82602 -
完結114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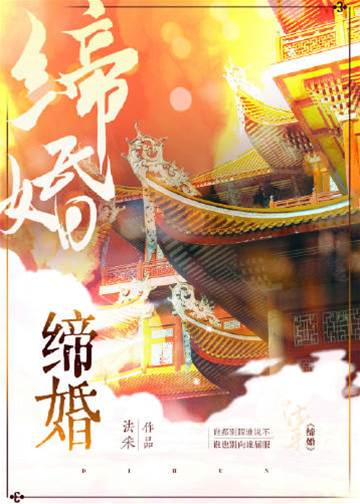
締婚
家敗落之後,項家老爹成了人人喊打的奸佞,項宜帶著幼年的弟妹無依無靠、度日艱難。 她尋來舊日與世家大族譚氏的宗子、譚廷的婚約,親自登了譚家的門。 此事一出,無人不嘲諷項家女為了算計、攀附譚家,連臉面都不要了。 連弟弟妹妹都勸她算了,就算嫁進了譚家,...
45萬字8.33 82137 -
完結136 章

重生之窈窈再愛我一次
謝令窈與江時祁十年結發夫妻,從相敬如賓到相看兩厭只用了三年,剩下七年只剩下無盡的冷漠與無視。在經歷了丈夫的背叛、兒子的疏離、婆母的苛待、忠仆的死亡后,她心如死灰,任由一汪池水帶走了自己的性命。 不想再次醒來卻發現自己回到了十七歲還未來得及嫁給江時祁的那年,既然上天重新給了她一次機會,她定要選擇一條不一樣的路,不去與江時祁做兩世的怨偶! 可重來一次,她發現有好些事與她記憶中的仿佛不一樣,她以為厭她怨她的男人似乎愛她入骨。 PS:前世不長嘴的兩人,今生渾身都是嘴。
27.1萬字8 2660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