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千金回家種田了》 第103章 洞房
擔任全福夫人的四嬸子,站在背後,為梳頭髮。
口中念著吉祥話兒:
一梳梳到尾
二梳姑娘白髮齊眉
三梳姑娘兒孫滿地
……
兩位嫂子在房間里檢查嫁、腰帶、繡鞋、首飾等。
杜金花則失去了往日的利落,難得像是沒了主心骨,不知道做什麼似的,這裡,那裡,時不時來到陳寶音邊,的頭髮。
想給閨梳頭,但算不得好命婆,只得忍痛割,把位置讓給別人。
「今兒啊,你要一天肚子,水不能喝,飯不能吃,你得忍忍。」杜金花轉來轉去,口中念念叨叨,「吃了東西,你坐不住,這樣不好,不好的。」
陳寶音聽著,便想扭過頭看。
但的頭髮被四嬸子抓在手裡,腦袋固定住,不能,只能用餘看過去。便見杜金花面發灰,看上去格外顯老,眼下褶皺很深,好似一晚上沒睡似的。
心頭酸了一下,陳寶音道:「我記住了,娘。」
這話,杜金花說了好些遍了,前幾日就開始念叨。可陳寶音不覺得煩,因為要嫁人了,往後還能聽到念叨的時日就了。
杜金花卻好似沒聽見似的,還在絮絮叨叨:「進了喜房后,蓋頭不能揭,要等姑爺來揭。」
陳寶音嚨哽住,想點頭,但腦袋本不了,便道:「嗯。」
錢碧荷察覺到什麼,把杜金花支走了:「娘,客人們的吃食做好沒有?您去瞧瞧。」
今日寶丫兒親,家裡事多,來幫忙的鄉鄰也多,需得管人家一頓飯。而這飯也不是們婆媳來做,都沒工夫呢,讓寶丫兒的大娘和嫂子們來幫的忙。
「我幹啥,你不會去?」杜金花反口道。才不想去。但沒頭沒尾的轉了兩圈之後,口中叨叨著,還是出去了。只是,出門的時候,低頭了下眼角。
Advertisement
陳寶音沒看見,正被兩個嫂子圍著穿嫁。
天漸漸亮了,熱鬧的聲音連片,大家都在忙著陳寶音不懂得的事,只需要端端正正地坐在房間里,一不,等待新郎來迎娶。
放在往日,陳寶音很不樂意這樣干坐著。但是今日,腦子裡好像進了水,泡脹了,轉得慢慢吞吞,又好像本轉不,只見人進人出,只聽高高低低、起起伏伏的說話聲,低頭呆坐著。
不知道過了多久,外頭轟然熱鬧起來,有人喊道:「迎親的來了!」
「新郎來了!」
鞭炮聲噼里啪啦的響起來,好似平地炸雷,將陳寶音猛地驚醒。忽然心慌起來,就像剛剛知道,自己要嫁人了!
可是沒有人在邊安,都跑出去了,招呼客人,忙碌婚禮。
鑼鼓聲喜氣洋洋,孩在窗下跑過,熱鬧得不得了,每個靜都在提醒陳寶音,要嫁人了,就在今日。
顧亭遠帶著迎親隊伍,抵達籬笆院落前。
進門時,按照規矩,被「刁難」了一番。不過,他文采出眾,整個陳家村的人加起來,也難不住他。
屋裡面,陳寶音依稀聽到他溫潤的聲音:「晚輩必好好對。」
「終我一生,不敢相負。」
這話說得好聽,引得陣陣喝彩。陳二郎又出了題,考驗他的格。顧亭遠稍稍狼狽了些,才過了關。
陳大郎進屋,沉默的將妹子背出來,送上花轎。
他是家裡最高大的人,也是脊背最寬闊的人。陳寶音趴在他背上,雖然跟大哥不算太相,但此刻卻格外不舍。
杜金花早就哭得站不住,被錢碧荷扶著,忍著喊「寶丫兒」「寶丫兒」。
錢碧荷一手扶著婆婆,一手蘸眼角,也很捨不得小姑子出嫁。
只有孫五娘,臉上不見多難過,只掛著許傷。仔細看,眼角眉梢還著歡喜——為啥不歡喜呀?妹子嫁人了,嫁的是個好人呢,以後就會過上好日子,就像跟陳二郎一樣,過得著呢,替妹子高興!
「若是他對你不好,你回家來。」上花轎之際,陳寶音聽到大哥說:「大哥教訓他!」
就算以後顧亭遠出息了,當了大,但那也是他妹夫。他一個大舅哥,教訓教訓姑爺,有什麼的?天經地義的事!
「嗯。」陳寶音眼眶酸熱。
轎簾掀開,坐進去,隔著紅蓋頭,最後看了一眼。滿地的炮仗皮,一雙雙鞋子,一角籬笆院牆。
只是沒見到杜金花,看了幾眼,都沒有找到杜金花的影。滿是憾的,轎簾落下來,什麼都看不見了。
隨著一聲「起轎」,下顛簸起來,陳寶音無比清楚地意識到,要離開家了。
又一次,要離開家了。而這一次,在家裡只待了一年半,就要去往新的家。
滴答,眼淚掉落在喜服上,暈染開一片。
鑼鼓聲敲得震天響,好似這是一件天大的喜事,可陳寶音只覺得委屈,忽然後悔了,不想嫁了。
為什麼要嫁人?想娘。
但轎子搖搖晃晃的,始終向前行。親這樣的大事,自然不能在村北的茅草屋裡舉行,顧亭遠前些日子就回到鎮上,把清水巷的院子收拾一番,布置喜房。
轎子搖搖晃晃的,抬到了鎮上。
巷子里也很熱鬧,顧亭遠的鄰居們,同窗,先生,顧舒容的乾爹乾娘,王員外等人,都在等著新人進門。看到迎親隊伍回來,頓時熱鬧起來。
下轎,進門。
拜天地。
陳寶音頂著蓋頭,被人扶著,完了婚禮儀式。然後,送喜房中。
顧亭遠在外面招待客人,眷們在喜房裡陪著陳寶音,還有調皮的小孩子想掀開蓋頭看看新娘子的模樣,被制止了。
「吱呀」一聲,門打開了。
顧舒容跟眷們打著招呼,然後走到床邊,抓起陳寶音的手,往手裡塞了一把什麼:「時間還早,你若累了,靠著床柱瞇一會兒。」
這卻是不合規矩的,但顧舒容不是在乎規矩的人,更心疼寶音。
「嗯。」陳寶音點點頭。
顧舒容還要招待客人,彎腰在耳邊說了句:「空吃了。」然後起走了。
沒人看見往陳寶音手裡塞東西了。陳寶音趁著人不注意,低頭看了看手心裡,微微驚訝。
是一把乾,炒得很乾的那種,既磨牙,又充。這是怕著呢,陳寶音惶惶的心,忽然就安定了兩分。
怕什麼呢?雖然是新家,但是家裡的人,都認得。顧亭遠是不敢欺負的,而顧舒容是很好的姐姐。這樣想著,放鬆了一些,悄悄把一塊乾塞口中。
乾很香,一塊就能消磨好長時間。
等到把乾都吃完,婚禮也到了尾聲。顧亭遠和顧舒容,以及鄰居阿婆幫襯著,一起送走客人們。
門外漸漸陷安靜。
很快,門又打開了,「吱呀」一聲,輕輕的腳步聲慢慢走向床前。
陳寶音嗅到了輕微的酒氣,不由得張起來,腦袋低垂,又很快被抬起來,改為絞著手指。
「嗒。」放在一旁的喜桿被拿起來。
有別於子輕盈的腳步聲,逐漸走近床前,男子低潤的聲音響起:「猜猜我是誰?」
「……」陳寶音。
滿心的張,瞬間破裂。
有些沒好氣,很想一把拽下蓋頭,好好看看這個不正經的人到底是誰!
手才一,就聽他阻止道:「別,我來。」
喜桿出,輕輕挑蓋頭,頓時滿屋的亮映眼底。陳寶音眨了眨眼睛,才看清的前人。
紅燭,紅,墨發。
抿抿,忍不住輕聲道:「顧亭遠。」
他的名字,顧亭遠。
不是別人,是要嫁的人,他顧亭遠。
「嗯。」顧亭遠應道,放下喜桿和蓋頭,坐到邊。
他很注意分寸,坐在離尚有一臂之隔的地方,這讓張了一下,渾繃的陳寶音都不好意思往旁邊挪了。
顧亭遠坐下后,手向被子下面,出一把吃的,遞過去道:「吃不吃?」
被子下面鋪的全是大棗、花生、桂圓、蓮子。
早生貴子。
陳寶音懂得這個。
瞪了他一眼,然後出手,了粒紅棗,啃起來。了一天,有吃的,還挑剔啥?
顧亭遠見吃紅棗,就又去被子下面掏,掏出來都擺在手心裡,讓從手心裡拿。
「我想喝水。」吃了兩顆紅棗,陳寶音道。
顧亭遠應了一聲,立即起去倒水。
陳寶音看著他。紅燭之下,他的背影比印象中的偉岸些,顯得有些陌生。而他執起茶壺,倒水的作,又斯文雅緻,看起來賞心悅目。
雖然陳寶音從前沒想嫁人,但此刻看著顧亭遠,心想,竟挑不出他的病來。他,就連頭髮看上去都不討人厭。
很快,顧亭遠端著水杯回來,在床邊坐下。
陳寶音手,他卻不給。
瞪圓眼睛,喝斥道:「做什麼?」
「我喂你。」他說,表並沒有多侵略,俊秀的臉上滿是溫與喜,偏偏讓陳寶音渾不自在,只想有多遠躲多遠。
不想怯,顯得自己很膽小似的,於是壯著膽子大聲說:「我自己喝。」
顧亭遠靜靜地看著,語調如常:「你了一天,有力氣嗎?」
「怎麼沒有?」陳寶音大聲說,「我不僅能喝水,我等下還能吃飯呢!」
男人眼底劃過一抹笑意,把茶杯遞給:「慢慢喝。」
陳寶音接過。
「你幹什麼?」正要喝,卻覺他坐了過來,立刻戒備地瞪他。
顧亭遠面龐溫,說道:「我擔心你握不穩,倘若灑在上,便不好了。我接著,你放心喝。」
陳寶音看著他一派正氣的樣子,慢慢臉上紅了。:,,.
猜你喜歡
-
完結315 章
冷帝在上,傲嬌皇後求休戰
一朝穿越,冷羽翎隨還冇搞清楚狀況,就被成親了! 他是萬人之上的皇帝,高冷孤傲,“我們隻是假成親。” 成親後,冷羽翎感覺自己被深深的欺騙了! 為什麼這個皇帝不僅要進她的香閨,還要上她的床 這也就算了,誰能告訴她,為什麼他還要夜夜讓自己給他生娃呢!
53.9萬字8.8 66122 -
完結260 章

流放路上炮灰寡婦喜當娘
許柔兒萬萬沒想到,自己竟然穿成炮灰寡婦,開局差點死在流放路上!不僅如此,還拖著個柔弱到不能自理的嬌婆婆,和兩個刺頭崽崽。饑寒交迫,天災人禍,不是在送死就是在送死的路上。但許柔兒表示不慌。她手握空間富養全家,別人有的我們也有,別人沒有的我們更要有!“那為什麼我們沒有爹。”“爹?”許柔兒看著半路搶來的帥氣漢子,見色起意,一把薅來。“他就是你們的爹了!”帥男疑惑:“這可不興喜當爹。”“我都喜當娘了,你怕什麼喜當爹!”
47.3萬字8 29692 -
完結377 章

女主,你狐貍尾巴露了
養狐貍之前,裴鳴風每日擔憂皇兄何時害我,皇兄何處害我,皇兄如何害我?養了狐貍之后,裴鳴風每日心煩狐貍是不是被人欺負了,狐貍是不是受傷了,狐貍是不是要離開自己了。冀國中人人知宮中有個“狐貍精”,皇上甚為寵之,去哪帶哪從不離手。后來新帝登基,狐貍精失蹤了,新帝裴鳴風帶了個蕙質蘭心的皇后娘娘回來。
66.9萬字8 11395 -
完結11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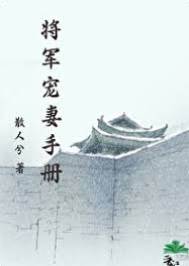
將軍寵妻手冊
雲府長女玉貌清姿,嬌美動人,春宴上一曲陽春白雪豔驚四座,名動京城。及笄之年,上門求娶的踏破了門檻。 可惜雲父眼高,通通婉拒。 衆人皆好奇究竟誰才能娶到這個玉人。 後來陽州大勝,洛家軍凱旋迴京那日,一道賜婚聖旨敲開雲府大門。 貌美如花的嬌娘子竟是要配傳聞中無心無情、滿手血污的冷面戰神。 全京譁然。 “洛少將軍雖戰無不勝,可不解風情,還常年征戰不歸家,嫁過去定是要守活寡。” “聽聞少將軍生得虎背熊腰異常兇狠,啼哭小兒見了都當場變乖,雲姑娘這般柔弱只怕是……嘖嘖。” “呵,再美有何用,嫁得不還是不如我們好。” “蹉跎一年,這京城第一美人的位子怕是就要換人了。” 雲父也拍腿懊悔不已。 若知如此,他就不該捨不得,早早應了章國公家的提親,哪至於讓愛女淪落至此。 盛和七年,京城裏有人失意,有人唏噓,還有人幸災樂禍等着看好戲。 直至翌年花燈節。 衆人再見那位小娘子,卻不是預料中的清瘦哀苦模樣。雖已爲人婦,卻半分美貌不減,妙姿豐腴,眉目如畫,像謫仙般美得脫俗,細看還多了些韻味。 再瞧那守在她身旁寸步不離的俊美年輕公子。 雖眉眼含霜,冷面不近人情,可處處將人護得仔細。怕她摔着,怕她碰着,又怕她無聊乏悶,惹得周旁陣陣豔羨。 衆人正問那公子是何人,只聽得美婦人低眉垂眼嬌嬌喊了聲:“夫君。”
17萬字8.33 5690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
